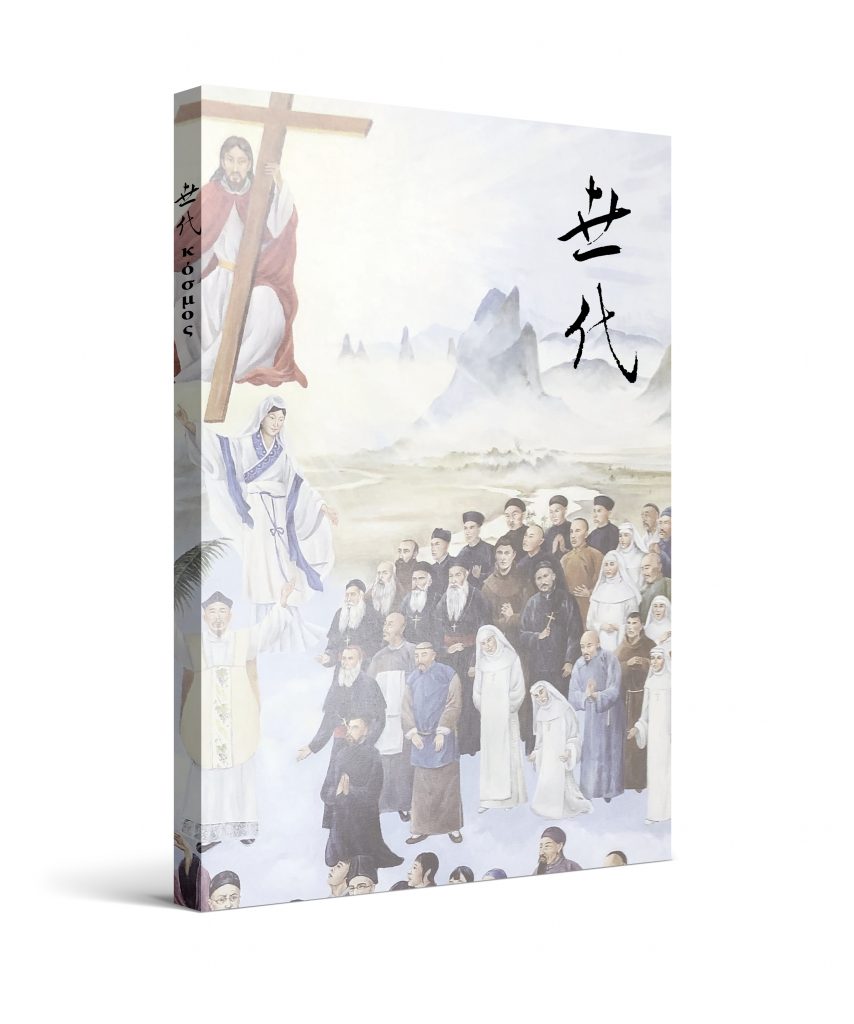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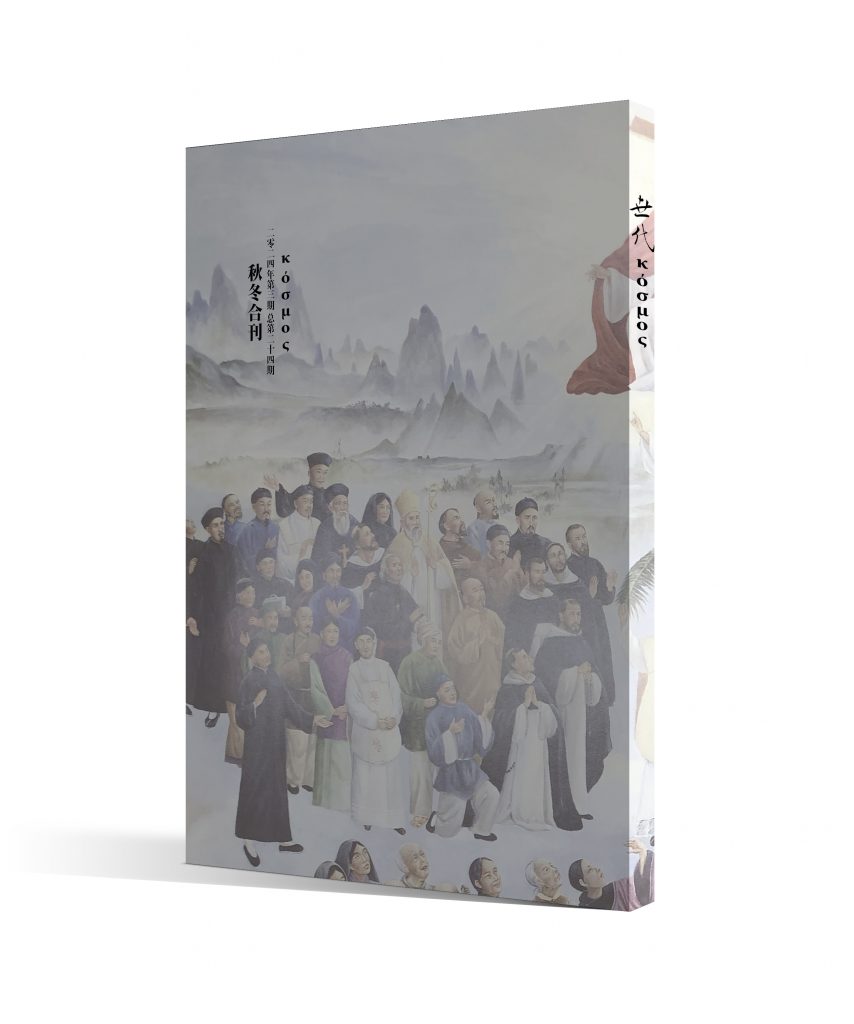
据学者统计,晚清800余起几乎遍及全国的民教冲突(1860—1899年),其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并非基督信仰与儒家价值观念在“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差异,仿佛二者绝不相容,而是涉及有关社会秩序(如教士逾分、地方习俗、谣言)和实际物质利益方面(如还堂纠纷)的龃龉。<1> 这提示我们,对晚清教案的认识与评价,要避免以笼统的理论概念演绎,取代对复杂多面的历史现象做具体分析。一种可以参考的研究路径是,将个别教案放在地方和区域社会的框架中,梳理该教案的前因后果,发掘其独特之处,展现教案的多元面向和立体图景,将微观分析与宏观脉络结合起来。<2> 因为教案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当事者各有不同,其背后的直接原因错综复杂,所产生的影响有大小之别,难以从中归纳出教案发生与进展的通则。<3>
确实,不可否认,条约制度(treaty system)对传教事业的保护,以及列强在华的势力扩张,是晚清民教冲突迭起的宏观处境。条约对传教的负面影响,让晚清士人直接感受到的是,基督教来华与释、回不同,“彼以顺施,此以逆取”,基督教“常与丧师辱国之意,胶结而不可分”,致使国人“创钜痛深”。<4> 这种感受以及基督教与武力联姻的印象,用民国人物蒋梦麟(1886—1964)的话来说就是,人们逐渐“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5> 话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据此将晚清所有民教冲突化约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代具体分析基督教(包括传教士和教民)在怎样的处境中,与地方官绅和民众呈现何种张力,特别是,传教士对炮舰外交所持的矛盾心态。
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晚清教案的反帝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笼统叙事,仍然频频见诸网络和各种读物,特别是纪念性质的教案遗址、博物馆展览等处的文字说明材料。在这些叙事中,来华传教士多被描述为作奸犯科、鱼肉乡民、道德败坏、心怀叵测之辈,华人教民则以仗势欺人、贪婪无忌、入主出奴的面目示人。
借用柯文(Paul A. Cohen)在《历史三调》中的术语,我们可以将上述反帝反洋教的教案叙事,看作某种刻意制造的“神话”(Myth)。它是神话制造者认识和理解历史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关心历史对当下的功用(比如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超过关心历史参与者的实际经历(Experience),也不真正在意对历史真相的探知与理解;后者则是历史学家的追求,他们利用搜集到的证据,发挥想象力,努力去理解和解释作为事件(Event)的历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6> 有时,教案的神话制造者为了让自己的叙事看起来“可信”,也会利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来获取当事者的“经历”,然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受访者反映的与其说是自己的经历和当时的意识,不如说是当前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访问者的观念意识。<7>
虽然柯文也承认,事件、经历和神话,这三种了解历史的途径,其间虽有明显的矛盾,但在其各自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历史学家追求的历史事实必定比人们想要相信的历史更有价值,这种观点本身也许只是一种神话。<8> 然而,真实可信本身在事物的价值序列上仍值得人们优先关注与追求。<9> 或许需要提醒的另一个极端是,教会方面(包括传教士、信徒)对教案的叙事,对传教士的圣徒式刻画,是否也可能是制造出来的另一种神话,偏离了圣经叙事“书法不隐”、善恶俱彰的原则?<10>
本期主题为“晚清教案”,所刊两篇主题文章,分别探讨咸同之际的贵阳教案和光绪年间的兖州教案。《胡缚理与咸同之际的贵阳教案》一文,虽未尽合区域研究的标准,仍试图基于清方、法国领事和传教士三方的来往记录,理清该案来龙去脉,呈现三方在教案交涉中各自的关切与立场,冀此表明教案发生及进展的复杂性,以往对涉案传教士是非得失的评论过于简单,需要重新认识。《何处不可设教?——历史上的兖州教案》,则借清末兖州建堂之争引发的教案,联系现实,说明耶儒之争既是晚清民教冲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摆在当今儒生和基督教会面前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
我们认为,就晚清教案这个议题而言,无论是重新评价传教士的是非得失,还是以古观今照看现实问题,其前提都是尽可能基于完整史料梳理清楚个别教案的始末因果。事件(即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与理解)应优先于神话(即从历史中吸取能量,服务于特定的现实目的),泛泛之论应让位于具体分析,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1>
<1>见陈银崑,《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一八六0——一八九九)》,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5页。
<2>邢福增,“晚清教案与反教思想研究述评”,收入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54—1255页。
<3>参见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xi.
<4>“支那教案论”,见《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12页。
<5>蒋梦麟,《西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
<6>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言及第52、177—178页。
<7>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有关教案的口述史和田野调查报告,基本上反映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观点,在采用时应当谨慎。比如1963年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师生在广西田林县做调查,完成的《广西田林县天主教调查报告》。由于西林教案案发时(1856年)距此次调查事件已过百年,显然不是当事者口述,被访群众对此案的认知多半是“听(闻)老人说”、“听说”、“口碑流传”。访问者承认由于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关于杀马神甫的经过,各种说法有差异,有的说法不一定真实。(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院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田林县天主教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64年,第16页)又如1961年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巨野教案调查小组发布的“巨野教案调查”,其中提到根据巨野县公安局提供的材料,证明德国圣言会传教士薛田资强奸妇女十余人,然而仅一笔带过,未附录该材料。“磨盘张庄座谈记录”(1957年10月2日)受访者讲述巨野教案发生前后,当地群众恨恶教徒,因教徒不准村民说“教”,包庇无赖。(见山东省历史学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0、41页)这类口述史调查自身存在的局限,大概与义和团口述史调查存在的限制相似,比如技术与方法落后、方言障碍、受访者为文盲且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等等(参见第柯文,《历史三调》,第84、276、300—301页)。
<8>柯文,《历史三调》,第248页。
<9>“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圣经·马太福音》5章37节);“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圣经·腓立比书》4章8节)。以下所引经文均出自和合本。
<10>此处的圣经叙事原则,最明显的体现大概是对大卫王犯奸淫和借刀杀人的记载(见《圣经·撒母耳记下》第11章)。耶稣的家谱记有其先祖妓女喇合、摩押女子路得,直书“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圣经·马太福音》1章5—6节),亦体现圣经叙事的书法不隐。
<11>司马迁,《史记》卷130(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5页。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4期的主题是“晚清教案”,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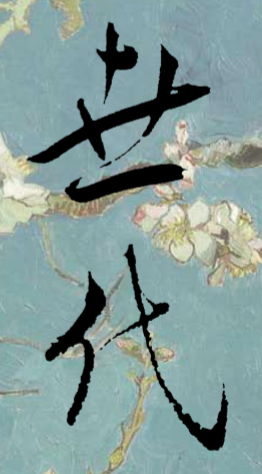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