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华人基督徒学者温伟耀(左)和罗秉祥(右)]
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汉语神学运动,是华人文化宣教事工需要理解、对话和借鉴的重要对象。作为一场影响广泛的思想与文化运动,汉语神学的参与者们尽管对神学、教会与社会主题的理解存在诸多差异,但大多致力于促进基督教学术研究成为中国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使之与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各种现代文化思潮并驾齐驱。<1> 为了厘清汉语神学运动中独特的文化宣教向度,本文将首先概述汉语神学运动的定位与导向,随后以案例方式分析两位学人的实践与成果,最后提出与之相关的文化宣教议题。笔者认为,汲取前辈学人的经验与智慧,华人文化宣教的实践者需要将汉语神学作为其见证真理活动的空间、反思文化议题的起点和推进策略性目标的指南。
一、汉语神学的文化定位
“汉语神学”概念具有广义与狭义双重内涵。广义的汉语神学由当代神学家何光沪提出,认为凡以汉语为载体的基督宗教神学著作,不论撰写者的国籍地域,一律统称汉语神学。此一界定尤其重视不同地区汉语群体的生存经验和文化处境,肯定这是构成其神学内容的独特元素。按此定义,汉语神学可以远推至唐代景教,涵盖由古代和现代汉语所写成的有关基督信仰的全部著作。<2> 相比之下,狭义的汉语神学指的则是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大陆自发要求重新研究基督教思想与文化的人文学者,他们大多立足于人文学界而发展出有别于教会传统的汉语神学。与传统的教会神学不同,狭义的汉语神学起源并成长于中国人文学界。与传统神学类似,狭义的汉语神学也致力于提出面向教会与社会的各种议题。汉语神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杨熙楠曾明确指出,该运动自身的奋斗目标包含三个面向:
一、以汉语文化的历史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范的基督神学文化;
二、在汉语思想学术领域建设神学学科,与儒学、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思想构成学术性对话关系;汉语神学亦应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范,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
三、它是汉语世界(大陆、台湾、香港、星马、北美华人社区)的各社会地域的汉语宗教学者的共同志业。<3>
上述使命突显出汉语神学运动寻求以汉语为载体、从事文化与宗教对话的神学意象。基于上述特征,狭义的汉语神学即汉语神学运动在其关注焦点和议题设置方面,必然会与中西方的教会神学传统存在明显差异。学者卓新平将其归纳为三端,即人文性、跨教派性和跨文化性。<4> 这三方面特点都与文化宣教有着密切联系,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汉语神学运动发轫于中国人文学界,其生存形态也以中国人文学界为依归。大部分立足于人文学界的基督教研究学人不是要寻找信仰的家园,而是把基督宗教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来探究。当然,该运动自其伊始便不乏基督徒学者的参与,而在运动兴起十多年后,新生代的汉语神学学人中也多有活跃的认信者。基督徒学者的兴起及其信仰身份,不仅没有改变汉语神学立足于人文学界的定位及其相应的学术规范,反而为运动增添了与宗教经验有关的反思与讨论向度。<5>
其次,汉语神学自身不归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基督教派或宗派,其知识谱系可以来自中外历代基督教的思想和神学资源。这是因为多数学人对基督教研究的重点,不是考虑某议题是否合乎宗派或教派正统,而是更为关心该研究是否有助于推进其学科的发展。这种研究导向偶然间跨越了华人教会神学长久以来以西方教会神学为皈依的主导局面,同时又促成了基督教神学与不同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对话与整合。这种意义上的汉语神学运动,有潜力在传统建制教会和神学院外开拓新的研究平台,并发展出独特的研究旨趣。正如刘小枫所展望的,
如果人文旨趣的汉语基督神学定位在建设汉语的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神学学术,就会通过大学—研究院建制为基督教思想—学术生产知识人,扩展基督教思想学术的传承能力和参与现代思想对话的能力。……因此,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分化为人文神学和教会神学,恰恰是基督教在现代语境中的生存需要,汉语基督神学的发展同样需要这两种不同维度的神学。<6>
第三,该运动充分展示出跨文化特质,即不仅要跨越各个民族文化,而且要跨越中西文化的截然二分。汉语神学学人主张挖掘汉语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出发理解基督神学,并致力于消弭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隔阂。
上述特征若从文化宣教角度来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若要兑现相应的实践效果,还需要更具体的思想议题和工作方案加以充实。下文将选取当代基督教学者温伟耀与罗秉祥的研究成果作为代表,详细考察各自整合汉语神学与文化宣教方案的具体途径。
二、由沟通的情意主义建构汉语文化神学
温伟耀(1952— ),出生于香港,基督教宣道会会友,当代华人神学家,在文化神学、灵修神学和汉语神学领域颇有建树。温曾自述,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与使命,是使中国人能认识基督教的美好。<7>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温有十余年全身心投入汉语神学运动,于2009年出版个人文集《生命的转化与超拔》,该书一年内在大陆地区再版四次,成为多所大学基督教研究的推荐参考书。此外,温的其他汉语神学代表作包括:《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成圣之道》、《心灵爱语》以及《在地若天》等著作。本节重点介绍温在文化神学领域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这既是其本人多年学术思想成果的结晶,也是其长期身体力行文化宣教工作持守的原则。
早年深研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文化神学的温伟耀,将其汉语神学的一贯立场称之为“沟通的情意主义(Communicative Personalism)”。据其解释,这一方面是为了对应传统中国文化意识而提出的基督教独特的思维基础,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汉语神学的核心立足点。所谓“沟通的情意主义”,是要突出基督教的宗教经验,强调作为有情谊的主体的人与有情谊的主体上帝之间有情谊的相遇。具体而言,这一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文化指向:第一,对比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终极追寻是“境界性的自我超越”,基督教的宗教经验,本质上是一种追寻人与上帝作为主体与主体之间对话性的生命情操;第二,对比中国传统的人生修养哲学在于“向内反求”并信仰人的终极主体的自给自足,基督教因为体验到上帝作为一位“有情意的无限他者”,而在一种与他者相遇、他者介入、他者在场和他者指点的情态中修养并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第三,对比中国传统理解宗教的存在意义和功能在乎其是否给予人安身立命(自我超越)的条件与文化价值,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是人与上帝和好(关系的重建)。<8>
上述神学立场得以成立,首先需要处理上帝作为一位无限的主体与人作为有限的主体相遇时,这两个有情意的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张力问题。对华人教会及社群而言,这直接关涉到如何理解“上帝在其自己(God in Himself)”与“上帝在关系中(God in Relation)”这两个面向上帝属性之间的关系。温相信上帝属性的这两面尽管非常不同,却可以并行不悖。唯有如此,才能辨识出那一位既超越自存,又可以与人建立亲切关系;既信实不变、又能与人共尝痛苦的上帝的性情。<9> 这样理解上帝属性的两面对文化神学及宣教最重要的引申意义,是得以指出:只有紧扣上帝那超越的“在其自己”的本质,和上帝“在关系中”所显出的情意,一种对上帝整全的认识才能朗现于华人的宗教思维和经验之中。对屡遭苦难的华人教会与社会而言,上帝不会因为与人共尝痛苦而失去他信实不变的本质,而上帝也不会因为他那不动摇性,而令他成为只会隔岸观火的旁观者。
从沟通的情意主义立场出发,温伟耀进而将汉语神学理解为一种独特的跨文化神学,并从文化宣教的角度提出了三方面需要反思和重构的课题。<10> 他指出,当基督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接触的时候,可以被视为一种跨文化沟通的过程。这种相互性不仅要求把国人视为宗教的受众,也要求传教士一方愿意自我转化,去为了其沟通对象而尝试跨文化适应。在实践上,基督教可以对中国文化做出批判,但也需要因为认识了中国文化而做出自我批判。温认为,在这一方面的核心议题是关于人性善恶的理解。一方面基督教要挑战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人性本善论证的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也要做出反思,对自身传统尤其是新教传统中的原罪论做出客观而真诚的检讨。
第二,跨文化沟通一方面需要各方参与者保持多元文化的身份认同,同时也需要各自投入到不断开放和敏锐的自我转化的学习历程中。来华宣教士不是中国人,他们也不需要成为中国人,尽管他们无可避免地立足于自身文化作为出发点,却需要不断培养开放、敏锐的自我解构和重构的勇气,好让他们的宣教经验成为自我批判和自我充实的学习历程。例如,在中国传统以报应、伦理为导向的宗教氛围中,国人大多难以理解和接受新教因信称义的救恩论观点。对于这种障碍,温提出可以沿着关系范畴的思维加以分辨。首先需要肯定基督教从来没有轻视道德人格与修养,其核心价值“爱”正是伦理的最高展现。此外,基督教还主张人伦社会与道德情操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相处共存的规范力量和秩序,这是上帝赋予人类文明的普遍恩典。而拒绝与上帝建立和好关系的,其结果就只能是与上帝永恒的分离。
最后,除了自我批判和转化性学习,跨文化神学的实践者还需要有跨文化聆听的能力,即放下自己的既定思维模式,真切地进入对方的生命世界之中。温举例说,基督教救恩论中关于基督代赎的教义,已被证实是建基于西方传统哲学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之上的,其核心主张是耶稣基督带着“普遍的人性”去经历死亡与复活,而全人类也就在基督里都被替代地死了并复活了。然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没有这种理念论的既定思维模式。据此,他提出汉语神学需要审慎反思这种建基于某一哲学传统的救恩论教义,重构以宗教体验境界为基础的圣灵基督论,否则可能会重蹈以往宣教实践中先西化才可信教的覆辙。
温伟耀在汉语神学实践中贯彻上述倡议的成果,以《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化》和《成圣、成仙、成佛、成人》两书最为突出。前书是其年近五十出版的一部专著,凝聚了中年时期神学思考的结晶。此书独到的创见,在于首次从宗教经验的视角提出,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需要基督宗教。第四章详细讨论基督教的宗教经验模式,是全书的精华部分。作者指出,基督教所信仰的神不同于其他宗教信仰的对象,是一位有情意的无限他者;而基督教的宗教经验也有别于其他宗教的“奥秘经验”,是经验者与神性的对象之间可以发生对话关系的经验。<11> 本章的重点是分析《圣经》中人与神之间有情意相遇的两种宗教经验模式,分别是超自然的启示(或神迹),以及圣灵内住的启示。无论哪一种模式,作者强调都需要以《圣经》作为认识神的最高标准,和对人神相遇的权威记录。而圣经叙事的中心是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事件,这是神向人启示、与人沟通和拯救行动的高峰与终极表现。当基督升天之后,圣灵则继任其职分,承担起真理的教导者和信徒信仰生活之维护者的工作。
在讨论在祷告中寻求和辨识圣灵带领的一节中,作者首先区分了神向人传达心意的两种类型:普遍规范和特殊指引。就前者而言,重点是认识到辨识神的声音本质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无法归纳成公式或方法,因为其中的关键是人的生命品格和人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与神亲近的人能够辨识出神的声音,依靠的是“经验积累得来的直觉”。 倪柝声则直接将这种特殊的直觉称为“灵的直觉。”<12> 作者进一步指出,“灵的直觉”的经验性特质,是其发自全人最深的地方,带给人平静和安稳,并催促人按照圣灵的原则行动。这与人的理性思考和情感冲动皆有不同。前者是人有意识通过分析和推理而获得的思考成果,而后者是由外部的环境因素挑动、带有起伏变动的非理性反应。
就辨识神的特殊指引而言,信徒操练的重点落在所谓的“三重亮光”上,即分辨圣灵在人内心的说话和感动,并与《圣经》的教导和环境际遇的布局相互配合,以此来判断神在特殊处境下要向人传达的心意和要求的具体内容。作者在此发展了倪柝声的观点,提出圣灵感动与际遇布局互动方面的阶段性指引。简言之,无论透过环境的布局还是圣灵的感动,神除了向人传递心意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与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对那些心思与神较远(或灵命较浅)的人,神通常使用特殊的际遇来启示自己的心意和要求。而对那些熟悉神的声音、与神心意接近(或灵命成熟)的人,神则用更简明和直接的方式对其内心说话。本节的讨论集中呈现出作者神学和伦理省思的旨趣,对中华神学传统特别是倪柝声圣灵观的继承,以及对信徒信仰与灵性操练实践的关注。
《成圣》一书是温伟耀后期神学、伦理与灵修创作的代表作品。<13> 该书以探索人性善恶根源与扬善弃恶之道为主题,对比中国儒、道、佛的人生体验与基督教传统的人性洞见,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更为全面且富有实践性的生命提升蓝图。在结论和应用部分,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基督教伦理实践的独特基础与动力两个方面,总称之为有上帝介入的道德修养模式。
作者首先指出基督教信仰与伦理实践的独特之处,在于“回归上帝、与上帝重建关系,让上帝介入人的道德生命之中”是使人为善去恶的最关键因素。<14> 具体言之,与上帝和好带来的生命转变包括了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在客观上,是与上帝的关系及个人身份上的全新转变,即获得儿女的地位,从此有份于上帝的救恩计划,并分享上帝的恩典与能力。在主观上,则是圣灵的内住与更新,恢复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亲密关系,并由此带来道德与宗教境界的突破。作者将其归结为五个方面的表现,分别体现在信徒的知性、情感、意志、能力和品格上。<15>
在此图景之下,作者进一步勾画出为善去恶的关键性动力,即是对圣灵进驻人的心灵的具体行动的展开。借用佛教禅宗的词汇表达,作者指出圣灵带来的变化既可以是当下和直接的(顿),也可以是长期和逐步的(渐)。 在“顿”的方面,圣灵会作为当下的超然外力来直接抗衡信徒行恶的意愿,并推动其行善的意愿。在“渐”的方面,圣灵会对信徒内在品格进行逐步的转化和完善,进而扭转其本性。作者此处的创见集中在提炼出“他者介入”、“他者在场”、“他者相遇”、和“他者指点”四种典型场景及其相对应的修养方式。在具体讨论中,作者肯定了儒、道、佛三大传统修养功夫中的深刻之处,但同时也清晰指出,对儒家关于人性本善的信念,道家对自然全善和人性本真的预设,以及佛家将无住、无执作为生命终极圆满境界的立场,基督教的道德情操与实践都应有所保留。
综上所述,温的文化神学立场鲜明反映在其圣经论、基督论和救赎论中。他极为重视圣经是神启示人与自己相遇的全备记录和最高标准,同时对十架神学有深切的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将中华福音神学的领域进一步扩展至圣灵基督论光照下的华人文化与伦理议题,并添加进实存体验的元素使其神学立场更加包容和圆融。可以说,从宗教经验出发展开基督教神学论述,是温人生经历孕育出来的富有中国色彩的生命学问,由此为当代汉语神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代的温伟耀便怀有上述强烈的中国宣教情怀,曾参与赵天恩在香港创立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协助赵编辑期刊《中国与教会》。在牛津学成后的温返回香港中神任教,也是为了在后方训练合适的宣教士进入中国。上世纪末,温开始在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讲授“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课程,同时创建“当代基督宗教教学资源中心”,每年定期邀请中国大陆学者来港研究和收集资料,终于有机会为大陆学者提供神学训练和研究资源。在回顾自己早年参与汉语神学运动的经历时,温坦言曾因“传教意识太强”而遇到挫折,随后便做出深刻调整:
跟着我知道,事情不是靠硬销就能做到,于是开始和他们对话,认识他们,和他们做朋友,分享人生信仰经验。我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这班站在中国高等教育课室的人,他们讲解基督教时,我只要求讲得正确,也希望讲得正面。做到这两点,我就很满足。至于他个人是否成为教徒,是他的选择,也是上帝自己的安排。…… 我和这些学者要做交心的朋友,不是要为向他们传教,而是爱他们,希望将自己最好的东西──自己的学识和人生体会──和他们分享,其中一定包括基督教,因为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在我的人生里面,最宝贵的是基督教。<16>
在访谈的尾声,温重申自己所有工作意义在于将福音信息阐释得“正面正确”,可视作其贯彻始终的文化使命的生动概括:
以前人们很喜欢发展一个伟大的神学系统,我倒觉得,若需要给世界留下什么,大概不是这些。若我能将信仰里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清清楚楚讲明白,有板有眼而合理有说服力,“正面正确”的,我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贡献。我希望以后的人记得温伟耀,就是记得这些。……我只是昙花一现,我最好能做到的是帮助这班老师“正面正确”,我就觉得够了。这是我常说的《提摩太后书》二章2节的讲法,能帮助那些教导别人的人。我的目标是这样。<17>
三、立足于人生境界的汉语伦理神学
罗秉祥(1954—),生于香港,香港浸信会会友,资深基督教伦理学家,长期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并领导该校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在宗教伦理与宗教对话方面建树丰硕。与温伟耀同道的罗也是汉语神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与温颇具中国情怀的文化使命不同,罗选择投身汉语神学运动,更多是为了回应大陆宗教热现象,特别是大陆学界发出的“马其顿的呼声”。在其1995年挑起“文化基督徒”争论的檄文中,罗直陈拘泥于现状的香港神学界需要面对若干危机,其中之一便是“未能把握时机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做宣教工作”。作者反省道,
香港神学界这几十年来培养及储备了那么多一流神学人才,难道只是为了香港教会和散居海外的香港信徒?也不为了中国?在九七年后香港已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知识界中的基督教文化热,难道与我们不相干?<18>
若要化危机为转机,罗秉祥提出积极面向神州,争取机会在大陆讲学、交流和出版。这其中,实践文化宣教的关键,是利用好大学宗教系和研究中心的学术平台,透过分析和诠释性的学术工作,参与中华文化的建设。<19> 在研究实践中,罗自己继承了以往汉学家对儒家宗教向度的强调,立足于人生境界提升的伦理神学立场,重新确立耶儒对话的出发点,并发展出对古今儒家的宗教与伦理向度的批判论述。下文重点解读罗借此推进汉语神学的具体方案。
运用中国传统与现代有关人生境界的思维方式,罗秉祥展开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对话,以便为方兴未艾的汉语神学运动奠定福音基调。他富有洞见地指出,生命提升的问题是基督教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共通之处。但与向着理想人格方向前进的儒释道径路不同,基督教的思维方式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后者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是由人与上帝的关系来揭示,而不是按人的本体来揭示。因此,人的生命的提升根本上是人的关系的提升,而非人格的提升。他进一步解释道,基督教传统下的人观大体从五个方面探讨神人关系,即(1)人是受造物;(2)人是上帝的形象;(3)人是堕落远离上帝;(4)人蒙上帝拯救;以及(5)人神无隔。 基督教历代思想家大多认同,人生命的提升唯有透过神人关系的改进来进行。
基督教人学指出生命提升的目标是活出上帝的形象。尽管人下堕沉沦,但透过基督的拯救与恩典,人得以肖似基督,效法基督的爱,并因此可以肖似上帝,与上帝有密切及亲切关系,生命便愈得以提升。人神之间非但不隔绝,而且是可以心灵和应;神人融通无隔,因此神人不二。<20>
在梳理基督教教义与伦理脉络过程中,罗秉祥特别强调人的生命提升的动力是在基督耶稣里。基督教传统下的成圣生活,关注的是上帝拯救工作的延续,是人的生命不断接受上帝医治,其新生命继续成长与成熟的过程。这其中更新的关键是他力,而非现代新儒家强调的自力。后者假定人性中有绝对充沛的内在资源,只要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生命自可提升至化境。这种自力改良的高言大义,在罗看来容易将道德理想流于虚幻层面,却没有正视具体现实人生的种种限制。为了纠正这种流弊,他主张借鉴基督新教卫理神学和东正教的洞见,即一方面坚持上帝是超越于人的上帝,人是有限定的受造物;另一方面也肯定在基督里的新人,其生命提升的极致是分享到上帝的道德属性,尽管人的本质与上帝的本质迥然不同。简言之,神人关系正是一种不一(本质层面),也不二(能力层面)的辩证关系。
将“不一不二”确定为耶儒对话的新起点,是罗秉祥从事跨文化宗教对话的重要案例,<21> 其灵感来自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刘述先(1934—2016)提出的天人不一不二说。罗进而从“本然”、“实然”、“应然”三个角度对此加以把握,提出从“本然”角度看,新儒家一直强调在本体层面人与天一;从“实然”角度看,新儒家也承认现实生活中人天为二;从“应然”角度看,新儒家则鼓励人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使人恢复与天同一。在罗看来,刘的突破在于为天人关系中设置了一个双重应然规范,即从应然层面主张人既要往天的境界提升,但又必须保持距离,不应僭越。
罗随后借用这一洞察来呼应基督教传统的伦理著述中长久被忽略的一个关键议题,就是神对人之爱及信徒对他人之爱,彼此之间具有一种既连贯(continuous)又断裂(discontinuous)的微妙关系。这种“相即不离”的关系可以拓展为两个命题:其一,信徒以爱待人及信徒要效法上帝或基督,这两个道德主题相互关联;其二,上帝及基督有其不可为人效法之处,对于这些方面信徒对他人的爱既不能也不应效法上帝及基督对世人的爱。<22> 换言之,耶稣基督不但是信徒爱的典范,也是其爱的限制。对此,作者解释说:
因为按基督教信仰,只有耶稣才是基督,“基督事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不能重复。我们对耶稣爱的效法,只能适可而止;若是有所逾越,我们便是以自己为基督,或扮演基督了。尽管我们在爱中要酷像上帝(“上帝形象”之动态表现),但却不能扮演上帝。<23>
在纵论马丁·路德、路易斯(C. S. Lewis,1898—1963)、虞格仁(Anders Nygren,1890—1978)等人在此论题上的创见后,罗总结道,基督教伦理学的境界论有两项要务,既要鼓励人在内心修养及待人接物上效法上帝,但同时也要提醒人不要扮演上帝,指挥历史乾坤。这种意义上的人与上帝或基督的不一不二辩证关系,与刘述先所主张的天人不一不二辩证关系是相通的,二者皆肯定了人生境界中人与终极者的二元辩证关系。一方面,人与终极者不二,因此人不应当自暴自弃,而是要超拔自己的生命,向终极者接近;另一方面,人与终极者不一,人的超拔不可傲慢而入魔,自以为上帝或天。新儒家与基督教,尽管对不一不二的程度与形态论说不尽相同,也各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但可以互相观摩,彼此借鉴,进而将各自的传统演绎得更精彩。
罗秉祥在跨文化宗教对话领域的另一个创见,出自对朱子儒家伦理与礼仪的挖掘。得益于钱穆等人的研究积累,罗进一步梳理朱子仁学主张的要点,提出若干重要的见解。首先,仁是人道和天道、人心和天心,透过仁可窥见“天人两界之诚为一体”。换言之,仁具有宗教本体论的意涵。第二,仁是“生之性”,作为天地心生化万物,作为人之心生化德行。第三,与此相关的,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仁导致爱,而非如孔子所言仁即爱。最后,人要法天,人之仁须与天之仁契合,此即朱子所谓“吾人之心即天地之心”。<24> 罗据此认为,对比上述基督教关于爱的伦理的两个命题,可见朱子的仁学在法天方面有充分论述,但忽视甚至排斥人之仁与天之仁可能有断裂,因此天的外在超越维度难以在朱子的天人关系中确立。
众所周知,朱熹是宋明新儒家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但除了少数学者之外,中外学界朱熹的研究者们大多忽略其思想中的宗教维度。罗秉祥在秦家懿和陈荣捷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就朱熹的《家礼》一书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家礼》中包含着明确的宗教情怀,而这种宗教情怀在原则上与基督教的宗教情怀不相冲突,且有互通之处。<25> 具体而言,罗发现整部《家礼》中祠堂及祖先均扮演了重要角色,相比之下祭祖只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据此,罗推断朱熹编修《家礼》是希望能培养人对祖先“爱敬”、“崇爱敬”、有“谨终追远之心”和“报本反始之心”,而这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宗教情怀。儒家对祖先的敬爱建立在对自身的血脉根源的深切怀念基础上,这种出于报恩之情的尊敬与基督教中对于造物主的感恩赞美类似,但不是常被西方宣教士误读的祖先崇拜或伦理风俗。简言之,儒家礼仪,正如很多其他宗教礼仪一样,既有宗教维度,也有道德维度。这样的儒礼传统有必要在现代华人社会复兴,来对抗日益迷信化的民间祭祖趋势,也可激发基督教传统在神学之外的礼仪上进行更多本色化尝试。
上述列举的成果,虽没有囊括罗所擅长的道德哲学和社会伦理方面,但已凸显出其满怀文化宣教使命的伦理神学建树。可以说,罗对身处传统神学院之外从事神学活动有着清晰的理解。这一方面体现在其活跃于大陆地区的高校及学术会议,积极推动耶儒对话延伸至伦理领域,借此拉近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与基督宗教的距离,同时为神学关怀加添上伦理维度。笔者赞同徐济时的评价,罗作为基督教伦理学家在此发挥出独特的作用。<26> 另一方面,通过与西方伦理著作和自身文化传统的对话,罗也自觉扮演起与温伟耀相似的承前启后的文化工作者角色。这是因为文化思想的演变具有其连贯性,因此,为了建设新的中华文化,学术工作的目标便需要继往开来,在古今中西的对话中实现继承与创新。
四、结论
文化宣教的目标是要让基督的真理进入文化领域,使圣经的世界观向固有的或世俗的世界观挑战,透过彼此之间不断的互动与对话,叫世人的心思意念转变而归向神。对文化宣教的实践者而言,文化使命奠基于福音使命,而后者也须配合文化使命的进行。因此文化宣教需要二者兼顾,才具备改变世界的潜力。在其广为引用的新作中,福音派学者亨特(James D. Hunter)将这种改变世界的方式称为“信实的同在(faithful presence)”,那是上帝在其道成肉身中实现了圣言(the Word)与世界(the world)独特的联系,在其中上帝自己追寻并与受造的罪人认同,最终通过牺牲之爱为其提供更新生命的确据与盼望。当新约作者们称呼上帝为“以马内利(God with us)”时,所要传递的正是上述含义。<27>
本文提供的两个案例,不仅展现了前辈学人在参与汉语神学运动过程中积累的思想成果与实践智慧,更反映他们从事文化宣教事工背后的深层关怀,即见证并效法基督在思想与文化领域中信实的同在。具体而言,无论是出于心系神州的宣教使命,还是忠实回应来自大陆的马其顿呼声,两位基督徒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走进汉语神学界,与从事相关研究的各种学者进行开放、真诚、平等且持久的交流。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主动参与了与中华传统与宗教的对话,并开始努力阐释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观念与取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他们能够正视与不同宗教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学者进行对话,将对同一处境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教会信徒的世界观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文化宣教所倡导的有效工作方式观之,温伟耀与罗秉祥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意识地将汉语神学作为见证基督信仰真理活动的学术空间,将关涉中华文化意识深层结构的议题作为神学反思和对话的起点,并将塑造汉语神学的研究路径作为实践中的策略性目标。这是因为二人在宣讲基督教真理与信仰时,都非常注意学术受众本身的意识形态、世界观、语词的含义等因素。因此在实践文化宣教时,便尽可能用对方能够理解的理性方式加以表达,同时努力争取听者的尊重与信赖。正如亨特所总结的,信实的同在要求我们在各自影响的领域中竭力塑造工作与关系的模式,帮助其他参与者见证基督的典范。<28> 二人十余年的投入与著述已充分验证了上述卓有成效的文化宣教理念与实践方案。
文化宣教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事业,其中不乏各样的困阻与争战。在华人文化中,至今仍然可以发现许多权势及其意识形态阻挡着人们认识神并接受福音。二十世纪的大陆经过革命的共产主义以及传统中国哲学复苏的洗礼,知识分子对于基督信仰难免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在过去十年间,威权政体治下的思想空间被大幅压缩,汉语人文学界的主流逐渐被政治话语分割与裹挟,与此同时文化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并开始大举排斥外来文化与宗教的影响。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现实,成长中的新一代汉语神学学人和文化宣教的实践者,有待回应上帝在重重阻力与艰难之下发出的文化挑战,并由此见证他跨越时代局限而亘古常新的福音使命。
<1>杨熙楠,“总监的话”,载《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讯》第1期,2004年,第20页。
<2>何光沪,“究天人之际:汉语神学运动的大历史、大悖论与大趋势”,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44期,2016年,第182—183页。
<3>杨熙楠,“复刊辞”,载《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1期,1994年,第8—9页。
<4>卓新平,“‘汉语神学’之我见”,载何光沪、杨熙楠编,《汉语神学读本》,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7年,第340页。
<5>参见孙毅,“神学言说与人文学进路”;章雪富,“言说之道和上帝之道——兼论基督教神学的本质”;陈雅倩,“学园与教会:基督教学人及其困惑”,均收入《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五辑第二册,2006年,第195—226页。
<6>刘小枫,《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第60、62—63页。
<7>罗民威,“十年磨剑——温伟耀(上)”《时代论坛》第1183期,2010年5月2日。
<8>在此基础上,温提出了一系列汉语神学正视与中国民族性及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相遇所应考虑的神学课题:第一,宗教的存在意义——安身立命(自我超越)抑或与上帝和好(关系性)?第二,在强调伦理意识的文化语境中如何理解因信称义的救赎教义?第三,在多元宗教文化语境中如何确定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与普遍性?第四,灵界是否就只有圣灵或邪灵?超自然的领域是否也有中性力量的存在?第五,生命提升与修养的自力与他力,并论上帝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第六,宗教经验的结构性分别,抑或境界性的自我超越与对话性的有情相遇。参见温伟耀,《生命的转化与超拔——我的基督宗教汉语神学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29—35页。
<9>温伟耀,“神作为一位有情意的无限他者”,载卢龙光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1年,第113—149页。
<10>温伟耀,“作为跨文化的‘汉语神学’”,载卓新平、许志伟编,《基督宗教研究(第十四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383—395页。
<11>同上,第87—92页。
<12>同上,第136页。参见倪柝声,《属灵人》(中),台北:福音书房,1999年,第87—88页。
<13>同系列的其他作品分别是《是否真有神的存在?》(2012年)、《上帝与人间的苦难》(2013年)、《为什么要我信耶稣?》(2014年)和《今生·来世》(2016年)。《成圣、成仙、成佛、成人》是该系列丛书的第四本。
<14>温伟耀,《成圣、成仙、成佛、成人:正视人的高贵与邪恶》,香港:明风,2015年,第142—143页。
<15>同上,第145—146页。
<16>罗民威,“十年磨剑——温伟耀(下)”《时代论坛》第1184期,2010年5月9日。
<17>同上。
<18>罗秉祥,“中国亚波罗与香港神学界之九七危机”,《时代论坛》第419期,1995年9月。
<19>罗秉祥,“大学还能出什么好的神学吗?” 载罗秉祥、姜丕盛编,《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年,第373—389页。在这方面,罗秉祥团队与大陆学人互动的代表成果包括:罗秉祥、赵敦华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罗秉祥、姜丕盛主编,《基督宗教思想与21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罗秉祥、万俊人主编,《宗教与道德之关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罗秉祥、谢文郁主编,《耶儒对谈:问题在哪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罗秉祥,“人生境界的汉语神学”,载何光沪、杨熙楠主编,《汉语神学读本》(下),香港:道风书社,2009年,第556页。
<21>罗秉祥,“‘不一不二’作为耶儒对话的新起点”,载黄冠闵编,《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宗教传统:多元对话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0年,第267—292页。
<22>罗在他处更详细地说明了“爱的断裂”的四种表现,分别是:(1)基督爱不值得爱的人,并赋予他们价值;门徒爱不值得爱的人,但不能进一步赋予他们价值;(2)基督的爱是普世的、救赎性的;门徒的爱只是包容性的,不能扩展到普世并产生救赎;(3)基督能以爱宽恕,包括赦罪;门徒对人的宽恕无赦罪成分;(4)基督牺牲的爱是为人代死;门徒为人牺牲却不能代死。参见罗秉祥,“爱与效法——对话及诠释性的神学伦理学”,载《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35期,2003年7月,第67—96页。
<23>同上,第285页。
<24>参见罗秉祥,“爱与效法”,第81—84页;罗秉祥,“论儒家的‘仁’主题及融合作为基本题旨的仁,及神爱与仁结合的处境神学之前景和问题——与尼格仁对话”,载罗明嘉、黄保罗主编,《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25>罗秉祥,“朱子《家礼》之宗教意涵与礼仪之争”,载《耶儒对谈:问题在哪里?(下)》,第589—616页;另见“Confucian Rites of Passag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Zhu Xi’s Family Rituals”, In David Solomon, Ping-Cheung Lo and Ruiping Fan (eds), Ritual and the Moral Life: Reclaiming the Tra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2), 119-142。
<26>梁燕城、徐济时,《中国文化处境的神学反思——中华福音神学人物研究》,本拿比:文化更新研究中心,2012年,第237页。
<27> James Hunter,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Irony, Tragedy, and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1-243.
<28>同上,第254页。
(作者为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学者)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1期的主题是“时代变局中的基督徒知识人·民国初年”,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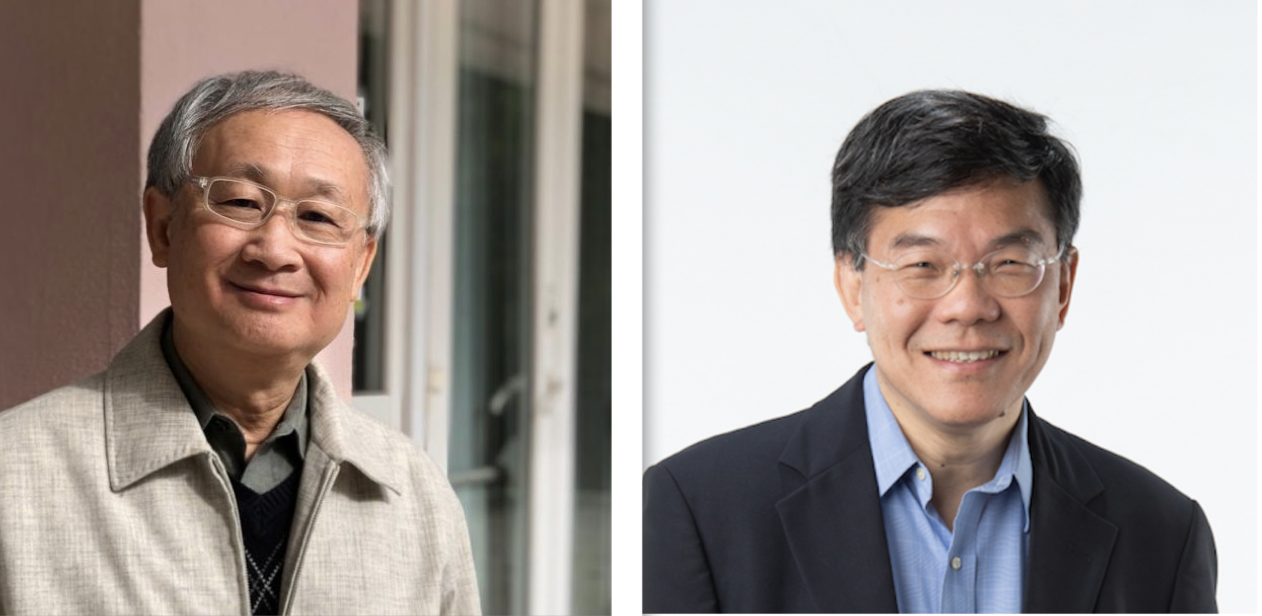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