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https://www.ustiendao.com/22788196.html]
公元1世纪,基督信仰开始在希腊文化圈中传播的时候,非常得益于《约翰福音》中所使用的“道”(Logos)这个概念。约翰用这个当时在希腊哲学中流行的“道”,来表达在永恒中就存在的圣子。这在当时新兴的基督教与流行的希腊文化之间建立了一个连接点,为之后几个世纪的神学家,在“道成肉身”的基础上建构适应当时希腊文化的“本土神学”,架设了无可替代的桥梁。
进入现代,当基督信仰在华语文化圈中传播的时候,是否可以找到其与中华文化的连接点,好让使用华语的人们,能够用这种语言来思想神学层面的问题呢?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能够看到的一个线索就是,无论在“礼仪之争”的时期,还是后来基督新教传入中国,都发生过是否可以用中国传统的“上帝”一词来指称圣经中的那位神的争论。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场争论似乎已经过去。更多的人开始认同用中国本土的“上帝”一词,来指称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那位上帝。如果这是基督信仰与中华文化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连接点的话,这对本土化的神学思考意味着什么?
近来在思想这方面问题的时候,读到温伟耀老师的《成圣、成仙、成佛、成人:正视人的高贵与丑恶》这本书。单从书名中将成圣、成仙、成佛与成人并列,就似乎预设了人在基督信仰中所追求的目标,与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可比性,这给人带来强烈的兴趣与期待:或许可以从这本书的视角,借着讨论与评论作者在这本书中的观点,可以对上述那个大问题稍有一点触及,即来看一下基督信仰在中华文化中的连接点具体地体现为什么。
一
温伟耀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曾以研究北宋儒学的论文获得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他在这本书中说,他多年来的心愿就是“要把中国文化在人格修养上的贡献和成就,清楚和精彩地陈述出来。”<1> 他之所以格外重视宋以来儒学的工夫论,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精神文化一直以来的兴趣,主要不是在于外在客观宇宙的探索,而是对于人内心世界的探索,重心落在人生体验的反思和智慧……中国文化传统的大动脉和成就,并非在于科学,而是落在人生的智慧和道德实践的探讨。”<2>
作者认为,中国精神文化传统对人生智慧的寻求所取得的成就,不只是体现在儒家对“成圣”的追求上,同时也体现在道家对“成仙”的追求、佛家对“成佛”的追求上。“这一切的追寻,都是人生最高境界的体验和实践……是对人性、人生的善良、高贵、优美方面的深度理解、反省和实践。”<3>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在对“成圣”、“成仙”、“成佛”分别给予具体阐释后,得出结论说:“这些对人生体验和修养的深度探索,我们可以说是人类精神文明最正面、或许也是最高度的成就。”<4> 相信作者行文中的这几个“最”字的使用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作者将中国传统中这几种寻求并列起来,不仅给予充分肯定,并且随后与基督信仰所追求的“成人”加以对照时,背后其实有一个预设,即无论是儒家所追求的“成圣”、道家所追求的“成仙”、佛家所追求的“成佛”,还是基督信仰所追求的“成人”,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或者至少具有可比较的相似处。既然前三者所追求的是人类精神文明最正面及最高度的成就,自然也应该或可以是基督信仰所追求的目标。
我们可以稍微来思想一下这个预设。这个预设是说,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从各自的角度,既知道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同时也有很强的愿望要去追求这个终极的目标。从儒家的角度来举例,将这个目标看作具有终极含义,是因为其来自于终极性的“天”、“道”(自然)或者“理”。天道或者天理既是有目的的,人所领受的天命或追求成圣的境界自然也是有目的的。在这个方面,赵紫宸先生(1888—1979)在概括中华文化的特点时,也十分强调这种目的性:“自然自有鹄的,就是要成己成物。天地实在不是一个死东西;乃是在‘成’的历程中,人在其中得以清澈地了解,尽量地努力,去完成自然的目标,达到自然的鹄的。”<5> 用儒家的表述,即“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6> 这成为人生最终的目标。
如果我们将上述的终极目的用今天更熟悉的概念“善”或者“真理”来替代,那么站在基督信仰的角度,将人目前乃是生活在亚当堕落之后这个因素加进来,对于上述的预设,我们似乎就可以提出下述的问题:1)生活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下,在没有所谓特别启示的光照下,人真有可能知道那个具有终极性的“善”或“真理”是什么吗?2)人真有将这种“善”或“真理”当作人生的某种终极目的来追求的渴望吗?
二
思考上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在什么层面上来理解上述问题中的“善”或“真理”。温伟耀老师在本书中没有直接用“终极”或“真理”这些词,但他确实用了“善”来阐释他想要表达的含义。
在上述预设之下,作者在本书中对于人性做了两点重要肯定。对作者来说,这两点肯定无疑适用于本书所论及的儒家、道家、佛教与基督教,因此是人性普遍的特征。
首先,作者认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仍有判断善、恶的能力,这种能力并没有消失,也不会因此而被质疑。”<7> 作者同时肯定人性的这种判断能力具有普遍性,“善(goodness)和恶(evil)的意识,却肯定在任何人的身上,或者任何民族之中存在。”<8>
其次,作者认为,“第二个对人性积极而正面的肯定是:无论如何,在道德信念(moral belief)上,我们始终是相信:人应该行善,而不行恶。”<9> 既然是人应该行善,那么善就应该是人所愿意或追求的目标。
这两点肯定,作者在表述上是限定在道德的层面上,不过随后在将这种善当作是“成圣”、“成仙”与“成佛”的追求目标时,其实是超过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层面,而具有某种“宗教”层面的含义。在对这三家之所“成”的目标的阐释中,作者几次使用从道德层面“翻上一层”的表述,而使其所追求的善的目标,不再停留在我们一般理解的“道德”层面。比如对儒家来说,“儒家说,从道德的自觉翻上一层,就能知道有天理运行在自己的内心。”<10> 可见,无论是本书作者,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自身,在道德与宗教,或者道德与更上层的形而上层面,实际具有某种连续性,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道德”与“宗教”层面的划分。
正是在对“善”的这种广义理解下,即所说的善同时具有“道德”与“宗教”含义的理解下,作者将他对人性的这种积极理解,用在了与基督教的比较中。其中在对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人性观有所肯定的同时,将基督教中对人性的极端负面的看法,归咎为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我们要承认,在基督新教的开创者(如路德、加尔文)的神学观点中,都让人看见他们对人性带有非常悲观、甚至近乎绝望的观点。”<11> 在作者看来,这种观点对后世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深受这种对人性悲观、负面的看法所影响,以致我们可以看见,在基督新教的传统里,若提到人性可以有行善的能力时,都会产生一种禁忌式的反应。”<12> 本书作者浸润基督信仰多年,相信他所说的都是出于某种切身的体验。
如果要为改教家们做一点辩护的话,改教家们对此问题的回答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区分属灵(属天)事物与属世(属地)事物,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与“宗教”层面。路德在将事物区别为“较低的事情”(the lower things)与灵性的事物(spiritual things)的前提下,认为堕落后的理智只能领会前一类的事情,或者与前一类事情相关的善与真理。<13> 加尔文的做法也一样,“为了清楚发现人在任何事上理解的程度如何,我们必须在此做区分,即对世俗之事的理解,以及对天上之事的理解。”<14> 在此区别的基础上,加尔文明确说明,人们在这些所谓“世俗之事”或地上的事物,其中包括政府(政治)、家政、道德、科技、文学与艺术等领域,表现的还是非常卓越,值得肯定的。<15> 在这个层面的行善能力及其结果,用普遍恩典的观念看,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无疑是被加尔文所肯定的。改教家们所否定的,只是人因为堕落的原因,所做的善行对于达到终极的善(即与上帝相关的属灵领域)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这种观点并非来自于改教家自己。无论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都是奥古斯丁的追随者。加尔文自己就认为他的这种划分来自奥古斯丁:“我也承认神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奥古斯丁的这个论点,即人的自然秉赋已因罪而败坏,超自然的恩赐已完全丧失。”<16> 其实奥古斯丁自己说的比改教家们表达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除了犯罪之外,一无用处。”<17> 这样看来,本书对中世纪天主教传统的肯定,对于人性的看法,也并不只有作者所肯定的阿奎那这一支的传统,同时还存在着更早的奥古斯丁这一支的传统。对人性及其成圣追求的看法在这两种传统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张力。
当然,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原本对人性看法的那种张力在基督新教中不再存在。我们这些宗教改革家的后裔们,深受上述两个领域之划分的影响,以致我们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思考中国先贤所追求的那种可以用广义的“善”所表达出来的“成圣”目标时,难以作出更为恰当的把握。这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基督徒所应该反思的。确实,这种“善”已经超过了改教家们所做的那种区别,不仅具有“世俗之事”层面上的道德含义,同时具有“天上之事”层面上的宗教含义。如果拿去改教家们所做出的这种区别,我们当如何看人对这种广义“善”的认识与追求呢?
三
上述的问题,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更具体地表述出来就是,在没有特殊启示的光照之下,人是否会对那种终极(属灵层面)的善或真理有所认识(至少知道这个目标)?人是否有真实的渴望想要去追求这种层面上的善或真理,将其当作一生追求的成圣目标?
我们就拿作者在书中特别摘文进行批评的加尔文的论述来看这个问题。其实仔细地看加尔文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可以让后人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加尔文将人具有的“上帝形象”置于人有其不朽的灵魂。人堕落后,理解力与意志作为灵魂的主要官能,在“上帝形象”受损却依然残存的前提下,两者之官能也就依然存在。对于“天上之事”的属灵领域,加尔文还是认为,就算是人的理解力在堕落之后已经受到影响而变得残缺不全,但“理解力是人辨别善恶和明白是非的一种机能,它就不可能完全丧失。”<18> 换言之,其受损的功用并不只限于在“地上之事”发挥功用,在“天上之事”中也还依然发挥某种程度的功用,这就是人的理性中仍然存在的那丝灵光:“在人败坏和堕落的本性中仍存有一丝光芒。这光亮证明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与禽兽有别。”<19> 这意味他在表达,堕落后的理性依然在某种程度可以分辨具有终极含义的善恶。当然对他来说,这种光亮实在有限,“当这光芒散发时却被极浓厚的愚昧掩盖了,以致无法明亮地照耀。”<20>
对于第二个问题,加尔文同样有某种程度的肯定:“在人的本性中有某种与生俱来寻求真理的欲望,这就表示人曾经尝过真理,否则他根本不会有这种渴望。”<21> 这意味着他在表达,堕落后的意志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有追求那真理的渴望。他在这里所说人“曾经尝过真理”,并不是在柏拉图回忆说的意义上这样讲(虽然他很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而是就亚当在堕落前拥有在上帝看为好的人性,以及与作为真理的上帝有美好的相处来讲的。不过,同样,加尔文也指出这种渴望的脆弱性,“这种对真理的渴慕在它尚未发挥之前,就衰残并落入虚妄中。”<22>
简言之,对于上面所提到的那两个问题,加尔文基本上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种肯定的回答意味着:无论在哪种文化背景中,就算是把人堕落的因素加进来,人们依然对那终极的善及真理有某种认识,并且对其有一种渴望与追求。如果对于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追求的人性所“成”之目标,与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那么,回到我们在引言中所提到的那个问题,这种共同性的基础就是,中国远古中所说的那位“上帝”,无论后来被用“天”“道”还是“理”所替代,确实可以指称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那位上帝。<23> 换言之,提供了这种共同的善与真理之目标的那位上帝是同一位上帝。
朋霍费尔(1906—1945)在其未完成的《伦理学》手稿中,反思了基督新教神学在“自然的”问题上所显出的不足,即对自然世界之有机性或目的性认识不足。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自然世界日益失去其与终极实在的关联,而变成人手中可以认识、改造或操控的对象。虽然这种观念的源头不一定是来自改教家们,但后来处在启蒙运动处境下的基督新教,难免会受其影响,使得改教家们在两个领域的区分变成自然世界(世俗层面)与其终极实在(属灵层面)的脱离。
中国传统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其借助于“天”、“道”或“理”所彰显出的自然世界的有机性及目的性,在朋霍费尔那里一样可以得到说明。在他看来,在亚当堕落之后,被造的世界变成了自然的世界(包括人及其精神),即在自然法的意义上拥有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规律性与目的性。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朋霍费尔将这种“自然性”视作亚当堕落后被上帝保存下来的自然形式:“自然的是上帝替堕落的世界保存的生命形象,这个形象对准基督带来的称义、解救与更新。”<24> 说明这个被上帝保存的自然世界,一方面具有某种生命机体的特征(生命形象),有其自身的法则和动力机制,指向某个终极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在耶稣基督没有将这个终极目的向人们指明之前,自然世界的生命形象所指向的那个终极对象或目的,无论被称之为善、真理还是别的什么,就只具有“形式”的意义。<25> 就像是古老的修道院墙壁上的一幅图画,因为年久失修,只能让人隐约地看到图画的轮廓,以及某些局部存留的色彩,无论人走远还是走近来仔细查看,都无法更清楚地看清图画的内容,直等到真正知道这幅画作内容的那个人来,才可能将这幅图画修复出来。
这种具有消极性及形式化特点的善或真理,或许可以借保罗在亚略巴古的讲道来帮助我们理解:“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徒17:23)这里所谓“不认识而敬拜的”那个对象或目标,就是这里所说的那种“形式的”善,或许也是温伟耀老师这本书中所说的古代先贤修身养性所致力于追求的那个善、那个目标。
<1>温伟耀,《成圣、成仙、成佛、成人:正视人的高贵与丑恶》,香港:明风出版,2015年,第33页。
<2>同上,第35页。
<3>同上,第37页。
<4>同上,第87页。
<5>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见林荣洪编,《近代华人神学文献》,香港:天道书楼,1986年,第429页。
<6>《中庸》22章。
<7>温伟耀,《成圣、成仙、成佛、成人:正视人的高贵与丑恶》,第6页。
<8>同上,第7页。
<9>同上,第11页。
<10>同上,第42页。
<11>同上,第26页。
<12>同上,第28页。
<13> Luther, the sermon on Exodus, 18, W. A. 16, p. 354; the commentary on John I, 8, W. A. 46, p. 587.
<14>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I,2,13。中译文见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基督教要义》,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2017年重印)。除特别标明,本书中《要义》的引文均出自此中文译本,下面只标出《要义》的卷、章与节数。
<15>《要义》II,2,13。
<16>《要义》II,2,12。参见Augustine, On Nature and Grace 3. 3; 19. 21; 20. 22 (MPL 44. 249, 256 f.; tr. NPNF V. 122, 127 f.)。
<17> Augustine, On 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 5, 译文引自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
<18>《要义》II,2,12。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同上。
<23>如译名之争所论及的,这里只涉及到“神(God)”之名,即《创世记》14:18论及麦基洗德时所说的“至高神”,而不涉及到“雅威(Lord)”之名。
<24>朋霍费尔,《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1页。
<25>这里的“形式”是相对于“内容”而言。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0期的主题是“时代变局中的基督徒知识人·晚清”,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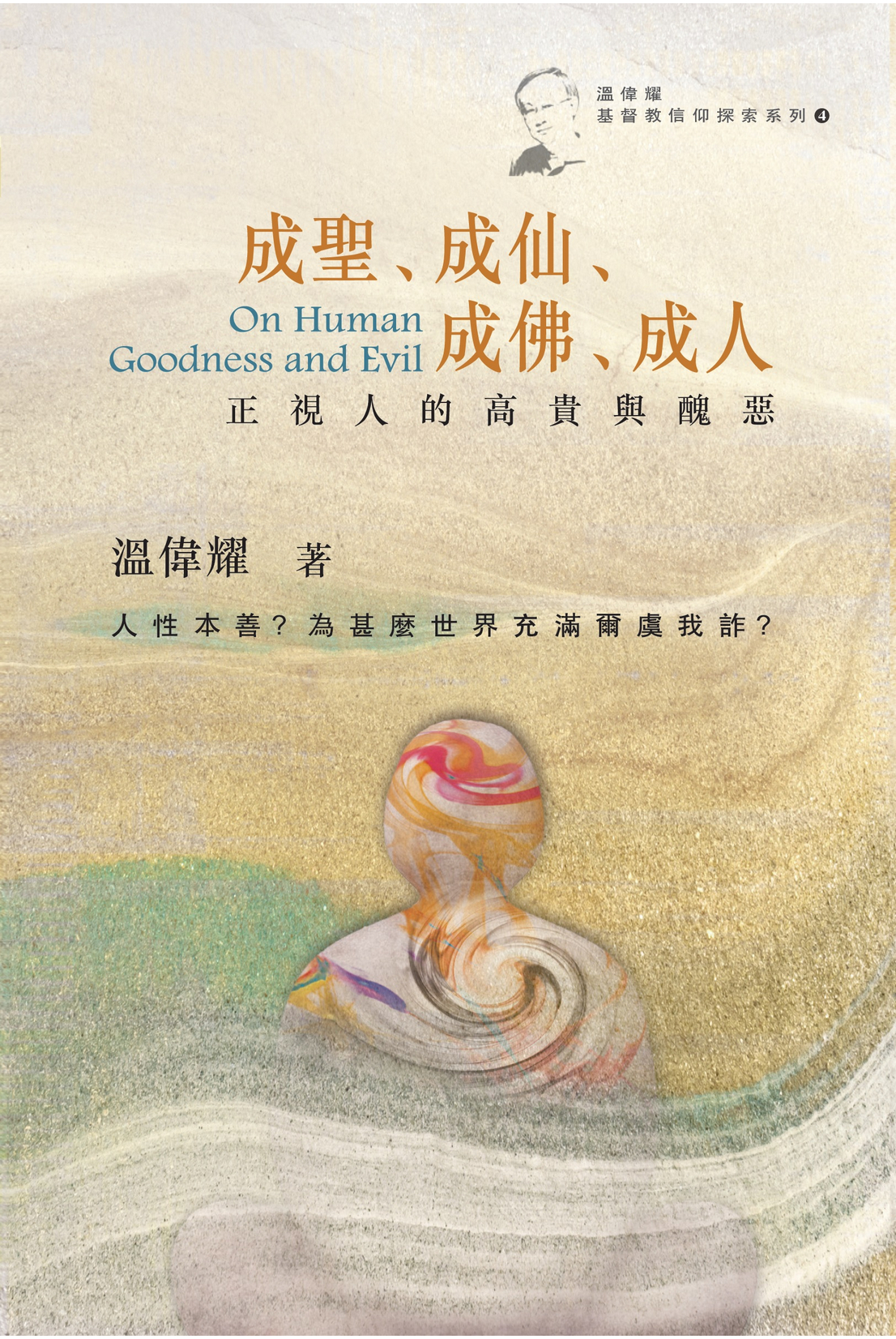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