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受过教育的人是点着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借着烛光行走。这在中国可能比在大多数异教国家更为真实。——狄考文
引言
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1916—2007)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曾如此评价1920年代初的宗教问题讨论:“非宗教人士广泛引用西方思想家的有关言论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其中主要是来自英国、法国、俄国思想家的思想言论”。在列举一连串具体人名后,作者总结道:“他们争论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观点、理由,几乎就是过去三四百年间西方所进行的有关宗教的争论的重复。”<1> 其实,早在非基督教运动爆发近半个世纪之前,美北长老会来华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就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类似情形的出现。
他在1877年5月于上海召开的第一届来华宣教士大会上,竭力为教会办学辩护,断言西方怀疑主义进入中国的日子不会太遥远:“休谟和伏尔泰的背教学说,施特劳斯和勒南破坏性的(圣经)批判,一定会在中国再次出现。”“科学要么是宗教的盟友,要么是其最危险的敌人。”<2> 狄考文进而指出,要抵挡这些攻击,在不信者面前为真道辩护,教会就要提供更高层次的教育,培养出在知识、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能与本地士绅一较短长的教会领袖。这样的教会领袖对外可以护教,对内有能力抵挡异教迷信。除了为教会输送人才,教会学校还可为国家育才,培养一批受过教育的教师、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和技师等“利世有用之士”,他们将引领涌入中国的西学潮流,为福音在中国的推展扫清障碍。<3>
事实上,狄考文本人创办登州文会馆,就寄望经过数年教育“造就”之后,毕业生都能“无愧称为有学之士”。他们要在知识结构上超过传统儒生,而且要像儒家传统教育培养出的“君子”那样,在道德教养上成为百姓的表率,所谓“风动草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些“有学之士”的特别之处在于,尽管他们可以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upward mobility),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却不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晋升为功名社会中的官绅为人生目标,也超越同一时期通商口岸英华书院所培养的翻译买办阶层功利的价值追求。与其他教会学校相比,文会馆毕业生多半投身教会教育,从事牧职,或受聘官办学堂,他们对近代中国一系列自强、改良和革命的参与,特别是对20世纪初中国本土自立教会的建立与坚固,确实表明狄考文当初的教育远见与卓识。<4>
这样的“有学之士”,就其游走于教会与社会、福音与文化而言,与今天方兴未艾的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期待的将来毕业生——具备整全的世界观,具有通识、修辞和护教的能力,预备在各个领域服侍、更新文化——有类似之处。故此,本文尝试梳理狄考文创办登州文会馆期间的教育理念和目标,考察承载实现这一教育理念与目标的课程设置,以期对今天的教会办学提供某些借鉴。
一、转向教育
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伴随基督新教来华而出现。1818年10月,意识到在中国传教将是一项长期工作的马礼逊,与助手米怜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目的是“交互教育中西文学,以促进基督福音的传播”。书院不仅教授汉语,也教华人英语和西方科学。然而,作为新教宣教士来华创立的第一所学校,它所体现的超越福音传播,沟通中西文化的宽阔视野,并没有因为清廷在1842年开放通商口岸后得以延续。相反,开埠后的最初十年,教会学校基本上被宣教士当做赢得皈依者、培养华人助手和牧师的场所,作为宣教规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
之所以如此,除了宣教士自身的神学背景和个人经历之外,可以推想一旦教禁松弛,宣教士可以合法踏足中土,他们自然会将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福音布道,对教会学校的定位通常情况下只是传福音的手段,少有文化媒介的功能。这种情况甚至在1860年清廷增加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之初也无甚大的改变。在这种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大多数教会学校最初靠提供免费食宿甚至给学生家长钱财来招生,因此学生多来自社会底层,教师由宣教士兼任,学校规模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基本停留在小学水平,教学内容主要是圣经、中国经典和少量西方史地知识。办学主要是宣教士的个人行为,尚未引起差会和宣教士的普遍重视。另一方面,教会学校的开办也是宣教士适应本土环境的结果。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被列为第二批通商口岸的登州,曾经吸引数以百计的外国宣教士,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有重视教育、尊重学者的传统,因此在宣教工作之初就注重学校教育,希望借此打开宣教局面,这“对于孔子的故乡山东来说是非常适合的”。持这种观点的宣教士中最突出的一位,就是被称为美北长老会在山东宣教事业“三大先驱”之一的狄考文。<6>
狄考文在选择以宣教士为终身职业之前,曾有一年时间主理宾州的比弗学院(Beaver Academy),治校颇有成效。<7> 这一经历部分解释了他为何刚到登州(今蓬莱)不到3个月,就希望在当地创办一所教会学校。新学校蒙养学堂于当年9月份开学,但最初十年间校务主要是由狄考文的妻子狄邦就烈(Julia Brown Mateer,1837—1898)一人负责。事实上狄考文最初并不真的看重学校的价值,他相信自己将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布道和传福音。<8> 就像他那一代来华的美国宣教士林乐知(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1836—1907)和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1841—1913)那样,只是在向当地人布道受挫之后,狄考文才开始全身心投入学校教育。这与成长于19世纪后期受学生志愿运动影响的那一代来华宣教士不同。后者大多倾向社会福音,来华之初就抱着以基督教教育、医疗服务来变革中国这样的理想,最终成为把美国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传统引入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媒介。<9>
学堂开办十年,前景依然暗淡。招不到合格的本地基督徒教师,学生家长不顾约定让子女中途退学,生源质量差。“及开学九载,计收生徒九十一人,不堪造就者十之九,其效用于教会者仅一人耳。”此外,学堂中伤风败德之事时有耳闻,如学生霸凌、敲诈,伙房与学生串联监守自盗、放高利贷、吸鸦片、醉酒、鸡奸、懒惰、贪食、撒谎等等。很少有人看好这间教会学校的未来。<10>
决心投身教育的狄考文从三方面着手对学校加以整顿:放弃过去重量不重质的招生政策,从基督徒家庭中挑选新生(但不排斥非信徒学生),逐步收费,一改过去学堂单纯的慈善性质;进行课程改革,提高教学水平;严格治校。此外还推动学生、中西教师三方的沟通连结,密切学校与家庭的关系,形成信仰核心圈,提升学堂的信仰和道德氛围。此后,学堂注册入学人数从1874年的22人上升到1876年的34人,1880年有45人,1882年达到70人。学堂声誉日隆,生源质量较以往大为提高,而且报名人数继续增加,学校不得不扩建校舍,仍然不能满足需要。<11>
1877年2月,狄考文为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三位毕业生做了精彩演讲,给现场来宾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狄考文回想这一幕仍然充满深情:“不管其他人如何评价他们,对我和狄邦就烈来说,他们都非常宝贵。”<12> 这三位毕业生不但是他们夫妇多年的心血结晶,证明他们数年辛劳的成功,也向社会和广大宣教士揭示教育蕴含的巨大能量。也正是在同一年,学堂正式采用“文会馆”一名,由原先的登州男子高等学堂升格为大学,并在1884年获美北长老会总部认可,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13>
二、为教会办学辩护
然而,狄考文的办学成绩并不能打消多数宣教士对教会办学的疑虑。确实,1877年,西方来华宣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已达347所,在校学生5917人。但与其说是对传道方法的研究,不如说是中国处境的现实,首先促使宣教士办学,但学校作为传福音手段的工具价值也越来越受人质疑。从1838年到1877年,西方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是国家的责任,因而是世俗工作,宣教士的使命是传福音,教育在很多人看来不属于宣教事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创刊10年来(1868—1877)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两篇涉及教育话题,也从侧面反映来华宣教士对教育议题的忽视。随着从事教育的宣教士与从事福音传播的宣教士之间出现鸿沟,教育宣教士常常需要为教育工作的合法性辩护,重申教育工作的宣教目标。<14>
187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宣教士大会,就为狄考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辩护平台。
他在大会上宣读了题为“新教差会与教育之关系”的文章,目的是承认教育在宣教事业上地位虽低于布道,但仍有其重要的合法地位。狄考文先从理论层面说明基督教与教育有“天然的亲和性”,并引用初代教父都是博学之士的例子证明知识是基督教的“天然同盟”。故此,他反对教会学校单单以引人归主为唯一目的,轻忽教育本身的价值,为了让孩童归信仅仅开设宗教课程,远远不能培养合乎主用的、合格的教会人才。在他看来,真正的教会人才,要有能力履行福音“大使命”,也就是破坏福音对象中的异教主义,让基督信仰和道德渗透进整个社会结构。
他把教会事工比作军队打仗。军队的目标不是尽可能多地杀伐,而是征服敌人。组织一支有效的军队,数量不是唯一主要的考量,质量、操练和指挥才干同样重要。同样,对教会来说,成员数量的增长不是唯一目的,质量和资质同样重要。而要实现教会质量的提高,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对年轻人的教育,“要在智力、道德和宗教方面教育学生,使其不但归信,而且在归信之后成为上帝手中有用的器皿,捍卫和推进真理的事业”。这一教育目标贯穿文会馆办学活动始终。<15>
具体到中国处境,狄考文认为教会办学不但可为教会供应可信赖的本地牧师,向教会学校提供师资,还可以向社会输送掌握西学知识、从事各种世俗职业的人才。后者将把西方先进的教育和现代文明的科学艺术引入中国,这不但可促进中国的物质进步,也能根除传统中国社会的迷信,有利于宣教事业在华推展。借助掌握西方科学知识,这些基督徒毕业生能够与当地乡绅对话,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对内可辨识异教,维护纯正福音,对外可应对有学问之人的怀疑主义,捍卫福音真道,从而促进中国本土教会的自立。最后,狄考文指出这样的教会学校不能停留在小学阶段,应当是大学(college)水平,自然科学应当是学校的主干课程,而且学生要来自基督徒家庭,教会学校要逐渐实现收费自立,同一地区同级学校要联合办学。<16>
狄考文这篇辩护文赋予“大使命”文化征服的色彩,可能会令今人感到不安,但另一方面,他的教育目标背后蕴含的教育理念,却又带有当时西方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教育特征,并作为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组成部分为今人所提及。<17> 只是碍于该文的目的是要论证教育是宣教工作的合法分支,这一教育理念才没有得以充分展开。此外,狄文提到的培养本土牧师、教会自立、联合办学等目标,都是20世纪初中国教会耳熟能详的议题。然而,这种带有先知性的声音,在1877年的宣教士大会上应者寥寥。13位参与讨论的宣教士中,只有4人与狄考文的主张一致或相近。质疑教会办学的人中,有的认为狄考文过于强调教育的地位,有的不相信教授科学等世俗学问能预备人心接受基督,还有的害怕教育取代宗教会带来危险。美国公理会来华宣教士谢卫楼直言不讳地指出,世俗教育本身不会领人靠近基督,学习西方科学的人比异教徒更难被福音触及。或许令狄考文稍感安慰的是,大会成立了益智书会(“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着手为教会学校编撰“优秀和适合的教科书”,这标志着来华宣教士在中国本土开办的各类教会学校,一改以往各自为政的状态,转而加强彼此联结。<18>
三、教育理念
如果说像狄考文这样主张教会办学的宣教士,在1877年的上海大会上还要为教会学校的合法性辩护,那么13年后的第二次来华宣教士大会则是另一番景象。人们对教会学校的普遍看法,用福州美以美会来华宣教士李承恩(Rev. N.J. Plumb)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无需为教会学校辩护。它们一直以来是传播福音的得力机构”。此时的谢卫楼在这次大会上用类似13年前狄考文的口吻,肯定教会办学的重要性:如果教会要培养一批在知识和道德修养方面与宣教士看齐的教会领袖,要让“基督徒担负有影响、负责任的职位,诸如政府官员、西学教师、医生、商人,以及在中国已经开始的伟大社会变革的领导者,那么教会必须主动开展教育工作”。<19>
与上一届大会相比,本届大会召开时,全国教会学校注册学生人数增长了1.8倍,达到16,836人,而达到大学水平的教会学校也不再是文会馆一家独秀,还包括北京的汇文大学、通州的华北协和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20> 狄考文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也由13年前说明差会与教育的关系,变成教育如何最为充分地推动在华基督教事业。换句话说,教育议题已经由合法性问题(why)变成方法论问题(how),但以宣教为导向的教育定位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狄考文将他在文会馆25年的办学实践,总结为三方面经验,可以说这也是对他教育理念的一次梳理。简言之,第一是实行“全面教育”(thorough education);其次是主张用中文教学,不开设英文课;最后是在强烈的宗教影响氛围中开展教育。由于最后两项涉及具体的课程教学,留待下文详解。这里先来看第一项。所谓全面教育,指的是“要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真理有比较好的了解,接受这种教育需要10到14年的时间”。在这里,全面教育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学习内容广泛,建立以中国经典、西方自然科学和基督教教义为主干的课程体系,二是学校规格提高,不仅有基础教育的小学,还有进行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中学和大学。<21>
狄考文提出全面教育这一教学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其他教会学校和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认识。他批评教会学校专授宗教教义而不顾其余是“完全邪恶的”。教会教育不能局限于此,而应增加对已归信的学生施以智力和道德方面的训练,“预备其将来做社会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教会中成为教师和领袖”。这一教育目标与上一届大会上的表述基本相同。他观察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参加科举获得功名,由此步入仕途,因而课程局限于背诵和解释儒家经典,练习作文,却忽视培养推理反思能力;没能教授有用的现代学科知识,而是局限于儒家经典,因循守旧,不鼓励创新,不利于思维能力的健康发展。按照狄考文的标准,标榜培养“君子”理想人格的传统教育(偶像崇拜内容和科举制主导的学风)也没能很好地培养人的道德意识。<22>
因此,“全面教育”首先表现为学习内容之“全”,这就要求狭隘的教会教育除了宗教教育,还应增加儒家经典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狄考文也以同样的标准建议中国传统教育要进行课程方面的改革,也即除了儒家经典之外,还要包括1)主要科目如算术、地理等等,其次是2)自然科学,最后是3)一些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第一类是为了提高普通人的智力,解放其思想;第二类通过教授真正有用的知识,启发和增广人的思想;第三类是为了均衡发展人的心智才干,促其独立思考和行动。<23>
按照狄考文的设计,接受全面教育大概需要10到14年的时间,如果在当地私塾有些基础预备则可相应缩短学时。文会馆1891年开示的章程标明,备馆和正馆学制加起来也要9年,多于同期的上海中西书院(8年)和福州鹤龄英华书院(6年)。狄考文的解释是,全面教育所需的这些时间,足以在学生的心灵和性格上烙下宗教印记。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福音布道和个人谈话的模塑所取得的效果,是短期学制不可能做到的。这是从宗教教育的角度言之,从文会馆课程学习的要求来说——“每一门课程都以彻底学好为目的,每一个学生,除非他的才能证明他成了一名真正的学者,是不能毕业的”,较为长期的学习时间也是必要的。<24>
当然,狄考文也看到了全面教育的实际好处,除了前文提到的毕业生掌握自然科学知识有利于消除迷信,加之熟悉中国儒家经典,能在地方上与士绅竞争影响力之外,全面教育向学生及其家长也展现了良好的就业前景。因为宣教事工在中国日益增长,中国向西学逐步开放,都会为接受全面教育的学生们将来提供用武之地。<25>
其实,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全面教育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避免教育的专业化和功利化,提倡思想解放,通过普通的文化修养课程来促进人的智力、道德和身体等多方面的发展。这种教育理念在19世纪成为西方教育界的主流思想,影响了一批包括狄考文在内的晚清来华传教士。他们据此为教会学校设定的教育目标就是在智力、道德和宗教方面训练学生,使其将来成为“有学之士”,在社会和教会中发挥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把教会大学形象地比作中国的“西点军校”。未来的军官和指挥官在此受训,预备将来成为社会领袖。<26>
四、课程设置
围绕全面教育和培养“有学之士”,狄考文为文会馆设置了一系列课程,这些课程主要分为传统儒家经典、西方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三大类。此种课程分类并非狄考文首创,而最初见于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及后来的马礼逊学堂,并在1890年代成为宣教士来华所设教会学校的标准课程类型,只是不同的学校在具体的学科设置和课时比重上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从侧面也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教育理念及其目标。<27> 狄考文在1896年5月于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教育会“三年会议”中,根据他在文会馆30多年的教学管理经验,认为中国教会学校最宜开设六类课程,分别是语言、地理、历史、数学、科学和宗教(基督教)。限于篇幅,下文结合文会馆课程列表,对这六类课程中的语言、科学和宗教课程作一述评。<28>
1、语言
狄考文认为,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能用母语流利准确地读写是基本条件。为此,他修正了13年前对中国传统教育几乎全盘否定的做法,转而接受背诵经典的传统教学法,只是要求教师在学生背诵经典时加以讲解。在他看来,传统经典是汉语文学风格的典范,单词和短语的意义及用法离不开它们在经典中的使用情况。因此,学好中文完全要靠熟悉经典。外国人很少能用中文写出好文章,大多是缺乏背诵经典之故。也就是说,文会馆开设儒家经典课程,不同于传统经学教育道德和形而上的追求及培养传统士大夫的教育目标,其最基本的目的是为教会学生提供中国语言文字的教育和训练。<29>
因此,文会馆特别重视背诵传统儒家经典和练习写文章,要求学生每天都要背诵,特别重视对经典加以解释。馆中正备两斋9年,每年都有儒家经典课程。如备斋前两年念《诗经》,讲解《孟子》,第三年念《书经》第一、二册,讲解《大学》、《中庸》,正斋6年学习四书五经、诗赋,作文。从备斋第三年到正斋第五年,每周作文课要写一篇文章,临毕业当年每周两篇。其目的一是为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做预备,但主要还是因为能写好文章、熟悉儒家经典,才能赢得当地人的尊重,有资格成为学者。
针对有人认为儒家经典包含异教色彩,因而反对教会学校教授儒家经典,狄考文的答复是,基督教历史上,希腊拉丁文献的异教色彩比儒家经典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在基督教学校自由教授。“防止儒家经典谬误的最佳办法不是忽略之,毕竟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在一位明智的基督徒教师的指导下加以研究。”然而事实上,学堂开办之初延聘当地儒生基督徒教授儒学经典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中文老师无力分辨调和,甚至诋毁学堂和基督教义,多被狄考文辞退。此外,狄考文预见到将来官话会取代文理,也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用官话写文章。他本人不但花了25年时间编写《官话类编》,为来华宣教士学习汉语提供帮助,还主持了圣经新约官话和合本的翻译。<30>
截至1895年卸任文会馆监督一职,狄考文始终坚持文会馆用中文教学,反对开设英文课,这使文会馆在19世纪末同期的教会学校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担心来教会学校学英文的学生,大多以学英语为寻找高薪职业的敲门砖,一旦有机会就提前离校,而且他们往往被吸引到通商口岸从事外贸工作,非但对自己的同胞失去影响力,还会在那样的商业环境中变得道德败坏,追求奢侈享受,生活习惯和信念洋化。狄考文并不想让文会馆培养此类买办阶层,他希望自己的学生掌握好本国语言,成为合格的学者和牧师,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间,不但保存和坚固其道德品行,更能发挥影响力。在他看来,中英文同时开设的主张不切实际,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时间。学习中国经典和文学要花费数年时间,再加上西文和科学,所需时间要翻倍。此外,学习英语几乎总是以牺牲年轻人对母语文学及其风格的品味为代价。他认为最好是中文学好后再开始学英文。
狄考文对教会学校英文教育不留情面的批评,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自然遭到反对者的强烈抵制。标榜“中西并重”、教授儒家经典和英文的上海中西书院、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的与会代表就对狄考文给出的理由不以为然。直到20世纪初,宣教士还在就教会学校的双语模式展开激烈辩论。1904年,文会馆迁到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开办的广德书院并入广文学堂后,始设英文选修课。<31>
值得一提的是,狄考文观察到“中国教学之道,独重笔下之文章,不重口中之谈论”,不知口传胜于笔写,“言辞更要于文辞”,加之缺乏公共集会,不重视公开演讲,因此疏于口语训练。而基督教常有布道,鼓励公开讨论,教会学校因而通常训练公共演说的艺术。因此他格外重视组织辩论会(literary society)来训练学生口才。辩论会是文会馆成立最早的学生自治团体,每周六下午开展活动,每个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要按次序参加辩论,教师则充当评论员和裁判。辩论会不但训练学生的写作和演讲口才,也锻炼学生的团体合作能力,培养责任心,“凡诸生少年负办事之名者,无不得力于斯会”。<32>
2、科学
狄考文所要造就的“有学之士”,不是仅仅停留在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更是要在学识(知识结构)、影响力上与传统儒生竞争,最终取而代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掌握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将来涌入中国的西学浪潮之领头羊。因此,他理想中的教会学校,自然科学自然要在课程设置中占有突出位置。他相信科学可以帮助中国人破除传统迷信,进而为福音传播扫清障碍,同时也给中国带来物质进步。当然,更为直接的好处是,教会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能够在追求西学的中国获得声誉,精于西方自然科学的毕业生将来容易在洋务企业谋得职位。
但作为宣教士的狄考文在教会学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不单单是看重其实用价值和实际好处,他所超越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地方,在于赋予自然科学以神学意义,将之从“用”的层面提升到形而上的层次。狄考文不认为科学与基督教有冲突,相反,“所有真理彼此相关,历史和科学与宗教有许多关联点”,具体而言就是,“精神与物质的真正科学,事实上不过是对上帝未成文律法的揭示”。在这一点上,狄考文的真理观与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非常相似。他甚至认为正如初代教会上帝赐给教会行神迹的能力,见证福音,如今,“在圣灵的直接启示之下”,上帝赐给教会科学,以赢得人们的关注,为福音预备道路。因此,教会学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就不单单是从自身得失着眼,而是“上帝的命令”。何况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与科学联姻,已经证明科学在对抗异教主义方面的巨大优势,这足以启发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教会,抓住洋务运动期间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声誉日隆的大好时机有所作为,以免科学被敌挡信仰的势力用来攻击教会。<33>
狄考文设置的科学课程除了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和矿物学、生理学等格致之学之外,还包括精神和道德哲学(性理)、政治经济学。而格致之学在科学课程中所占比重最大。如物理学在正斋第三、四年开设,内容包括水力学、气体力学、声学、热学、磁学、光学、电学。化学在正斋第五年开设,包括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地质学和矿物学在正斋第四年开设,生理学则放在正斋第三年。这些格致之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教材基本上根据外国教材编译,辅以实验、仪器和模型开展教学。狄考文深知必须有仪器设备才能教好自然科学,向学生和更多的人展示自然科学的规律及其实用价值。为此,除了向外国订购机器设备和实验仪器之外,他还利用假期到各大工厂参观学习,掌握操作技术,又充分发挥自己在机械制作方面的天赋,自学仪器制造,在学校设立研制所仿造教学仪器,不但满足学校自用,“全国各地学校都来定制”。在这个过程中,狄考文还培养了学生丁立璜,帮助其开设理化器械制造厂,专门生产教学仪器供应全国需要。<34>
3、宗教
上文提及,全面教育的理念要求在知识、道德和宗教上对学生施教,因此,教会学校固然不能以领人归主为唯一目的,也不能办成只是培养教会工人的神学训练机构,但其信仰特质要求它与私立学校和官办学校区分开来,开设宗教课程。也就是说,宗教课程在教会学校不存在合法性问题,问题是宗教课程所占的比重和形式。对此,狄考文首先提醒在教宗教课时要注意宗教与其他科目的平衡,不要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教会学校完全以教宗教为目的,其他科目不过是幌子。与此同时,也不要让学生误以为宗教只是知识的学习,这样的学生不理解宗教真正的精义不在乎头脑,而是心灵,这正是许多学生毕业离校后丢弃基督徒品格的原因。<35>
狄考文特别强调让学生参与教会在主日进行的各项宗教活动,比如阅读和背诵圣经、布道、上主日学和查经班等等。他相信这些课堂之外的信仰学习和操练,可以在人的心灵和良心上留下信仰的印记。在学校的宗教课程设置方面,狄考文建议小学阶段主要是背诵,熟记基督教版的《三字经》、《耶稣教问答官话》,《马太福音》、《约翰福音》、部分《诗篇》等圣经篇章,包括《天道溯源》、《天路历程》等信仰书籍,只是要求在背诵时教师应加以讲解。与小学相比,中学和学院阶段的宗教授课不那么重视背诵,而是要让学生熟悉圣经,对教义有综合全面的认识,所读书目包括《新旧约圣经历史》、《天路历程》、《圣经地理》、《天道溯源》、《救世之妙》、《自然神学和道德科学》等等。尽管有这些课程安排,狄考文并不把全部希望放在课堂,而是认为要让学生的心灵和品格烙上基督信仰的印记,主要还是靠参加主日的布道、教师的言传身教和学校整体的精神氛围。<36>
宗教课程在文会馆正备两斋中虽然占有突出位置,每年均有开设,但其实所占课程比重并不比儒家经典和数理化科目高。文会馆之所以能保持浓厚的宗教氛围,主要是把信仰操练安排进学生每天的生活中。比如按照文会馆的规条,每个学生周间要参加早上八点的早祷会和晚上八点的晚祷会、周三晚上七点半的祷告会。每逢主日,上午学生聚集祷告,然后分成小班,由教习带领读经,再一起参加十一点在讲堂的集体敬拜。下午三点上主日学,晚上八点再分成小班,检查上午的听道情况。文会馆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主日信仰活动,但不强迫未信教的学生入教。此外又成立学生自治宗教组织如传道会、赞扬福音会、勉励会、青年会等。文会馆日后多有毕业生从事牧职,多赖此类社团之功。比如被称为“中国慕迪”的布道家丁立美,在文会馆读书期间于学生勉励会及传道会“效力特多,且为会中之中坚份子”,加上品学兼优,好学勤谨,深得狄考文夫妇器重,尤其是得狄邦就烈栽培劝导,“遂成为狄师母之爱徒”。丁立美日后成为民国著名的布道家,狄氏对其影响颇大。<37>
这些课外活动拉近了师生关系,学生从老师那里看到活出来的信仰,生命影响生命,越发追求属灵成长,文会馆的宗教氛围就越发浓厚,就越能抵挡世俗化潮流。事实上,在狄考文看来,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开展的教育,最能推动基督教在华的宣教事业。“总之,宗教影响在一所学校中占主导地位就是一切。有之则未来可期,无之则学校变为无用,如果不是更糟的话。”文会馆毕业生无论入馆之前是否信主,毕业时“从未有不皈依基督者”,且“颇能洁身自好,过着清教徒的严谨的生活”,多半在教会学校教书或从事牧职,不能不说是学校浓厚的宗教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38>
为了造就“有学之士”,除了所开设的语言、科学和宗教三类课程之外,地理可以启蒙人心,开阔视野,历史(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让中国人明白中国过去和现在于万国中的真正位置,数学则可以培养中国传统教育忽视的推理分析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文会馆为学生提供的音乐教育。主其事的狄邦就烈认为音乐“可以训练唱圣诗,培养和表达年轻人的纯真之乐,可以使沉闷的生活充满生机和快乐,培育爱国主义和真正的英勇精神”等等,故而引入西方乐理知识,教学生视唱作曲,并出版《乐法启蒙》(1872年初版,1892年出版修订本《圣诗谱》)。她将许多中国民间曲调改编为赞美诗,同时也意识到西方音乐进入中国必然要根据本地文化做出调整。“如此伟大的民族有权拥有自己的音乐风格,只是其中应有生命和成长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文会馆学生谱曲作词的诗歌中,其中有乐赴天城的渴慕、春日赏花的惬意,还有呼吁中国变革富强,“光复青岛威海卫,奉还旅顺大连湾”的爱国情怀。<39>
五、余论
狄考文反对无知是敬虔之母,因此提倡全面教育,在知识、道德和信仰方面培养学生,“凡按课程学毕,业经考准者,即为有学之士”。简言之,就是培养敬虔和有学识的中国人。为了实现这样的办学目标,文会馆除了开设儒家经典、西方科学和基督教课程,鼓励学生参加自治社团之外,尤其注重对学校严格管理,比如对礼拜、寝务、课堂(如课时、考课)、放假、禁令、赏罚都有明确规定,严格执行。<40>
当然,没有经费的支持,学校就无从谈起。文会馆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北长老会差会总部的拨款,但相当一部分来自差会总部之外的募款。狄考文联系当年神学院的同学,如今母国教会的牧师们,向他们通报文会馆的情况和需要,特别是个别学生的需要,结果成功收到这些教会主日学的认捐。1874年狄考文转向教育之后开始逐步要求学生家长负担学生在校期间部分费用,直到1895年狄考文卸任文会馆监督,文会馆仍然实行学费免费,只要求学生负担衣物、寝具和书本等费用,并且坚持不教英语。他非常警惕教会学校以追求自立(self-support)为名,迎合学生需要,开设比如英语等具有商业价值的课程,这样固然可以多招学生多收学费,但代价却是教会学校的宗教色彩淡化,为了适应市场越来越走向世俗化。这方面的例子比如上海的中西书院和圣约翰大学。<41>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教会学校的办学模式,均源于西方教育思想,比起传统教育,其先进性表现在:真正实现大众教育、职业教育和全面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实行分科、分班和分级教学,注重培养思维能力和实验教学,这比传统教育围绕科举应试只重背诵更符合教育规律。随着19世纪后半期洋务运动的发展和维新运动的兴起,在师夷长技和变法图强的时代潮流中,转眼看西方的中国人越来越注意到传统教育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独立的教育制度,可以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中发挥某种“示范”作用。1901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上奏清廷,拟聘文会馆监督赫士为山东大学堂总教习。赫士率馆内师生十余人来济,以文会馆典章为蓝本,草拟大学堂运行办法,该办法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学章程。文会馆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示范”地位于此可见。<42> 当然,宗教教育的“示范”除外。
对于今天处于探索阶段的基督教教育,如果以培养敬虔而有学识之下一代为办学目标,那么狄考文在文会馆的办学实践至少可以提供以下几点经验作参考:
比如,将宗教教育放在整个教育规划中的突出位置,培育学校浓厚的宗教氛围。将基督信仰融入包括课堂在内的学生日常生活中,尤其注重主日敬拜及其他教会活动对信仰的操练,使信仰不单影响学生的头脑,也塑造其心灵。其次,由于学校规模小,师生同住校园,教会学校师生多有接触,教师一般来说能与学生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进而发挥影响力。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教会学校的突出优势。第三,避免教会学校世俗化,但不要走向与世隔绝的极端。文会馆开设儒家经典课程,注重背诵和讲解,固然是进行基本的语文教育,其实也含有对当时科举教育制度的某种妥协,尽管当时不少来华宣教士对科举考试多有诟病。<43>另外就是严格治校。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虽然肯定文会馆的办学经验值得今天的基督教教育借鉴,但并非忽视其存在的问题和时代背景。比如,文会馆的全面教育就并非那么“全面”,最明显的是课程设置中没有体育一项,要到1904年文会馆迁到潍县并入广文学堂后始设体操课(体形学)。<44>另外,全面教育过于突出“全”也会存在一些弊端。比如文会馆号称“欲学者洞识各种要学”,“将天下至要之学汇聚于兹,取以文会友之意也”,“总集天下学问之大要,以备造就英才”,其实取法于现代西方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分科教学,强调专业之分而不见学科知识的融贯。对于世俗大学来说这似乎不成问题<45>,但对于教会学校或者基督教大学来说,如何处理宗教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特别是能否用基督教世界观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就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文会馆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经验(或者是没有留下相关资料?)。作为中国传统教育变革的“示范”,教会学校及其毕业生曾经在主流社会的地位自不待言,甚至在19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教会学校依然保持着中国教育近代化“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46>。相比之下,今天的基督教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挑战要复杂和严峻得多,或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将在这个社会不那么显眼的地带继续向下扎根,为将来的世代培育新一代的“有学之士”。
<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陈永明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第310—311页。其实,这份名单不应省略非宗教人士所乐于传诵的金句“宗教是人群的鸦片”之作者马克思。见萧子升等,《非宗教论》,非宗教大同盟出版,1922年,第29页。不少研究也揭示了近代西方各种思想流派和“主义”对20世纪20年代反教人士的影响。如Tatsuro and Sumiko Yamamoto,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22-1927,” i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2, No. 2 (Feb., 1953), 133-147; 叶嘉炽,“宗教与中国民族主义——民初知识分子反教思想的学理基础”,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第106—128页;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3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77页;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VI、86—87、92页。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法国政教分离思想的援引,见张宗文,“教育与宗教”,收入《无所谓宗教》,1922年8月法国印行,传播品,出版者不详,第37—44页;李璜,“法国教育与宗教分离之经过——其用意及其效果”,见《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1925年。
<2> C.W.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RGC), 1877: 177-178;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London & M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75-182, 特别是第180页。
<3> RGC, 1877: 177-178;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80;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58—60页。
<4>“有学之士”,引自“文会学馆文凭”,郭大松、杜学霞编译,《登州文会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以下简称《登州文会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页。儒家传统培养“君子”的理想,见李弘祺,《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86—587页。文会馆毕业生“阶层跃升”及对本土教会的扶持,见Daniel H. Bays,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iley-Blackwell, 2012), 94-95。据统计,自1864年到1895年,也就是狄考文卸任文会馆监督的这一年,文会馆注册学生共300人,有80人毕业,其中60余人受雇为牧师、医生、传道人(evangelists)、教会学校教师等等,毕业生供不应求。见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Fryer (Shanghai: 1895), 17,28。19世纪末,清政府开办的新式学堂向文会馆毕业生敞开大门,特别欢迎长于自然科学的毕业生。1897年初,狄考文曾记载文会馆有12名毕业生获聘丁韪良任职的京师大学堂,除了一位之外,大学堂所有西学年轻老师均毕业于文会馆,见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London & Edinburge: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62。文会馆毕业生的特别之处及参与辛亥革命,见李铁,“培育‘新士’:狄考文与近代中国教育”,《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3期,2013年5月;李日,“登州文会馆与辛亥革命”,《山东高等教育》2015年第1期,第75—81页;张子清,“丁牧师略述”,见谢扶雅编,《丁立美牧师纪念册》,广学会出版,1939年,第38页。对中国本土教会特别是基要派影响甚大的文会馆毕业生,除了毕业于1892年的丁立美外,还有毕业于1901年的贾玉铭。正是贾玉铭在1922年秋担任华北神学院辨惑学讲席期间,批判当时流行于教会内部的“新神学”(其中包括圣经高等批判)和当时走偏的“中国化”教会。贾的课堂讲义后来整理出版,被文会馆第二任监督、也是贾在文会馆的老师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 1857—1944)视为从中国人视角写的护教著作。见贾玉铭,《新辨惑》,南京灵光报社,1930年。贾玉铭对1920年代初期“中国化”教会的批判,见拙文,“‘枉道而媚人’——贾玉铭论‘中国化’教会”,《世代》第16期,第11—33页。丁贾两人均追随赫士任教华北神学院。华神对中国教会自立和本土化的推动,见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2008年,第157—164页。
<5>Robert Morrison, “Anglo-Chinese College Deed.”, https://digital.soas.ac.uk/AA00001481/00002?search=anglo-chinese+=college+=deed ; Ching Su,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in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7.3 (2021): 207-231; 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28页;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香港:道风书社,2009年,第230—231页。
<6>陶飞亚,“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101—108页;John J. Heeren, On the Shantung Front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40), 226;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39. 认识到可以利用中国人重视教育这一传统来办学辅教的来华宣教士,还有1877年被选为主教的施约瑟,他向母会呼吁在中国建立教会大学。理由是教育曾被很好地用来传播基督教,西方如此,东方亦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书籍和教育的地方,更有必要。他在后来回忆回国募款筹建圣约翰学院时说:“我相信接触中国人的最佳办法就是借助教育,原因有二:首先,中国人是有知识的民族;其次,在所有国家中他们或许最重视教育的价值。”见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N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5; “Bishop Schereschewsky’s account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llege.” In The St. John’s Dragon Flag 1907: 13(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s, Record Group 11, St. John’s University, Box 239: 3944. Yale Divinity Library)。
<7> 丹尼尔·W·费舍,《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以下简称《狄考文传》),关志远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History of the Class of 1857, Jefferson College (1886), 50。
<8> 《狄考文传》,第20—21、80页;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40; Charles Hodge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10、12。
<9> 贝奈特,《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金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29页;Roberto Paterno, “Devello Z. 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 in Kwang-Ching Liu eds.,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66), 48-52; Clifton J. Philips,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s, 1886-1920,” in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91-110; Terrill E. Lautz, “The SV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in Daniel H. Bays and Ellen Widmer ed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19;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以下简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88—89页;Leping Mou, “The Liberal Arts Curriculum in China’s Former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 9 (2020): 25-46。
<10>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62-164;《登州文会馆》,第51页;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72-82.
<11>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66-175;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第45—49页;The Presbyterian Monthly Record, V.33, 1882: 349。
<12> 《狄考文传》,第90—92页;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76; The Church at home and abroad, v.5 (1889), 424。
<13> 《登州文会馆》,第25、197页;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75; 郭大松等主编,《文惠天下——登州文会馆与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学术研讨会论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141—145页。
<14> 对1877年教会学校和学生人数的统计,不包括主日学及其学生人数。见RGC, 1877: 486; Alice Henrietta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46), 18;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
<15> RGC, 1877: 172; 狄考文对教会学校培养目标的类似表述,还可见RGC, 1890: 457;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EAC), held at Shanghai, May 6-9. 1896: 54。1895年之后接替狄考文担任文会馆监督的赫士,在学校培养目标上也与狄考文一致。见W. M. Hayes, “The Aim of a Christian School in China,” in EAC, 1899: 60-66。
<16> RGC, 1877: 171-180;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79-180;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376页。
<17> RGC, 1877: 172;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113页;张亚群,《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95—196页。
<18> RGC, 1877: 196-203;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80-181; Roberto Paterno, “Devello Z. 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52; Alice Henrietta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18;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三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6页; C. W. Mateer, “School Books for China,” in Chinese Recorder (CR), Vol.8., 1877: 427-432。
<19> RGC, 1890: 447, 475-476; 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20> 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380、123页;Kwang-Ching Liu, “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0, No.1 (Nov., 1960): 72。
<21> RGC, 1890: 457;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第60页。
<22> RGC, 1890: 457; RGC, 1877: 172; C. W. Mateer, “Chinese Education,” in CR, Vol.14, 1883: 463-469.另见狄考文,“振兴学校论”(选录),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07—211页。谢卫楼对传统儒家教育的批评,比如偶像崇拜、缺乏道德品质的坚实基础等等,与狄考文的批评类似(见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26—34页)。倪维思也批评了中国教育体制过分强调背诵经典,却阻碍和打击了思想的自由表达和创新能力(见倪维思,《中国和中国人》,崔丽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7—39页)。
<23> CR, 1883: 463-469.
<24> RGC, 1890: 457-458;《登州文会馆》,第9、28—31页;周愚文,“晚清林乐知在华教育事业与美国教育的引介”,《教育研究集刊》第66辑第3期,2020年9月,第88页;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212—214页。
<25> 按照狄考文的估计,接受过全面教育的毕业生,其出路在他们的亲友看来也是不错的,比如他可以在各种教会学校教书,在教会谋职(比如当助手或传道人evangelist),预备学习神学日后牧会,给有钱人家的子弟教科学和数学,或者自己办学授课等等。(RGC, 1890: 460)
<26>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第112—114页;RGC, 1890: 497。
<27> Ching Su,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225; Ryan Dunch, “Science, Religion, and the Classics i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to 1920,” Daniel H. Bays and Ellen Widmer ed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1-63; 张伟保,《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4—79页。
<28> C. W. Mateer, “What is the best Course of Study for a Mission School in China,” in EAC, 1896: 48-55.
<29> EAC, 1896: 49-51; CR, 1883: 464;胡卫清,“晚清基督教中等学校课程研究”,第27—29页。
<30> 《登州文会馆》,第3—10页;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61-162; 狄考文编著,《官话类编》(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拙文,“狄考文与新约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世代》2019年第7期,第68—129页。
<31> 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 (Shanghai: 1895), 7,17,26,28; RGC, 1890: 461-464, 497,501;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第274—290页;《登州文会馆》,第100—102页。
<32>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选录),第210页;EAC, 1896: 51;《登州文会馆》,第12、87页。
<33> RGC, 1890: 458-459; RGC, 1877: 179, 171, 174; EAC, 1896: 52-53.评估狄考文的真理观与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相似而非延续,是因为笔者并未从其他课程的设置说明中看到类似科学与真理关系的表述。狄考文的课程设置理念也没有突出上帝的主权和普遍恩典,相反,文会馆的课程设置中,基督教只是作为与其他课程平行的科目来教授。参见董·佩奇尔,“加尔文主义与科学”,收入大卫·霍尔、马文·帕吉特编著,《加尔文与文化》,赵刚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第197—201页。
<34> 《登州文会馆》,第3—6、10—11页;EAC, 1896: 53; 《狄考文传》,第151—160页;韩同文编著,《广文校谱》,1993年,第16—17页;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文史资料选辑》第9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对文会馆物理实验的研究,可参考郭世荣主编,《登州文会馆物理实验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35> EAC, 1896:54; RGC, 1890: 457.
<36> EAC, 1896:54-55; RGC, 1890: 458, 465-466.
<37> 《登州文会馆》,第3—9、14、27—28、73、87页;谢扶雅编,《丁立美牧师纪念册》,第33、36—37页;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87-89。事实上,狄考文特别鼓励教师要与学生多有个人性的接触,尤其是外国教师更要通过课堂内外的教学、谈话、讲故事,当学生遇到麻烦时给予同情和施以援手等方式,与学生建立个人性的关系,帮助他们形成高尚的基督徒品格。他本人和狄邦就烈就身体力行。为了保证老师对学生有个人性的接触和影响,狄考文建议学校开办之初规模要小,然后再扩大。“开办学校就像点火,首先最好是用一些小碎片,当它们着火之后,再逐渐增加更多和更大的燃料。如果一开始就很快堆起粗糙和冷硬的燃料,结果就会失败。”见RGC, 1890: 464,465-466;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71-172。
<38> RGC, 1890: 466; 《登州文会馆》,第94—95页;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第101页。
<39> EAC, 1896:51-52; Mrs. C.W. Mateer, “What School Songs and Songs for 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should we teach and encourage in our Schools? Have such Songs been tried, and if so with what result?” in EAC, 1896: 107; Mateer, Julia Ann, Music Library(《圣诗谱》), 1907, preface,出版地不详;《登州文会馆》,第109—132页。
<40> RGC, 1890:460;《登州文会馆》,第27、73—75页。
<41>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61,167,169,177-178; 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 1895: 28; C.W. Mateer, “Self-support,” in EAC, 1899: 49-52; 《狄考文传》,第139页;张华腾,“1882—1895年中西书院诸问题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第88—92页;贝奈特,《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第88页。圣约翰书院1881年在几个中国商人的强烈要求下(pressing demanding)教授英文。次年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决定圣约翰学院开设英文课程,见The Spirit of Missions, Vol.46., 1881: 233; Vol.47, 1882: 146。在向国外母会募款方面,圣约翰学院也曾采用对个别学生认捐的方式,见The Spirit of Missions, Vol.46., 1881:34。
<42>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0—225页;崔华杰,“登州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学缘述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26—131页。
<43> 1873年,狄考文鼓励文会馆学生邹立文参加乡试,邹不负众望得中,为文会馆在当地赢得极大声誉。此后十年,又有16名学生乡试得中,但大多数学生并不热衷科举。狄邦就烈曾提及,文会馆最初的18名毕业生中有一人在1885年之前以优异成绩通过县考。但其余毕业生离校后无人继续学习预备参加科举考试以谋仕途,“他们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声称‘对于知道科学和真宗教的人来说,写应试文章索然无味’。”狄考文本人也对培养政府官员和科举士子缺乏兴趣,但这不意味着对科举考试完全排斥,也不妨碍他向清廷建言多设学馆,赏人功名,以振兴国家。他更从中国变法图强的时代潮流中预见到文会馆学生将来必有用武之地,因此他才对在文会馆推行全面教育充满信心。见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166, 167, 186;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选录),第218—219页。
<44>《登州文会馆》,第100—102页。
<45> 比如崔华杰先生就认为今天的中国大学在处理中西知识关系上,就可以借鉴文会馆代表的中西“平衡发展”路向,也即“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地位与西方科学知识看齐”,为学生未来之计开设各种中国知识类课程,为推动社会发展教授实用性的西方知识类课程。见崔华杰,“《文会馆典章》的时代意义与制度建设价值”,《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216—223页。
<46>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序,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页。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18期的主题是“教会学校”,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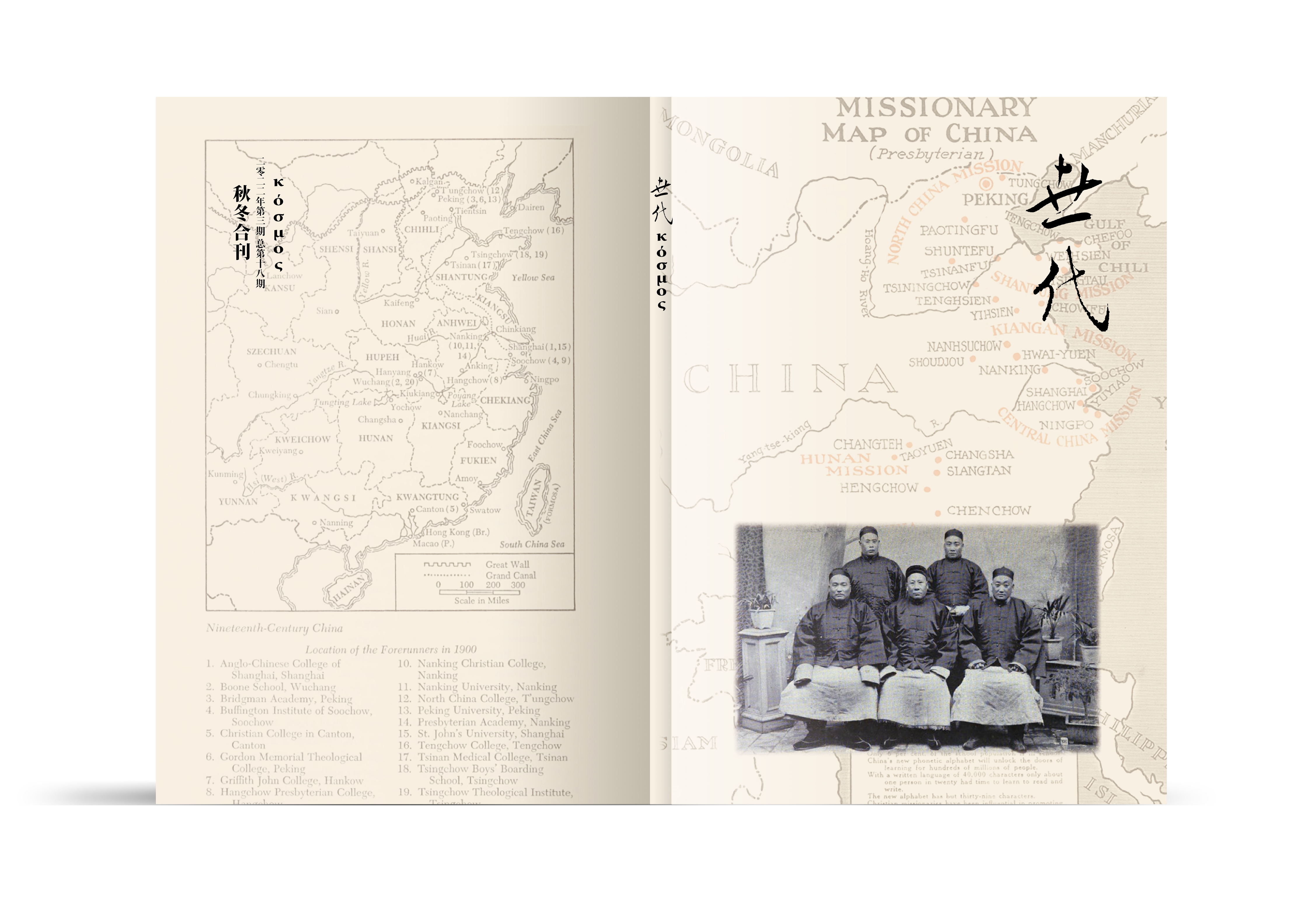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