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封面(2008年)]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已成为探讨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巨变的经典作品,此书分为“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三部,“帝国主义”是这部巨著的第二部,1968年也作为单行本出版。作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三部曲之一,阿伦特在“帝国主义”开篇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霍布森(J. A. Hobson,1858—1940)的观察,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有明确起点和终点的历史阶段,以1884年西欧列强对非洲的争夺和各种世界性运动的产生为起点,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终点。不过,与霍布森从经济学以及列宁从政治经济学对帝国主义的经典研究不同,阿伦特此书考察的是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这一“全新的政府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她认为,“这个时代的某些基本面向显示出非常接近于20世纪的极权主义现象,以至于有理由认为这整个时期是即将来到的大灾难的准备阶段。”<1> 从政治反思的角度,阿伦特分析了被极权统治所“照亮”的那段历史中涌现出的各种政治力量和事件: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资本和暴民的联盟、种族思想和官僚统治、大陆帝国主义的泛斯拉夫运动和泛日耳曼运动等等。她不是说这些事件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的发生,而是展示这些耦合的、集聚出现的效应,为极权统治准备了思想的、时代的条件。<2>
一、帝国主义的政治哲学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形成了她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即政治共同体(或国家)是由不同政府形式的法律和建制维护的、使人类生活有意义的“有形空间”,一个稳固的公共世界。她批评帝国主义不仅让政治全然蜕变为资产阶级的私人利益、经济利益扩张的工具,更是让“权力”本身的力量释放出来,摆脱了它为之服务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变成政治行动的本质和政治思想的中心”(p.138)。也就是说,权力或暴力已不再作为手段,服务于一般的政治或经济目标,而是权力本身就是目的,为了扩张而扩张。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统治阶级在它的经济扩张受到民族国家的限制而转向政治时,帝国主义就产生了。帝国主义带来一种为扩张而扩张的运动,它的逻辑结果则是摧毁一切现存的社会架构,以至于有帝国主义头脑的商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853—1902)担心:“人类的处境和地球的限度是通向进步道路上的严重阻碍。”(p.144)由此,阿伦特强调“帝国主义”是一个全新概念,绝非古已有之,不能以罗马帝国那种在殖民地强制建立共同法律的古代帝国形态来理解,也不同于古希腊掠夺式的海外殖民统治:“扩张作为政治的永久和至高目标乃帝国主义的核心政治观念。既然它所意指的既非暂时的掠夺也非更长久的征服同化,它就是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全新概念。”(p.125)
正是在帝国主义作为彻头彻尾的“权力政治”意义上,阿伦特声称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是帝国主义政治哲学的“唯一伟大思想家”(p.139)。首先,他预见到未来政治的趋势,从权力扩张的政治需要做出对人性的刻画,而非相反,从一种哲学人性论或心理学出发建构他的政治理论。阿伦特认为,霍布斯对哲学或心理学不感兴趣,他从人对权力的无休止渴求这一“现实主义洞察”出发,一面“根据利维坦的需要来刻画人的特征”,一面推演出“最适合这种权力渴欲动物的政体计划”。(p.140-141)如果说传统的国家用财产、法律、公共利益来限制权力这种本身不受限制、无休止扩张的力量(用霍布斯的话说,人类欲望的目的是要“永远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3>),那么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商人成为政治人,对金钱的疯狂占有和对权力的永恒渴望,才让私人利益和手段转变为执行公共事务的法则和规则。其次,霍布斯也是资产阶级应当承认的“唯一伟大哲学家”,因为霍布斯尝试从“私人利益”中得出“公共善”,“为了私人利益(private good)而构思和概括出一种国家(Commonwealth),后者的基础和最终目的是权力积累。”(p.139)在阿伦特看来,霍布斯论证了为权力本身而组织起来的政体的合理性。
最后,霍布斯让那些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失败者、不幸者、罪犯,从对社会和国家义务中解放出来。告知他们既然国家不再照顾他们,他们就可以释放他们的权力欲,利用自己在自然状态就具有的自卫保全的杀人力量,在社会的不平等之外恢复自然平等。阿伦特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两个多余力量——多余资本和多余劳动力(暴民)结合起来向海外殖民地扩张,国家充当了扩张运动的保护人,导致一方面破坏了有一定疆域和宪政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也摧毁了人权和法治的政治传统,从而一切驱逐、杀戮都成了可能的;另一方面毁掉了国家间的道义与和平,造成强权即公理、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最终破坏了欧洲传统所依赖的政治常识和利益法则。阿伦特在《起源》各个部分都描绘了现代的无根、多余之人的形象,但在她看来这主要是失能、无序的政治状况造成的。“不是他们走出社会,而是社会将他们抛弃;他们不是雄心勃勃地跨出文明许可的界限,而是无用的、失能的牺牲品。”这些多余人中最有才智的分子建立起一种“反社会”(countersoceity),“藉此找到一条回到一个有友谊、有目标的人类社会的道路。”(p.189)她认为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中的库尔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形象:从一个有着被认可的社会价值的世界被驱逐,抛回到自身,无根、空虚,对人类同伴毫无感觉的人,“在他们空虚的灵魂里唯一能迸发的才智是一种迷人的天赋,能够造就‘一个极端政党的出色领袖’。”(p.189)
[插图1:《黑暗的心》英文版封面(2016年)]
《极权主义的起源》已经贯穿了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维护政治的公共世界对于抵御极端恶的重要性。我们都同意人类生活需要政治的法律和组织架构,但我们也可能不知不觉认同权力哲学的假定,认为政治边界、规则等只是工具,只是追求个人或集体利益的手段,是为了其他更高目的可以替代或抛弃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与权力的疯狂扩张相匹配的政治共同体,大概只能是“种族主义”,泛民族运动这类基于人的肤色、民族的天生属性建立共同社会的疯狂形式。
二、帝国主义的自食其果
阿伦特在1944年的《政治评论》上发表了“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想”一文,后来作为“帝国主义”的第二章。在文中,她区分了“种族思想”(race-thinking)和“种族主义”(racism)。十九世纪盛行的各种种族思想: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德国浪漫主义的,但种族思想并不是种族主义,后者是帝国主义时期采用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帝国主义才是“开启历史的新钥”。早期帝国主义理论家迪尔克(Charles Dilke,1843—1911)就认为,共同起源、继承、“种族光辉”等既非有形事实,亦非历史的关键,“不过是一种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指引,无限空间的唯一可靠联结”。(p.182)例如,德国以种族统一作为民族解放的替代,与周围世界隔绝的英帝国必须发明一种理论来统一远在海外殖民地,同母国相隔千万里的英国殖民者。在阿伦特看来,种族主义产生自帝国主义这一新的经验和政治类型,“帝国主义必然会促成种族主义思想的发明,作为其行为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和借口,即便文明世界里从未存在过任何一种种族思想。”(p.184)阿伦特政治分析方法的特色总是现象学的:以事件、经验为意义中心,寻找被事件所“照亮”的先前的概念或活动,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概念或对旧概念提出新解释,以充分理解事件的新颖性,而不是用所谓古已有之的说法回避思想的挑战。在她那里,纳粹极权统治就是她一生政治思考的核心经验。
近年来随着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阿伦特的帝国主义叙事也受到欧洲中心论、甚至文化帝国主义的质疑。在批评者看来,她似乎并非像她后来的政治哲学所主张的那样,肯定不同民族的人们平等地共享一个世界。<4> 激起这类批评的文本集中于“帝国主义”的“种族与官僚统治”一章,她在那里分析了两种帝国主义统治的手段,一种是围绕种族建立起来的统治,以南非布尔人对黑人的统治为典型,另一种是以官僚统治为治理海外殖民地的方式,以英国为典型,不过她叙述的重心不是放在南非黑人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被压迫状况,而是放在了殖民统治如何令“白人”精神扭曲堕落上。
阿伦特在开始提到南非土著居民时,用了“霍登托特人”(Hottentot)这个贬低性的称呼,这个词相当于“野人”。如果说她只是无意识地用了这个词,不清楚它背后的冒犯含义的话,那么她在文章中似乎也持一种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野。她说,“种族”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殖民者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一部分人,或一些未有历史记载、不知它们自身历史的部落的一种“应急解释”。(p.185)在他们眼里,他们的低劣不是由于肤色,而是没有在自然之外创建一个更高的文明世界,行为举止更像蛮荒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创建一个人类世界,一种人类现实,因此自然就始终以无可争议的主宰者保持为唯一强大的现实。相比之下,他们看起来更像幻影,像幽灵一样不真实。”“他们是如其所是的‘自然’人,缺少具体的人类特征,特定的人类真实性,以至于欧洲人屠杀他们的事后,并未意识到是在犯谋杀罪。”(p.192)类似地,在《黑暗的心》的主人公、殖民者马洛的眼里,黑人仿佛是一群神秘无解的存在,以至于他无法从自身的感情、动机、冲动,甚至对饥饿这一极端肉体痛苦的人类反应来了解他们。阿伦特的这段话既反映了与非洲大陆初次相遇的白人文明视角,又隐含了她自己的批评视角,即对于白人无法理解、不愿理解的部分人类,他们惯于以文化和自然的对立让对方“自然化”,从而使之“野蛮化”和“非人化”,看起来不像具体真实的人,因此对他们的杀戮就变得容易些。
有学者认为阿伦特在这里的叙述角度,跟她坚持文化优于自然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一致,并将之追溯到德国哲学传统一贯的对“教化”(Bildung)的推崇。<5> 在她关于劳动和工作、行动的三分中,阿伦特也认为单纯的劳动作为维持人类有机生命的新陈代谢活动,不具有创造持久现实的价值。这里我们暂不论“文化优于自然”的观点是否暗含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偏见,不过她在这里主要据此批评南非布尔人在文明和道德上的堕落:不是由于他们受到非洲人未开化的自然状态的影响而从文明的高处堕落,而是种族统治让布尔人堕入“自然化”、“去文明化”。布尔人是居住在南非境内的荷兰、德国和法国移民的后代,作为早先失去土地和定居生活的多余者,他们来到南非,却仅仅靠肤色被土著人当作自然神来崇拜,奉为部落领袖,结果,他们变得懒散而生产力低下,失去创造文明世界的热情。阿伦特发现种族统治造成的恶果是,布尔人不再有力量将现有的生活环境改造为一个文明的世界,失去了“欧洲人那种对领土、祖国的感情”,丧失了“西方人以生活在自己创造和构筑的世界中”体验到的“自豪感”(p.194,196)。接下来发生的是,他们在淘金热中更倾向于相信关于犹太金融家的传言,更把犹太人当成一个不同的种族来仇恨。种族统治的历史让南非白人难以摆脱“白人的恶习”,相反,阿伦特发现,黑人工人却在正常的劳动和城镇生活中,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人类地位和人类尊严。可见,她并非将“文化/自然”的区分和种族等级观念挂起钩来,同时坚持普遍的人道观念不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而是在人类共同建构的世界中培养起来的。
与布尔人缺乏“欧洲人”文明意识相对照,阿伦特比较了英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印度的官僚统治。如果说布尔人的种族统治是逃避“白人责任”的结果,英国人的官僚政治则是出于“白人责任”的结果,一种源自新教的、对“落后民族”的牺牲精神和对大不列颠王国的“责任感”,让他们试图承担起任何人对人类同伴、对其他民族都难以担负的责任。但同样可叹的是,这批优秀的英国人既非虚伪,也非出于种族思想,认真地担负起所谓“白种人的负担”,却让自己成为“悲剧的、唐吉可德式的傻瓜”、愚蠢的“屠龙者”形象。(p.209)
[插图2:“白人的负担”(1899年)]
造成这种事与愿违的悲剧原因,在她看来一则在于,官僚统治只能是有经验的少数人去统治多数人的专家政治,从而必须要不断抵制和应付来自没有经验的多数人的“经常性压力”。而每个人其实都属于“没有经验的多数人”,也就意味着不能托付他们像政治和公共事务这类高度专门化的事情。(p.214)结果,每个人都没有理解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整体的愿望,管理的每一步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团漆黑,当然也无人负责。二则,她发现让一个民族去统治另一个民族,让英国人去统治印度人的责任风险还在于,他们对于治下的臣民缺乏真正的兴趣,秉持一种“正直”和“超然”的态度。
阿伦特引用克罗默勋爵的自传,分析了这类帝国优秀分子的特征。这种态度有别于当地统治者的残酷和独断,有别于亚洲征服者极度的剥削,他们的正直甚至不允许独裁者和臣民之间由贿赂和礼物构成的关系,却使英国殖民当局比当地独裁统治更无人道,更远离臣民。“相比之下,剥削、压迫、腐败看来像是人类尊严的卫士,因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腐蚀者与腐败者仍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互争夺同样的东西;而超然态度摧毁的正是这类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第三方。”(p.212)
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人类维护政治的公共世界之重要性。在《起源》的帝国主义部分,她试图从各个面向展现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在“帝国主义”的序言中,她用“反向效应”(boomerang effect)来形容帝国主义的自食其果,对西方文明传统的瓦解和对启蒙以来人道信念的摧毁,为随后到来的恐怖搭建了舞台,为极权主义准备了条件。可见,她关心的始终是理解欧洲人自身的问题,即“欧洲,这个人权与启蒙运动的故乡,如何孕育了极权主义这样一种残酷的、嗜杀的政治形式?”<6>
<1>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8), 123;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83页。本文引文参考了该中译本,并根据原文略有改动。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下同。
<2>《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标题虽醒目却有些误导性,因为这里“起源”的意思既非极权主义在历史上的开端,也非导致它产生的原因。这本书在英国出版时所用的标题《我们时代的重负》,更为接近阿伦特的原意。
<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72页。
<4> Anne Norton, “Heart of darkness: Africa and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Writings of Hannah Arendt,” in Bonnie Honig 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Hannah Arend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7–262; Christopher J. Lee, “Locating Hannah Arendt within Postcolonial Thought: A Prospectus,” in College Literature 38(1): 95–114.
<5> Jimmy Casas Klausen, “Hannah Arendt’s antiprimitivism,” in Political Theory 38(3): 394–423.
<6>达纳·维拉,《剑桥阿伦特指南》,陈伟、张笑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页。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题图:《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封面。图片来自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101021/
插图1:《黑暗的心》英文版封面(2016年)。图片来自google books.
插图2:“白人的负担”(1899年)。图片来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White_Man%27s_Burden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7期(2022年夏季号)。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17期的主题是“反思文化帝国主义”,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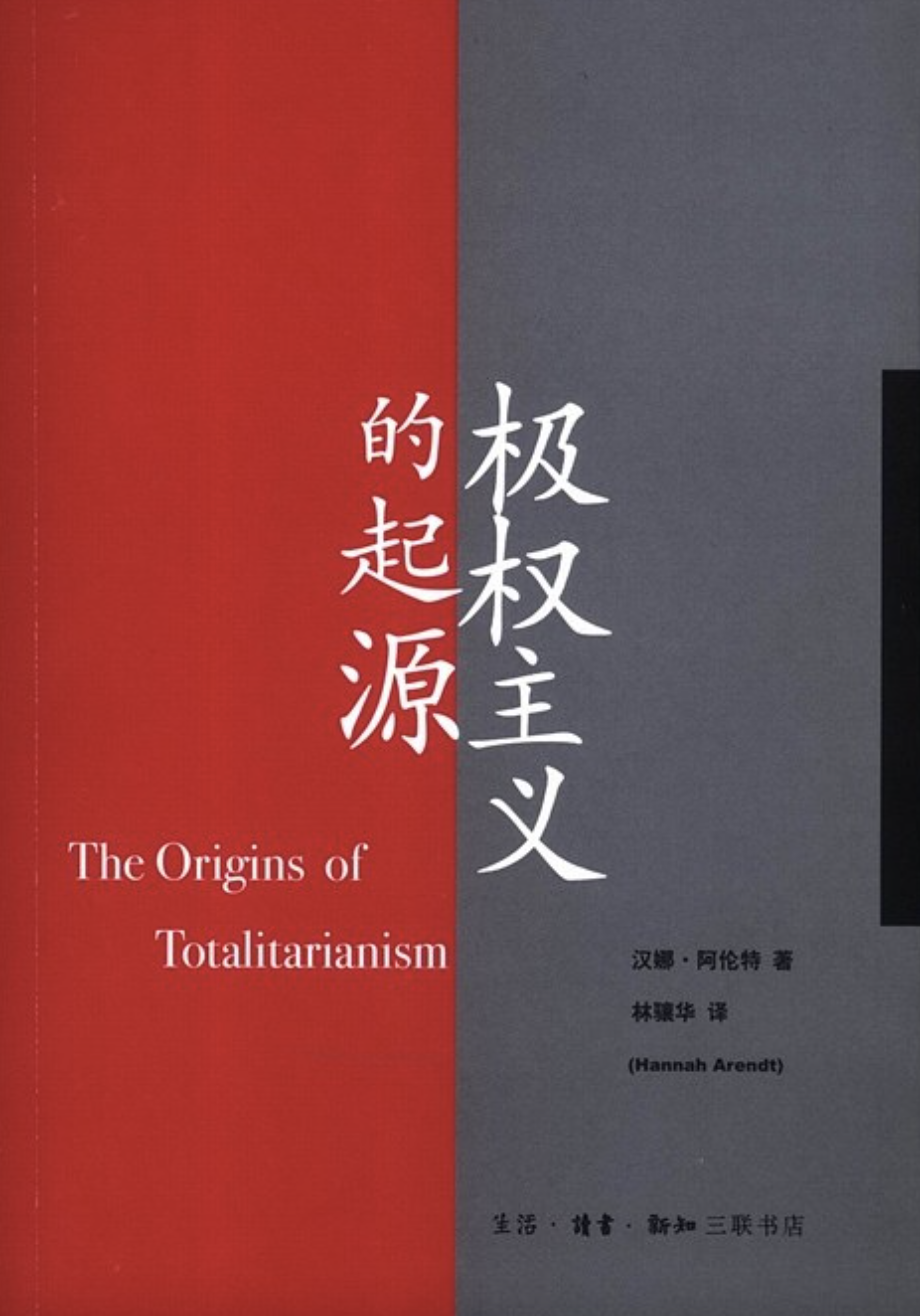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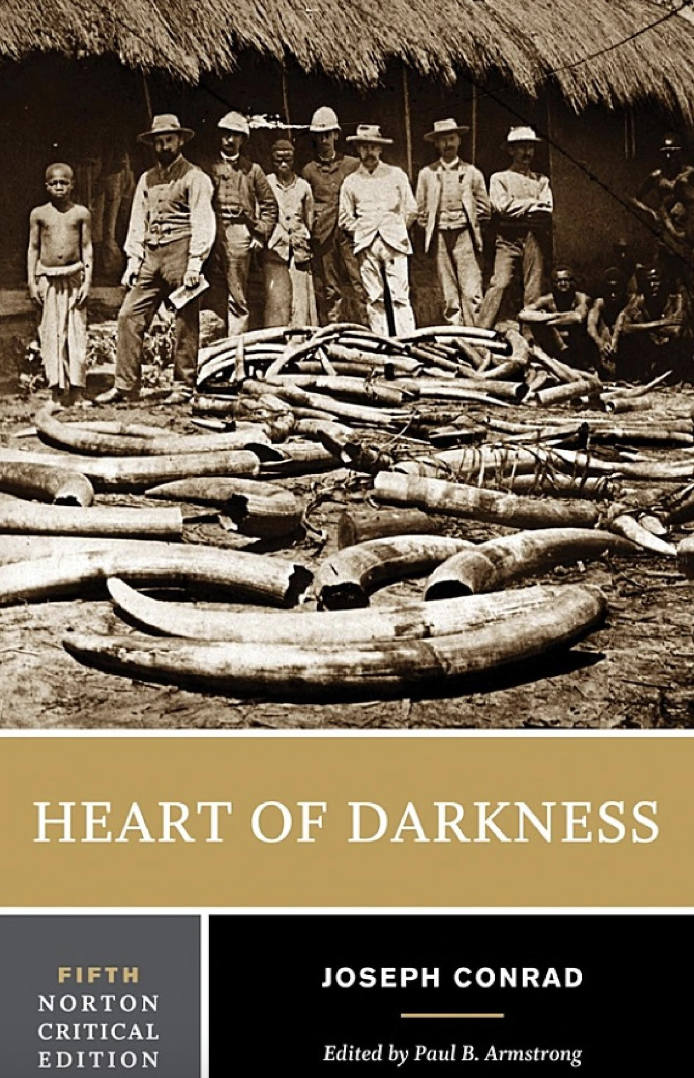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