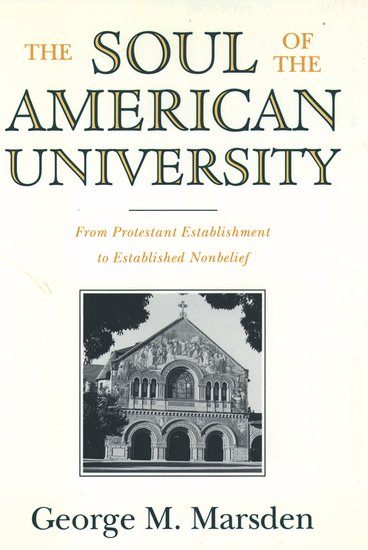
《世代》按:
此文是美国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引论译文。接下来会分享其余部分。为便于阅读,《世代》增加了这部分题目,对段落也有所细分。
原文发表于1991年1月《首要之事》(First Things):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1991/01/005-the-soul-of-the-american-university,后在1994年扩充为同名书出版(封面见题图)。马斯登写作此文时,在杜克大学神学研究生院任教。马斯登曾在加尔文学院长期执教,现在是圣母大学历史学荣休讲座教授。
我们考察的主题是当今世人习以为常的特色现象之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却是不正常的。这个现象就是,美国众多抗议宗基督徒(Protestants) <1> 对高等教育中在神学院以外有明显基督信仰色彩的研究项目几乎都不给予支持。尽管超过60%的美国人是教会成员,他们当中一半以上的人是抗议宗基督徒,大约超过55%的美国人说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但似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信仰对高等教育来说“很重要”。
美国的抗议宗基督徒大致平分为福音派和持中间立场的自由派。然而两派都不支持任何有抗议宗基督教信仰且有规模的大学。他们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小型自由文理学院。这些学校跟主要的宗派有关,通常只是隐约受基督教影响。一百多所福音派学院有更显著的抗议宗基督教信仰。其中一些是相当好的学院。但是这些学校学生的总数大概等于两所州立大学的规模。神学院之外,美国几乎没有抗议宗基督教大学的研究生院。
抗议宗基督教会领导层和会众都已经对基督教高等教育鲜有兴趣,从不同宗派教会的角度看,这尤其让人困惑。当传道人哀叹平信徒缺乏教育,他们为何不鼓励基督教的学院教育呢?当平信徒抱怨很多传道人自身的教育水平差,他们为何不支持学院和大学好让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进入神学研究生院?当教会领袖谴责异教哲学泛滥,他们为何对研究生教育没有任何严肃的兴趣呢?
考虑到抗议宗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悠久历史,这种状况尤其触目惊心。归正运动始于一所大学中一名学者的洞见,教育机构在抗议宗的成功中早就扮演一种主要角色。受过教育的传道人在挑战罗马公教(Catholic) <2> 权威方面至关重要,在受抗议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包括美洲的抗议宗殖民地,传道人在几个世纪当中通常是一个城镇或村庄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在这个国家,直到19世纪,高等教育还主要是教会的一个职责,一如西方文明中一贯的情形。大多从事教育的人是传道人,教授的职业跟传道人的职业没有清晰的区分。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当然不完全都是抗议宗的。尤其是罗马公教提供了显著的不同选择。然而,直到近来,抗议宗基督徒及他们的后继者们在制定美国大学的标准方面却起到了压倒性的重要作用。如果这些学校曾经有灵魂的话,在主导的愿景或精神的意义上,这个灵魂曾经所在的就是抗议宗基督教的谱系。
直到美国内战时期,绝大多数美国学院都由教会建立,不少有国家或社区税收的支持。由于高等教育通常被认为既是公共服务也是宗教事业,教会与国家看起来就很自然地携手工作,甚至在教会不再享有官方地位之后也如此。抗议宗学院当时不仅是教会学院,也是公共机构。即便是在美国革命之后出现的州立学院和大学,有时带有杰斐逊式的去除教会官方地位的意图,仍不得不向它们所在选区的居民保证,这些学校会看顾学生们的灵性健康问题。
几乎所有学校当时就是或后来变成了广义的抗议宗机构,都有必要的教堂,不少都要求师生周日去教会。晚至1890年,一份关于二十四所州立学校的调查报告显示,二十二所仍然有必要的学校教堂敬拜或者在大学建筑中有自愿的教会敬拜,四所仍要求学生去教会。这些只是州立学校。跟教会相关的学院和大学,就更是严格的抗议宗机构,这些学校在1890年时仍然由传道人担任校长。
那么,上述当今抗议宗与大学关系状况的特色就更加显得触目惊心,不仅因为抗议宗基督徒已经抛弃了在基督教高等教育中具有领导位置的长久传统,也在于,他们其实是在如此晚近才抛弃的,而且抛弃得如此彻底。即便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院和大学一般仍然表现出这样的看重,就是支持宗教活动,这在今天大部分大学人士看来会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可以再次通过察看州立学校的情况让这一点充分表现出来。一份1939年关于州立大学和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24%的学校仍然有学校教堂敬拜,8%仍然要求这是必须的。超过一半(57%)的州立学校负责学校教堂敬拜的特别讲员或宗教聚会的财务开支。40%的学校对自愿宗教团体有补贴。尽管州立学校在那时不再要求必须有教堂,有些州禁止州立学校教授神学,支持自愿宗教活动的补偿措施在别处得到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了在州立大学增设宗教课、宗教系或学院的显著运动。其中最知名的是艾奥瓦大学宗教学院,创立于1920年代,作为平衡,其中除了有抗议宗,也有罗马公教和犹太教的代表。这所学校创立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宗教活动和培养宗教领袖,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没有个人感受的宗教学术研究。1920年代,伊利诺伊大学开始允许合格的校园宗教组织提供有大学学分的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公教纽曼基金会仍然在继续这种做法,尽管抗议宗基督徒在1960年代因教职人员广泛抗议放弃了这种做法。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是有关州立学校的状况。私立学校大多曾经有抗议宗的传统,相比州立学校,那里的宗教传统要更显著而且更悠久。耶鲁直到1926年才取消学生必须参加学校教堂敬拜的要求,普林斯顿彻底抛弃这个做法是在1964年。1890年代,芝加哥大学是作为一所浸信会学校创建起来的,其首任校长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希望这所学校支持以《圣经》原则为基础的文明。循道会基督徒也创立了一系列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学,包括杜克大学、埃莫里大学、波士顿大学、叙拉古大学、西北大学、南方循道会大学,以及南加州大学,其中大多有神学研究院。杜克在1924年创立的时候,其创始文件声明,“杜克大学的目标在于宣称一种信心,就是相信知识与信仰的永恒联合,这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教导和品性中得到了阐明……” 直至1960年代,杜克仍继续要求其本科生上《圣经》课。卫斯理学院也是如此,这所学校由德怀特·穆迪(Dwight L. Moody)的朋友们创办于1870年代,当初是福音派学院。
20世纪上半叶,诸如普林斯顿、杜克、芝加哥这些学校建造的大教堂或者耶鲁的哈克尼斯塔,也许是名牌大学致力于保留宗教之地位的最好象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以建筑形式表达的声明也许可以被看成面对势如破竹的世俗化而出现的最后补偿姿态,世俗化在那时实际上正在接管这些学校。
人们已经如此彻底地忘记了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上半叶还有宗教维度,部分原因在于就在那时,这些宗教维度对于大学的主业来说已经边缘化了——如果不是完全不重要的话。还有,在1960年代及以后的新文化压力热潮下,这些宗教维度中最重要的部分大多很快蒸发了,很多情况下几乎毫无踪影,也罕有多少抗议。
那么,让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世纪前还相当可观的抗议宗教育事业——这事业到那时一直是抗议宗传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为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抛弃,而且是人们自愿抛弃的。或者,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为何一个世纪前还在西方教育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基督教,如今却变得不仅对高等教育来说完全边缘化了,而且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对教育事业而言也是全然陌生的?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我们该回去的、失落的黄金时代。从我自己持有的多少是传统的抗议宗观点看,大多数抗议宗基督徒抛弃了对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兴趣,这的确是一个损失。今日学术界呈现的各种观点,没有任何表达明确基督教观点的实质性位置,这也是损失。我确信,基督教观点在思想上是成立的,能够也应该塑造基督教机构。另一方面,很多基督徒会认同,我们这里描述的世俗化并非都是坏事。世俗化的相当一部分是拆除残留的宗教主流地位,在那种状况下,按照宗教身份形成的社会精英将官方的宗教活动强加于所有将会进入社会主流的人身上。另外,19世纪抗议宗主流学院通常只提供少数人的教育,学生只有几百名,几乎不能与这种学校发展而来的成规模的大学相比。若要在20世纪的环境下继续存活并提供服务,无论这些学校有哪些优点(它们曾有很多优点),它们都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加以改变。这些有较长历史的机构失去了很多基督教维度,这是此消彼长的一部分,似乎是应对现代性的需要所必有的。
因此,这里涉及的历史,不是简单说一些坏人、幼稚或愚蠢的人决定抛弃抗议宗传统中最宝贵的方面。而是关于一些人,当他们的传统跟现代世界产生接触时,他们意识到了一些严重问题。结果是否为改进甚或合理,这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教育的领导者们对一些异常困难的境况做出了回应,他们并非完全能够为他们决策所产生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负责。
我在这里分析中所提,是想强调三股主要的力量,这些力量是当初那些新兴大学及所在地区的领导者们回应的:第一,跟技术社会需要相关的力量;第二,跟意识形态冲突相关的力量;第三,跟多元主义及相关文化变迁有关的力量。我们对这些力量如何塑造美国大学当今灵魂的理解,就可能为基督徒及其他宗教信仰人群在面对美国高等教育主流问题方面提供如何前行的基本参考。
<1> 抗议宗,即宗教改革或归正运动中兴起的基督新教,相对于罗马公教或天主教。——译者注
<2> 罗马公教,即天主教。——译者注
译/许宏
此译文首发于《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