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国大陆城市家庭教会向堂会的转型,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的建制化发展,教会似乎出现了一种中产阶层化的现象。如何理解教会在建制上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信众参与的关系?中产阶层的这种参与跟教会的中产阶层化又有什么不同?本文试图对此问题给予初步的梳理。
一
在福音书的记载中,耶稣所关注的更多是当时社会的弱势或低层群体。最早跟随他的那些门徒,多来自社会底层,比如彼得与他的兄弟及约翰与他的兄弟等,都是渔夫。这给后来的人们一种印象,似乎在基督教兴起的初期,构成教会主体的都是来自社会底层或边缘阶层的信徒。这个印象似乎与保罗的这句话也是吻合的:在蒙召归信基督教的人中,“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1>
20世纪的不少思想家们似乎加强了这种看法:基督教起源于社会底层的无产者,当时社会底层的无产阶层构成了最初新兴的基督教团体的主体。直到上世纪30年代,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古迪纳夫(Erwin R. Goodenough)在一本广为流传的教科书中还这样说:“在罗马人的眼中, 基督教信仰之所以毫无吸引力可言,更是在于信徒的社会身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归信基督教的人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 <2>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考茨基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甚至在一段较短的时期内达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恩格斯也有类似的看法:“基督教在起初的时候是被压迫人民的一场运动:它最早出现时,是奴隶、解放了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贫苦人民,以及被罗马帝国征服或遣散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 <3>
其实,古代的资料显示,基督教并非就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无产者运动。常被引用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吉本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污蔑说,新的基督教派几乎完全由农民、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等等人类的渣滓所组成。” 这里,他显然是在描述他所不认可的对于早期基督教的污蔑,而他自己的看法是:“也有一些天赋过人或财产丰富而有一定地位的人成为它的信徒。” <4>
19世纪末,苏格兰考古学家、新约圣经学者兰塞(W. M. Ramsay)在其经典著作中就曾写道:“基督教刚刚开始传播的时候,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接受这种信仰比从未受过教育的人要快的多。在罗马皇帝的朝廷之上,基督教立足最稳……别的地方哪也比不了。” <5>
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哈纳克(Harnack)注意到,伊格纳修(Ignatius)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怕他们对他将要在罗马的殉教进行干预,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将他解救出来。<6> 哈纳克认为,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即伊格纳修很自然地认为,罗马的基督徒有“能力”使他获得赦免,而“如果当时的教会之中不存在这些有财富而且有名望的成员,有能力通过贿赂或者个人影响来干涉这件事,那么伊格纳修的担忧完全是没有理由的”。<7>
1960年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贾吉(E. A. Judge)在对早期基督教团体的社会阶层进行仔细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基督徒群体的主导者是大城市中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看上去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地位。除此之外,他们似乎来自于一个广泛的社会范围,并且源源不断地流入教会。他们很可能依附于那些领导者们的家庭……但这些依附于领导者家庭的人们绝不是社会中最为低下的部分。即使没有充分的自由,他们仍然可以享有安全的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和富裕。”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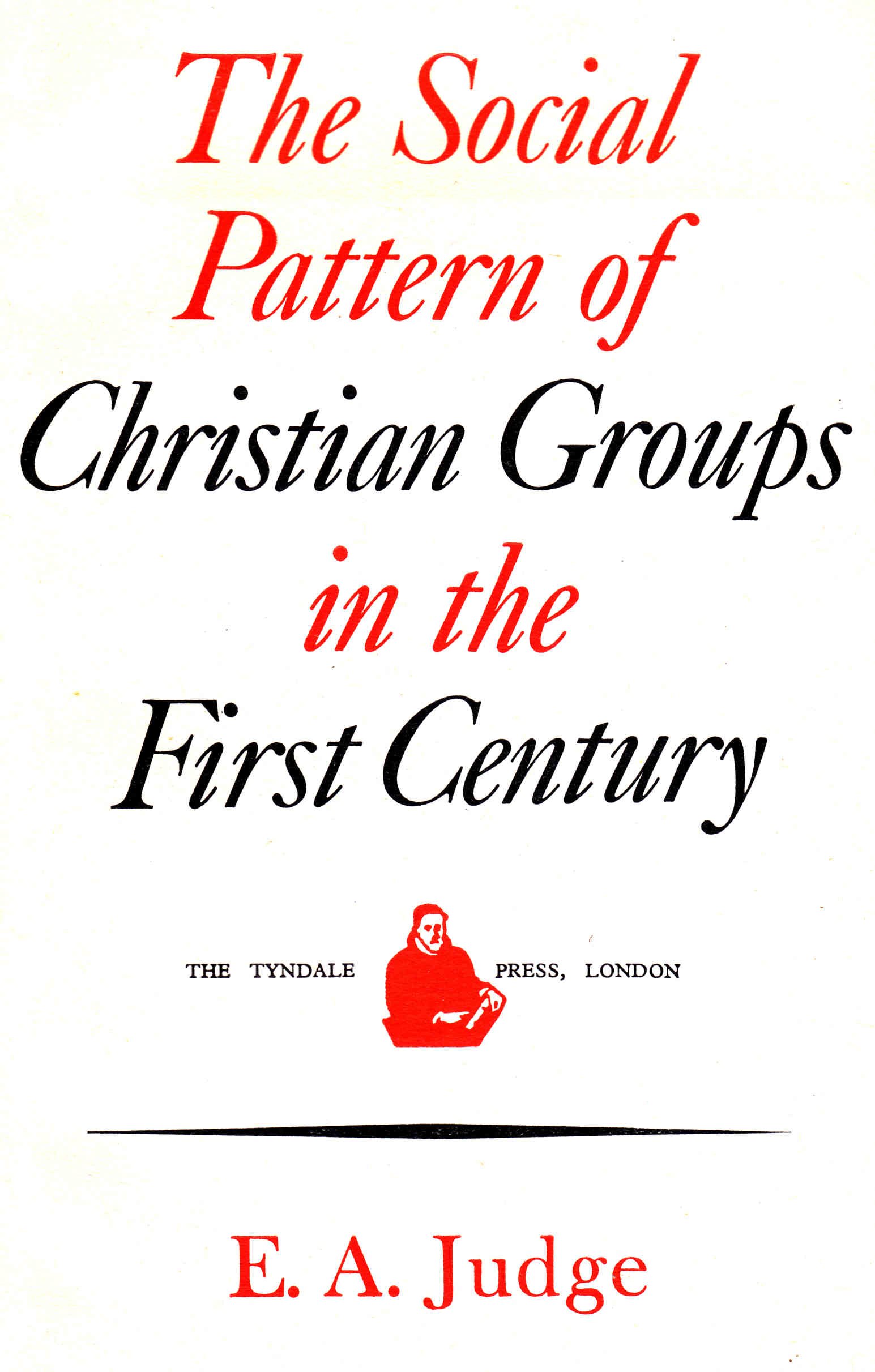
到了1980年代,研究新约的史学家们逐渐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早期基督教的信徒基础是建立在中产阶层和上流阶层之上的。在1986年出版的专著中,意大利历史学家索尔蒂(Marta Sordi)写道:“我们可以通过可信的材料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在公元1世纪后半叶的[罗马]贵族之中,也有一些基督徒……而且,即使是公元1世纪的前半叶,在使徒保罗抵达罗马城之前,情况也很可能是差不多的。” <9>
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从早期教会人数的绝对值来说,或许社会底层的人多一些,但从这个运动所起的作用来说,受教育的、或有地位的、富裕的群体所起的作用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圣经《使徒行传》6章中,引导最初耶路撒冷教会实行分工乃至走向建制的第一个事件,就是执事的选举;而选出来的七个人都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说这七位讲希腊语的犹太人都是受过较高教育、家境富裕的犹太人,但从司提反的例子中,特别从他那满有圣灵能力的辩论能力中可以看出,这些从世界其他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的“海归”犹太人,比起生活在耶路撒冷本土的犹太人来说,接受更高教育的可能性更高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扫罗也可以算作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同时受到非常好的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教育。正是他们这批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后来在耶路撒冷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被分散到各地,从而将福音的种子带到撒玛利亚与安提阿,并经过安提阿而传向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基督教由最初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拿撒勒教党”)变成一个普世的世界性宗教,最初的这些讲希腊语且受过较好教育的犹太基督徒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
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中产阶层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在古代社会,我们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可能是以一般贵族或者其他家族地位较高的社会身份出现的。在那个尚未进入普通国民教育的时代,也只有他们同时接受了更高的教育。
在宗教改革之后,当工商业开始大量兴起之后,中产阶层就与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水平关联起来。当普通国民教育普及之后,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提到中产阶层这个阶层时,我们特别将其与那些有稳定的、收入较高的工作,同时又接受过较好或较高的教育,因此会对社会及其文化领域有较高关切、且产生相应影响的那个群体联系起来。
1990年代,中国大陆城市家庭教会兴起的时候,无论这一代的带领者是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新兴的家庭教会便与这个中产阶层群体产生了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类型的城市教会中,约百分之七八十的成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他们中有很多人在自己各自的职场领域中有着较好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他们关注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事件,在不同领域对社会主流文化产生着影响。
当他们归信进入到教会中,他们渴望对自己的信仰了解更多,渴望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教会的服事与治理中。换言之,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参加主日敬拜,在讲道中只是听一下他人的信仰见证或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他们希望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希望通过主日学了解信仰的基本真理及生活的基本准则;他们想了解教会为什么是这样运转的;他们希望自己在福音、音乐、文字等多方面的恩赐能够在教会中得到发挥;他们希望自己的交友、结婚以及子女教育能够得到教会的指导。总之,教会不是一个只是主日来一下的地方,不是一个可以和日常生活分离而只涉及到个人情感或灵性的地方,教会就是一个共同生活的社区,是一同操练某种生活方式的地方。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少城市新兴的家庭教会开始向堂会转型。堂会型教会是指,已经有一定的教会建制,能够在多个方面,如福音与宣教、崇拜与圣礼、教导与神学教育、辅导与家庭关怀、社会服务与文化使命等方面承担教会在这个时期所当发挥之功能的较为整全的教会。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层(特别是指教育意义上的)信徒的参与是教会走向建制化的重要力量。
这里所说的教会建制,其实并不单纯指几个受过更好教育的人起草了教会的章程,或者把其他教会的章程转抄过来就完成了教会的建制过程。这些文字仅仅是存在于纸面上还是不够的,教会建制更深层的含义是指,教会形成了某种的团队带领与服侍,同工间的相互分工通过教会章程或其他文件确定下来。并且在教会实践中,教会成文文件中的基本观念或精神已经进入到这个教会整体的运行中,无论是带领层面还是普通信徒层面都形成了一种有意识的约束;特别是在教会同工层面上,已经在同工的配搭中被证明是被接受与磨合过的东西。这样,教会建制就不只是指教会已经有了明确成文的信约、章程、教会纪律,同时还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牧养体制、治理体制、事工体制及宣教体制等。
总之,教会建制就是建立在分工体系基础上团队配搭的进一步明确,涉及的是这个团队的基本理念与相互配搭关系的约定。如果在牧养或治理上没有这种团队彼此的配搭关系,其实也就不需要建制方面的建造。受中国文化而不是圣经真理的影响,过去人们在教会中比较简单地处理这个团队关系的方式就是由亲友构成事工的团队。依靠血缘关系带来的信任造成教会的家族化,依靠密友构成的“党朋”圈子带来的信任则造成教会的专制化,这些都使教会降格为家族或者朋友的事业。如何打破以往个人的、家族式的、党朋封闭化的教会模式,防止教会中的专制与腐败,是随着中国家庭教会迅速成长、人数迅速增加所出现的一个重要挑战。已经看到的一些案例证明,目前教会内部出现问题,基本上是教会的专制或者同工间的分裂带来的,这正是建制方面的建造所需要去面对的。
三
对于这些探索和推动教会转型的新型城市教会来说,推动教会走向建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推动家庭教会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也就是使得教会建制与社会建制有某种衔接。城市家庭教会向公开建制化的堂会转型趋向,从显在的层面来看,有其圣经及教会传统所提供的神学理念。但从隐性(或背景)的层面来看,教会对其公开与建制性的强调还是反映出这一代多少与中产阶层有关系的信徒的社会处境。
如果信仰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而“山上的城”更深地意味着它不只是个人的生活方式,而同时是指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推动家庭教会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或公共领域时,教会作为“山上的城”就可能有这样的榜样作用:作为一个信仰生活的共同体,教会不只是在生活准则方面,同时也在人际关系、社团治理、社会服务等方面成为中国社会的楷模,由此见证这个群体所传讲之福音真理的普世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家庭教会表现出的公开建制化的教会观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大致可以看出如下方面。第一,教会的公开化,使教会的大门打开,每一个想要寻求信仰的人都能更容易地进来,有利于教会完成福音使命,同时也会有效地抑制异端的产生。第二,教会的公开化,在不加入“三自爱国会”的前提下寻求其独立的宗教团体的合法地位,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模式,以及中国民间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存在;第三,教会的建制化,通过设立教会专职职分并教会章程来给予规范,特别是全体会友大会对想要承担这职分的人进行选举印证,为这个社会中的社团自治提供了一种典范。第四,教会纪律的执行,促进教会这个信仰群体有其特有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失去道德底线的社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重建道德规范的作用。第五,有一定规模的堂会型教会,可以更大的投入力度或年度规划,使社区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常态化。
至少从后四个方面来看,城市家庭教会向堂会的转型与这个处在危机中的国家的社会重建——特别是在法治、社会自治与道德方面重建,使中国社会向着公民社会发展——这个大方向是相合的。地上可见教会既是一个信仰的群体,由一群重生的或被分别出来的人组成(上一代教会观所强调的),同时也是一个生存于现世的可以被人看见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这是强调教会建制化的一个引申结果,从某个方面看,突出了教会作为基督身体道成肉身的入世性。这里,不是社会群体的组织性导致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有机性,而是相反,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有机性导致其作为社会群体的组织性。就教会所具有的后一方面的属性而言,教会群体与社会不同领域中的其他社会群体,包括政府机构(如果我们将其限定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群体的话),无论在组织模式、基本道德规范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在神学上,这属于神的普遍恩典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当然,从显在的层面来看,这些方面并不是教会在这个世代存在与发展的直接目标。教会在走向公开化进程中所有这些方面的发展,都附属于其福音使命的大目标之下,有其教会论以及相应圣经方面的指导,并非以上述概括出来的社会影响为其目标,或者说,上述诸方面的影响是教会发展及其福音使命的副产品,是教会建制与社会建制可能产生接触点的表现。
四
在城市家庭教会由重视灵恩的松散团契转型为建制化的堂会这一过程中,中产阶层信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在肯定其所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同样也要意识到,教会在这过程中亦有被中产阶层化的危险,即让某个社会阶层的世俗属性在教会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
中产阶层若是在经济收入或社会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上较其他阶层更高或更稳定的话,也正说明他们在世俗社会的这个阶层中浸润日久,因此会在追求成功的价值观,以及现代社会的竞争与自我实现意识方面,遇到更大的挑战。可以说,如果在教会生活,还没有用从基督信仰而来的价值观去胜过职场上的那种追求成功的、自我实现的价值观,那么后者就一定会影响到教会,让教会成为一群人相互帮助追求事业成功的俱乐部。好在基督信仰并不只是让我们放下所有,宗教改革家们还为我们提供了天职或特别呼召这个有力的武器,来让我们学习如何在职场中来服侍基督。当然,这里的前提就是我们真能够通过舍己而成为基督之门徒。
中产阶层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日常生活及思想上追求稳定,让一切都按部就班地照着一定的规矩而行,以便达到所期望的更好的目标。为此,他们易于向世俗或者强权妥协,如果后者让这个进程及其目标受到威胁的话。中庸之道虽然在处理事务方面不无稳重的一面,但若涉及信仰之根本问题,就会显出不冷不热,缺少不顾一切追随基督的激情。当信仰生活以事工目标来主导,功利的判断代替了属灵的看见时,人们所站立的地点就会发生漂移,而不再是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头,为教会群体唯一当站立的地点。
第三,置身于中产阶层的基督徒,在还没有学习舍己成为基督之门徒的功课前,在教会群体中总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其身份的优越意识。这种意识拉开了他们与其他信徒的距离。这种距离在教会内会影响他们与其他信徒的团契关系,而在教会外则会影响他们对福音的见证,造成缺少福音热情与社会关怀的热情,特别是缺少关怀贫苦与弱势群体的热心。委身教会的生活,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拆除在各个阶层或不同群体之间将我们隔开的墙。
教会中的中产阶层所具有的第四个显著特点就是头脑比较大,或者思想中的理论比较多,从而在语言上给予他人的道德主义的评论很多,但付出的行动却很少;表达出来的感动很多,直接付出的行动却很少。
由此看来,中产阶层真要是在教会建造及发展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信仰带给他们的更大的挑战。经历了更多更大的挑战所带来的生命的转变,会让他们在教会进入城市公共生活的进程中带来重大贡献。但如果没有在上述这几个方面的挑战中经历得胜,那么当他们在教会中发挥重要影响,所带来的教会的中产阶层化,则无疑是教会被世俗化的重要表现。
基督信仰乃是基于基督十字架之恩典的信仰,突出的是福音的中心性;福音适合于社会任何阶层与社会背景的人,任何人都是借着信而得着这恩典,并因此而得救,无论他属于哪个阶层,都与他们所具有的家庭、社会地位及教育背景没有直接关系。教会向所有阶层与社会背景的人群敞开,凡进入教会群体中的人,都必须通过委身教会而破除自身阶层带来的身份感,唯独以基督的门徒为自己的身份;打破不同阶层所形成之不同圈子之间的隔断,唯独以在基督身体中圣徒的相通为追求目标。如此,才能在基督里经历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改变,不再追求世上的成功与自我实现;活出从基督而来的爱,关心弱势及有需要的人群。
在教会今天所面临的两大挑战——既面临着日益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也面临着现代化所带来的世俗化的挑战——中,教会是否能够得着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而又不被中产阶层化,这一点对于家庭教会更深地进入中国社会主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哥林多前书》1:26-28。
<2> 转引自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5页。
<3> 同上,33页。
<4>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298页。
<5> W. M. Ramsay, The Church in the Roman Empire Before A.D.170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3). 转引自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38页。
<6> 伊格纳修,“致罗马人书”,黄锡木主编,《使徒教父著作》,高陈宝婵等译(三联书店,2013),98-103页。
<7> 转引自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39页。
<8> E. A. Judge, The Social Pattern of Christian Groups in the First Century (London: Tyndale, 1960). 转引自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36页。
<9> 同上,37页。
题图是《使徒保罗》(Apostel Paulus),作者为尼德兰画家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茵(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凡·莱茵”意思是“来自莱茵河的”),原作藏于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https://www.khm.at/objektdb/detail/1514。
文中插图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贾吉(E. A. Judge)著《公元一世纪基督徒群体的社会样式》(The Social Pattern of the Christian Groups in the First Century)封面。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2期(2017年夏季号)。如之前所写,《世代》并非一定完全认同分享文章的所有观点。分享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传递的某些信息,是值得反思却被忽视的。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