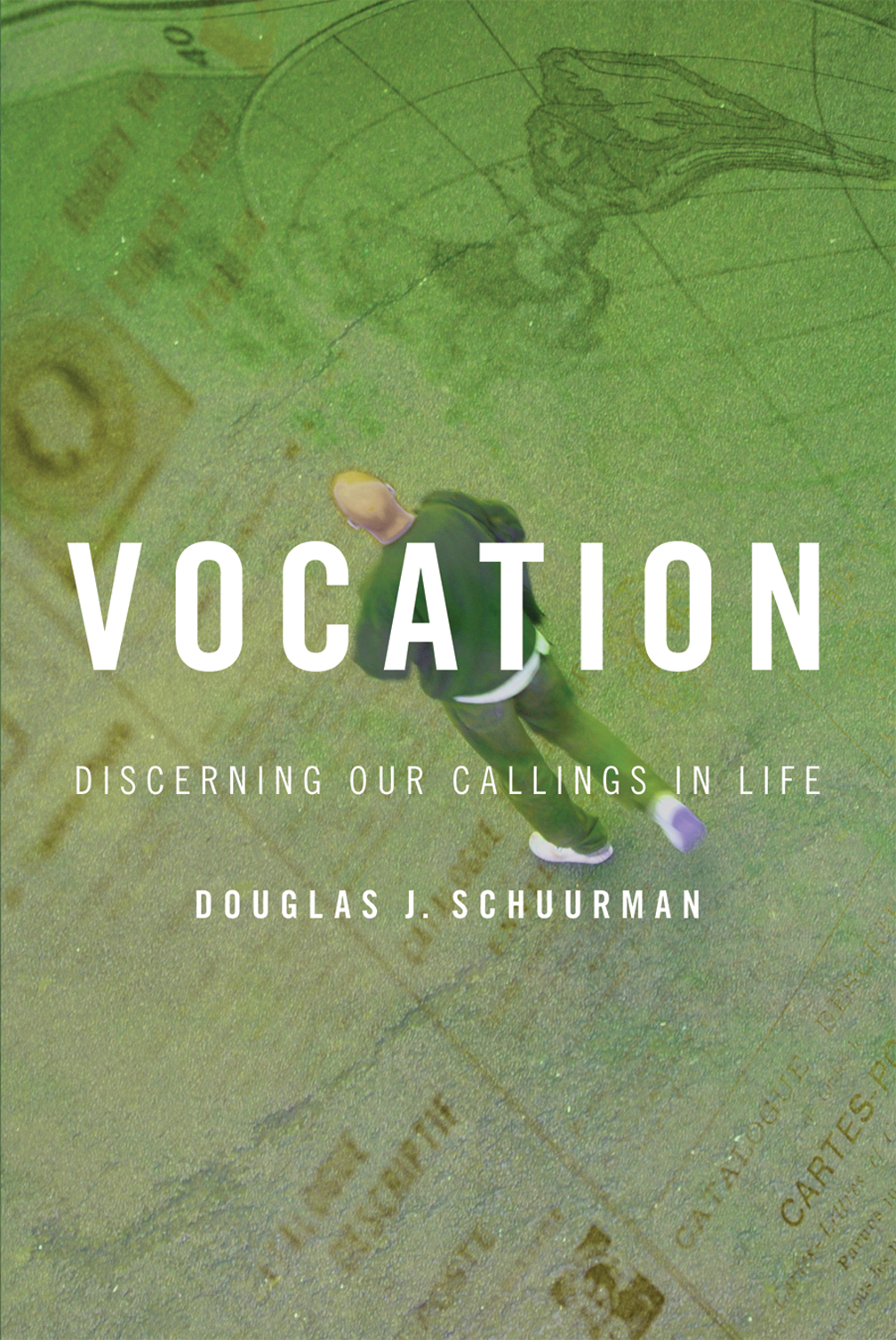
在日常的教牧辅导和基督徒彼此的分享中,有三个恒常的主题:婚姻、子女教育和工作。工作是现代人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尤其在中国这种社会急剧变革和城市化的环境中,工作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维度。甚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现代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对基督徒而言,虽然教会讲道中会涉及这类议题,市面上也不乏各种鼓励将信仰与工作结合、活出见证的书籍,但在现实中,很多基督徒仍然面临信仰和工作之间的冲突和困境,对工作之意义的疑惑总挥之不去。
将信仰和工作融合的书会指导人如何平衡家庭、工作和生活,以及如何在工作中荣耀上帝。一些书籍甚至引用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大力提倡一种“拼命挣钱、简朴生活、拼命奉献”的清教徒工作伦理和天职观。然而,这些现代流行信仰读物并没有提供一种对现代工作体系的反思。
工作意义的起源和发展
劳动作业(工作)是人类社会中最主要的活动。在西方社会早期,有两种主要思想源流塑造着人类的工作观。在希伯来文明中(以旧约为参考),工作(“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是人堕落后受到的惩罚。<1> 同时,因土地受了咒诅,自然资源成为稀缺,上帝将工作的命令赐给人,让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在新约中,呼召通常意味着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和救恩以及做门徒相关,而不是直接和日常的工作有关。<2>
在古希腊传统思想中,人们对劳动和工作普遍持一种轻视和贬低的态度。无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劳动通常是城邦中最下层的人和奴隶承担的任务。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人最终的目的是追求幸福。幸福就是人对这个存在(或者物)自身的一种渴求,是一种行动。在伦理学中,这种对幸福本身的追求,被视为一种最高的德行。但是,这一理念将人的生活分成了两种,一种是自由人的实践生活,包含沉思默想(contemplation)和政治行动,而且沉思要优于政治的参与;另一种是工作和劳动,就是奴隶的生活。在德行的秩序中,因沉思生活追求的就是其本身,它就也是自我满足的、自由的。总之,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沉思生活是一种完美的生活,也就是幸福本身,是人最高的德行的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b)。<3>
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阿奎那,而且在中世纪成为基督教看待工作和人类生活的主要世界观。在阿奎那的观念中,沉思的生活是基督徒最好的生活方式。对于阿奎那而言,基督徒在生活中有两种作为,一种是沉思(包括祷告、默想等等),与爱上帝直接相关。另一种是德行的行动,与爱邻舍直接相关。因爱上帝是先于爱邻舍,所有最好的生活首先是沉思,其次是德行。另一方面,在罗马帝国晚期,为避免教会世俗化,修道主义思想兴起,逐渐形成了各种修道制度。那时,最好的基督徒生活,理应是一种修道主义的避世生活。
一直到路德,教会对基督徒的呼召或天职观才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路德认为,在福音和律法的关系中,基督徒的呼召(vocation)来自于上帝的律法和命令。呼召是基督徒的十字架,迫使他们寻求福音。和基督一样,基督徒在呼召和地上的劳作中,通过上帝的律法,经历了十字架上的死,之后才能通过福音重新复活。如路德神学的权威学者古斯塔夫‧温伦(Gustaf Wingren)所总结的,对路德的神学而言,要“理解呼召的十字架的意义,我们只要牢记呼召是上帝所命定的,不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益处,而是为了实现其他人的益处,为了他人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在这个包括了许多琐碎困难的十字架之下,如:婚姻,养育儿女……” <4> 在路德看来,这些都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支撑,让人学会谦卑。因此,路德强烈批判修道制度,认为修士是逃避上帝的十字架和呼召,既没有爱上帝,也没有爱邻舍,他认为修道制度一无是处,只是人对上帝给予的尘世呼召和工作的逃避,是对属灵争战的逃避。
进而,路德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来自上帝的特殊呼召,每位信徒的日常工作都和牧师的工作一样,是神圣的呼召。如此一来,路德就彻底颠覆了中世纪以来的信仰观念。对于路德而言,沉思生活远远比不上行动的生活。沉思生活不再是最高的幸福,而不过是对现实的逃避。
在有关呼召的思想中,路德强调了一种基于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封建秩序的呼召观,即“基于身份地位”(status-based)的呼召观。在封建时代,人的出身和职业紧密相关,鲜有阶层流动的发生。也就是说,人若出身于农民家庭,就一生都是农民;出身于贵族家庭,就注定一生都是贵族。路德认为,“呼召意味着上帝放在人身边的家庭和工作:是人对于邻舍的爱”。路德强调说,人的出身和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就是上帝所赋予的呼召和责任。一方面,路德强调了牧职的呼召和世俗工作的呼召之间并没有差别;另一方面,路德认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门徒,应当恪守本位,在他们所处的社会身份地位上为福音做见证。如韦伯对于路德工作伦理的总结,路德和路德宗所强调世俗的责任不再次于禁欲苦修,对权威的顺服和对原有社会地位的接受,也在其伦理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是路德反对当时农民起义的神学原因之一。
直到加尔文之后,才出现了一种 “基于恩赐”(gift-based)的呼召观。如果说路德比较倾向于将律法和福音尖锐地对立,加尔文强调的则是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和谐。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来自于上帝,处于上帝的护理之下,也是上帝赐下不同的恩赐给基督徒。因此,人的呼召不是出于律法,而是上帝的恩典。他给予人不同的恩赐,为了能造就教会。这样,人就不必因为出身和社会地位,而被终身禁锢于某一社会阶层中;相反,社会具有了更多的流动性,更加强调,上帝对人类社会的普遍恩典,是通过个人才能的使用造就社会,让个人的天赋得到更好的发展。
现代性对传统工作观的挑战
现代社会体系(也被称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展,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的断裂,也重新塑造了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和价值伦理。在近现代,不仅仅是基督教神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些反基督教的思想也注意到了工作观和现代出现的问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对基督教传统之挑战的立足点之一是“劳动创造了世界”。但是,在现代体系中,出现了人的异化问题,即人不再是他的本质。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之异化具有四重维度:(1)劳动产品的创造者不再拥有他所创造的劳动成果;(2)劳动也不再是人本质的乐趣而成为了负担;(3)人不再是具有尊严和自由的人而是被“物化”;(4)最后导致的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人的关系,而是被工具化。
马克思洞察到了一点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被等同于他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甚至他的工资。 <5> 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挑战,实际上也是对现代教会的挑战:教会如何去面对一个复杂的经济利益机制为导向的社会生产体系?基督徒应该怎样在这样一个现代经济体系中定位自己?
现代教会回应的可能
在一个复杂系统的现代社会中,我们该如何回应和思考工作的意义?我们应怎样从更新性的福音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不只是解决一个神学的问题,更是切实地回应一个当下教会真正的需要。具体而言,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网络工程中的技术人员,高校中的教师,商业活动中的企业家等等,他们应如何看待自己工作的意义?如何处理信仰和工作之间的关系?
在1960年代,基督徒社会学家和神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对传统的基督徒呼召观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是法国社会学家,在学术界以研究宣传(propaganda)和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而闻名。埃吕尔青少年时期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成年后才回归信仰,深受法国胡格诺派传统的影响。埃吕尔基于他对现代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宣传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圣经中谈到呼召时,通常和教会生活有关。但是,圣经很少谈到日常工作是呼召,这就表明,工作的呼召观并不是核心的信息。他的几点看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6>

首先,在资本社会中,很多时候,工作根本无法再反映出做工之工人的真正价值。人甚至简单化地将他获得的工资和收入作为衡量一个人劳动价值的标准。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和人的异化”。在现代社会中,工作的复杂性使得工人已经不再像中世纪和前现代社会那样,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产品,知道它们最终的去向。相反,在现代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之后,人已经无法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自己真实的产品和价值。具有位格尊严的人被简化为非位格性的工具,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刻画的角色一样。人在工作中的异化,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埃吕尔曾说,“这些就意味着人彻底地无依无靠,只能够通过行动将自身异化,被外部的潮流强加在自己的身上。工作不再对应任何内在真实的实在,工作对于工人不是人真正价值渴求的生活——然而这些工作占据了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在这些条件下,很明显,工作对他们根本就不是呼召和使命。” <7>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洞察。我们在现代该如何谈论工作的意义和呼召?工作是否一定要被赋予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把这个问题用在具体场景中,我们可以问:对于很多为了生计挣扎在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周工作至少六天的工人,教会是否还应当教导他们要具有一定的使命感和上帝的呼召,去更加努力工作呢?
其次,更为复杂的是,在现代技术社会中,效率成为首要的工作原则。很多工作已经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像前现代社会那样,通过工作去直接爱其他人,或者对他人抱有同情。在现代生产中,经济绩效和利润成为首要的原则和必要的生存条件。甚至更为严重的是,现代技术社会的复杂性,也从根本上掩盖了我们真正的伦理困境。举一个有助于我们理解的极端例子:一个每天辛勤驾驶火车的基督徒司机,他的工作是否上帝的呼召和真正的使命呢?相信很多基督徒会认同。但是,如果我们在附加一些可能的情形,如果这位司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运送犹太人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一种真实存在过的情况),他的工作是否还可以称为是上帝的呼召呢?我想很多基督徒也会选择回答不是。或者一个不太极端的例子:在网络时代从事某种产业的人员,需要吸引更多的用户,我们也很难一下就分辨出他所从事的是否一件造就他人,有意义的事情。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在现代技术社会中,我们面对的复杂性和技术化所产生的很多后果,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我们也无法衡量一个工作和成果真正对人产生的影响力究竟如何。从伦理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小心地避免很草率地以上帝的呼召和使命的名义赋予工作意义。
此外,即便是职业人士,他的工作也不一定就是上帝的呼召和使命。职业人士(如律师、医生或者教师)本身就应当遵守一些职业的伦理,而不是因为一些人具有呼召才应该遵守。也许我们应回到“普遍恩典”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劳动分工后,各种职业在创造秩序中的责任。另外,我们依旧需要注意的是,职业人士也脱离不了当下的体系和世界观。我们所传递的内容也许是为一个复杂价值体系而运转的基础。我们应当如何面对?
本文不是要彻底否定工作完全不具有上帝给个人的特殊呼召,或现代人的工作不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但是,现代基督徒需要明白的是,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不同于任何以往的社会:技术效率化、体系化、人的工具化、复杂性等等,甚至超越了我们一般人的洞察和理解。我们需要真实地处理各种工作和信仰之间的挣扎、矛盾。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结构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为一种非位格的关系。我们必须用体系化的思维,来分辨这些现实。我们需要认识到工作生活中的异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工作的意义有时只在于提供生存的需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得不做的事情,这让我们无法判断一项工作能否展现出爱上帝、爱人的特性。
今天,在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中,我们需要谨慎地思考和反省工作的意义。这个时代的艰难在于,我们正处于一种伦理的张力中,而且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原则来指导我们。每一天的现实处境需要我们谨慎,以免落入试探;需要我们心怀盼望,对当下有所思考和反省。
<1> 《创世纪》3:23。
<2> Douglas J. Schuurman, Vocation: Discerning Our Callings in Lif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17-63.
<3>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Harris Rackham,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Watt (Wordsworth Classics, 1996), 274.
<4> Gustaf Wingren, Luther on Vocation, translated by Carl C. Rasmussen (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4), 29.
<5> 例如,在20世纪初的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使用“人力资本”这个词在道德上是否正当,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可参考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讨论。
<6> 埃吕尔对于工作的观点,可以参考 Jacques Ellul, “Work and Calling,” in Katallagete 4/2-3 (Fall-Winter 1972)。
<7> 同上,第11页。
题图为此文引用的一本论述呼召的专著封面。文中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照片,来自 Jan van Boeckel, ReRun Producti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acques_Ellul_in_his_studio_(cropped).jpg 。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2期(2017年夏季号)。如之前所写,《世代》并非一定完全认同分享文章的所有观点。分享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传递的某些信息,是值得反思却被忽视的。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