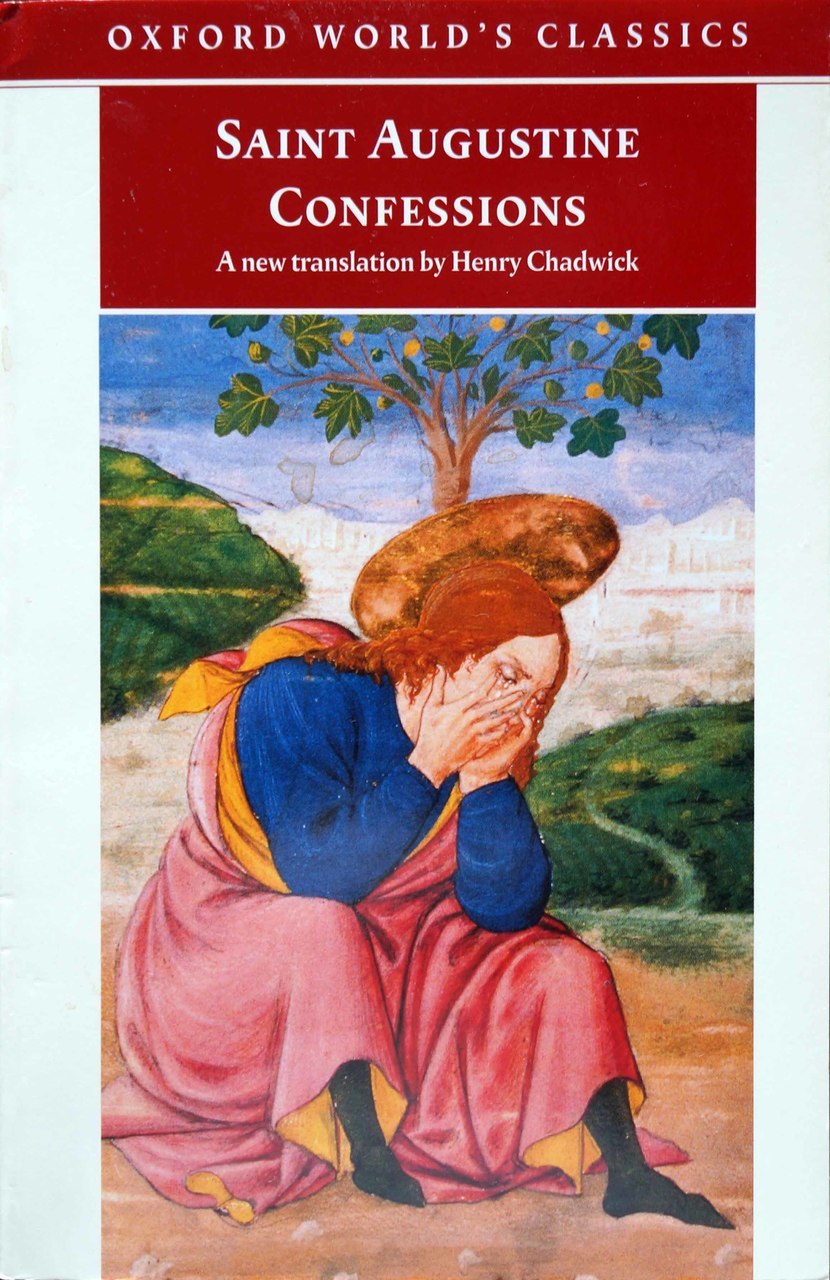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于386年的归信(悔改)是其叙事的中心与高潮。正是在这一年,奥古斯丁开始阅读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如彼得·布朗在传记《希波的奥古斯丁》中所引发的问题,奥古斯丁的归信与其所读的哲学有怎样的关系?在《忏悔录》的叙事中,奥古斯丁自己认为其归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果从一个神学家的归信叙事可以看到他日后的神学特征的话,那么奥古斯丁的这种神学对日后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忏悔录》第八卷的叙事线索,试图回答上述的问题。
一、《忏悔录》的背景与特点
奥古斯丁任主教后两年,大约公元397年,他开始撰写流传后世的《忏悔录》。全书共分十三卷,一至九卷为历史叙事部分,在描述完他母亲于梯伯河口去世这个事件后结束。十至十三卷主要涉及形上学的主题,讨论了如存在、记忆和时间等理论问题。
1、《忏悔录》的写作背景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奥古斯丁写作《忏悔录》的背景。
首先,从外在方面来看,在奥古斯丁被任命为主教的那个时期,当时一些比较保守的北非主教们,一方面非常害怕摩尼教,将其看作是对大公教会有威胁的异端;同时,由于不了解希腊哲学,他们也不喜欢希腊哲学。奥古斯丁这位新任主教,似乎与这两个方面都有着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关系。
就与摩尼教的关系,尽管奥古斯丁脱离了摩尼教后,因那些反摩尼教的作品名声大振,并且在与当地有影响的摩尼教领袖的公开辩论中获胜,以至迫使对方离开了迦太基,但北非教会内的这些主教们仍然不确定奥古斯丁在摩尼教的九年经历究竟对他产生了多深的影响。他甚至还被一位前辈主教指责为“伪装的摩尼教徒”。就与希腊哲学的关系,虽然奥古斯丁是由安波罗修施洗的,但在他的作品中却流露出对异教的新柏拉图主义十分熟悉。在当时的这些北非主教们看来,奥古斯丁似乎太过热衷于希腊哲学,他的归信似乎与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哲学有着难以分离的关系,以至他似乎讲什么都离不开新柏拉图哲学的理论框架。
从内在方面来看,奥古斯丁被任命为主教后,进入到他人生的转折点。在于386年归信之后的几年间,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带给他的影响。但到391年,他在希波城成为一名神父之后,他发现自己需要调整转变,以适应他作为神父以及随后成为主教所面临的新处境。他发现,自己“现在”面临的新处境不仅有他作为主教所承担的责任,还包括他生命在归信基督中发生的转变,这些都迫切地需要他对自己的过去有所清理,好让他对将来有所预备。“我求你,请容许我用现在的回忆回想我过去错误的曲折过程。” <1>
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奥古斯丁写作《忏悔录》的用意: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将“过去”与“现在”关联起来,使其成为一个连续的人生线索,这被视为是对“现在”的预备与面对。当然,这种对人生历程的重述与连接,力求是从圣经上帝话语中来的光照与诠释,而不是出于人自己的理性与思想体系。这一点正如他的传记作家彼得·布朗所概括的:“他与圣经之间的关系就成了贯穿整部《忏悔录》连续不断的主题。” <2>
2、《忏悔录》的文学特点
这本书给今天的读者最为深刻的印象,首先就是它的文学形式:以一个祷告者向上帝祈祷的方式写成。评论者们通常认为,这反映了奥古斯丁信仰生命的敬虔。不过,按布朗的看法,这种文学写作方式也是当时哲学家们普遍使用的一种写作方式,或者说,是哲学探究达到较高阶段的表现,“哲学的探究几乎达到了专心致志祈祷的状态。” <3>
为了证明这一点,布朗举出当时新柏拉图哲学的代表普罗提诺的一段话作为例子:“在勇于探求答案时,我们首先求助于上帝,不是大声向他祈求,而是用一种祷告的方式进行,这种祷告通常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通过渴望使我们的心智一对一地向上帝靠拢。” <4>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激发心智、进行更高哲学训练的方式。在向上帝的祷告与交流中,让人的心智能够与神圣的启示接上,在被光照中更加畅通无误地表达。
不过,对哲学家来说,或许这不过是一种思想的训练,但在奥古斯丁这里,却变成他与上帝活泼的对话,一种内心流淌之情感的表达。两者的区别就在布朗所点出的:“普罗提诺从来就没有像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那样,与上帝闲谈。” <5>
其次,之前的传记,比如之前的北非主教西普里安的传记,主要集中在外来的逼迫,高潮就是主人公最终为基督殉道。而在奥古斯丁生活的那个年代,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已经合法化。所以对奥古斯丁来说,基督徒最凶恶的敌人并不在外部,而来自他们内心之中的罪和怀疑。人生信仰生活的高潮并非殉道,而是从自己过去犯罪的险境中有内在的回转。
当然,《忏悔录》的这个特点似乎也与普罗提诺有某种关系。因为在普罗提诺看来,人需要回到内心的世界,个人“真正的自我”就躺在内心世界的深处。内心世界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世界。它从来不会失去与那无形的型相世界的联系。只是由于人自身注意力的狭隘,才将其与自身潜在的神性隔开。不过,奥古斯丁虽然也力求回到内心,但并没有把人内在的灵魂看得似乎有某种神性。在他看来,内心世界既是力量的源泉,同时也是焦虑的来源,因此对人是一个危险的所在,是人通常想要逃避的。人里面那“经常变化的、无边无际的空间”是如此复杂与冲突,更像是一种迷宫,以至没有哪个人能完全鉴察他的内心世界。
正因为人内心的世界似乎是危险的所在,所以每当出现危机与挑战时,人总是逃向“外面”寻求出路,不愿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冲突与挣扎,里面多种因素的冲突带来让人不能面对的痛苦与不安。正因如此,对奥古斯丁来说,敢于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人,才有可能从中发现上帝:“我在身外找寻你,我找不到‘我心的天主’,我沉入了海底。” <6> 也就是说,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乃是认识上帝存在的主要途径。
把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看作是认识上帝的主要途径,奥古斯丁同时关注人内心呈现出来的那种“灵魂的动力”,正是这种内在的动力推动着人生命与生活的进程。并且,从《忏悔录》中可以看到,奥古斯丁进一步把人的这种内在动力归因于人意志的被激发。
这个内在的激发过程,既与上帝有关系,又与人自己有关系。具体来说,意志依赖于内心的“愉悦”带来的激发,而内心的“愉悦”又被当作是思想和情感神秘结盟的结果。通过这些隐秘过程,意志等到了被“激发”的时刻,更高层面上看,就是上帝之手的推动。
在《忏悔录》中,奥氏异常坦城地分析了自己过去的各种情感。这些情感分析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在这些情感中,最为重要的涉及到两种:哀痛与悲伤。他分析自身情感的主要目的乃在于他对自身意志的关切,就如布朗所看到的:“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的情感呼唤成了更为深入广泛地研究他意志发展轨迹的一部分。” <7>
二、归信叙事的几重要素
单从《忏悔录》第八卷的叙事来看奥古斯丁的归信叙事,可以在这个叙事中分辨出三个重要的因素与线索:
1、在罗马教授修辞学的马里乌·维克托里努斯的故事(2—5章)。
2、同乡蓬提齐亚努斯讲述的埃及安东尼及身边隐修士的故事(6—7章)。
3、奥古斯丁经历的“花园奇迹”(8—12章)。
1、归信叙事的第一重要素
第一重的线索围绕着维克托里努斯。他同样来自非洲,当时在罗马教授修辞学,是奥古斯丁上一辈的学者。他在归信了基督后,将普罗提诺和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作品译成拉丁文,使不太熟悉希腊文的奥古斯丁能够阅读这些作品,并借此了解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如果从普罗提诺于270年去世算起的话,到奥古斯丁读到这些作品,新柏拉图主义已经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经过这一百多年,当时流行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多少带有一些基督教的色彩。
386年初夏,奥古斯丁拿到了维克托里努斯翻译的这些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奥古斯丁深深地被普罗提诺的思想所吸引,这很快就成为他那时思想的框架。正是普罗提诺的哲学思想帮助他最终走出了信奉了九年的摩尼教。对奥古斯丁思想最为重要的改变就是,使他从过去摩尼教的二元论转向新柏拉图主义的一元论。真正的张力存在于围绕着太一发生的“流溢”与“回归”之间的运动:灵魂(内心)回归终极实在,被其充溢,才有实在性。因此,恶并非是独立的实在,不过是善这种实在的缺失。善的力量总是处于主动的地位——这种力量流出来,触及一切,塑造所有被动之物并赋予其意义,而自身不受任何的损伤和消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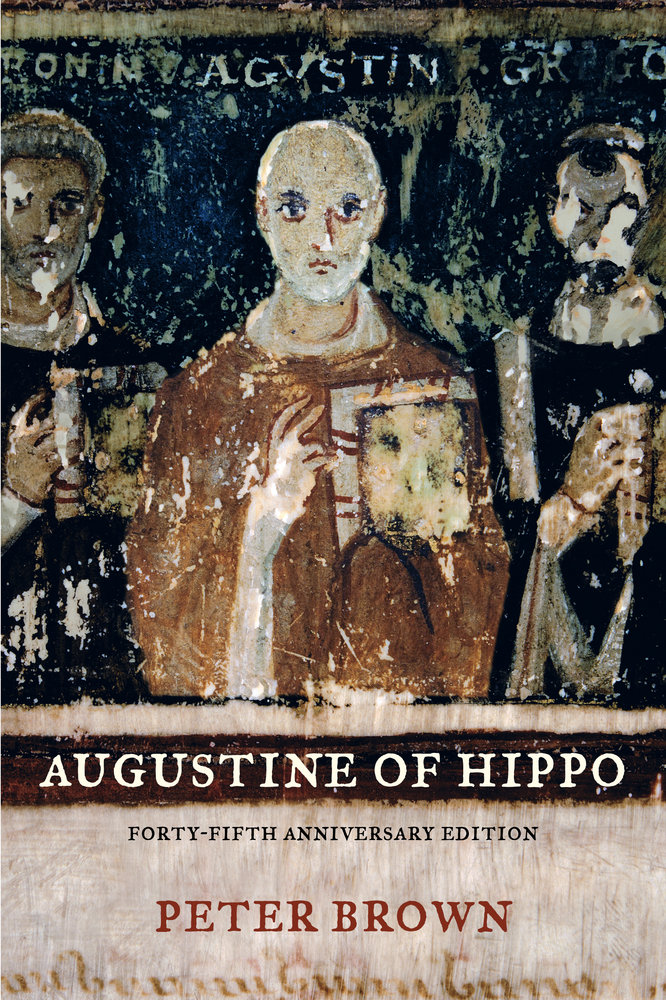
布朗认为:“奥古斯丁阅读了普罗提诺的著作,这产生了一个人人都知晓的后果:使奥古斯丁从以文学为生最终‘皈依’哲学。” <8> 这个看法似乎也可以从当时奥古斯丁的表述中得到某种印证。奥古斯丁在归信前一两个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哲学的渴望,除了我们都赞同的那种生活,其余我们一概不加考虑……它强大得超出了我的想象。经过这件事之后,荣誉、人生的虚饰、对空洞虚名的艳慕、现世的慰藉和吸引又怎能让我心动?” <9>
这就引发如下的问题: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哲学与奥古斯丁的归信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哲学是否奥古斯丁归信的最主要因素?下面,就让我们从《忏悔录》第八卷的叙事中来寻找答案。
《忏悔录》八卷开篇提到,奥古斯丁受到启示,向曾给安波罗修施洗过的希姆普利齐亚努神父请教:“这时他年事已高,我想,他一生都恪守你的道路,我相信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事实确实如此。因此我愿意就我的疑难向他请教,请他以我当时的心境,指示我最恰当的方法,来走你的道路。” <10> 而希姆普利齐亚努神父告诉了他下面这个故事:
最初,维克托里努斯只在私下场合向希姆普利齐亚努说:“你知道吗?我已是基督的信徒了。” 希姆普利齐亚努回答:“除非我看见你在基督的圣堂中,我不相信、我也不能认为你是信徒。” 虽然当时维克托里努斯笑着回答说:“那么墙壁能使人成为信徒了!” 但这故事的结尾是:维克托里努斯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后,最终在希姆普利齐亚努的陪同下走进教堂,在众目睽睽之下,上台公开宣告认信、接受洗礼。“这事在罗马引起了惊愕。” <11>
希姆普利齐亚努神父用这个故事来回应奥古斯丁的请教,并且被奥古斯丁记在《忏悔录》里。或许是奥古斯丁已经认识到,与当年的维克托里努斯一样,虽然让他们感兴趣的是哲学,而不是问题多多的教会,但真正让人成为基督之信徒的却是后者。
2、归信叙事的第二重要素
《忏悔录》第八卷讲述的第二重线索围绕着同乡蓬提齐亚努斯的拜访,以及他所讲述的埃及安东尼及米兰城边隐修士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无论是更早的安东尼还是当时他的那两个高官同事,果断地放弃已有的财富与地位而成为修士,给奥古斯丁带来极大的冲击力,挑战他良心中存在的自欺,看到自己里面的虚假:一方面以为自己是热爱智慧的,可以为之舍弃一切;另一方面却贪恋欲望,并没有勇气义无反顾地当即放下这种被欲望支配的生活。这让奥古斯丁无法面对自己。从随后发生的“花园奇迹”之过程中,安东尼故事发挥的提醒作用,可以让我们看到安东尼的故事对奥古斯丁内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这里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种关联就是:追求智慧与人的生活方式有着紧密联系。隐修生活是寻求智慧的最重要及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意味着放弃婚姻与财产。接近于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出家”观念。对奥古斯丁来说,最难的是放弃两性的关系。无法摆脱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感到十分的挣扎与无助。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放弃对隐修生活的向往。
385年,奥古斯丁还在米兰,他所在的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小团体,曾经考虑过一种“完美的生活”,即将资源合在一起,以便他们能像朋友那样过一种隐修的生活。这个计划没有实行,主要是遭到当中几位妻子们的反对。
将追求智慧与过隐修生活联系起来,这在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有点不可理解。但这却是古代社会流行的观念。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当时的教会。在罗马帝国晚期,人在教会中接受过洗礼,就意味着不能再犯罪。而过一个完全的生活,就意味着进入隐修的生活。
3、归信叙事的第三重要素
公元386年6—7月,在希姆普利齐亚努斯以及安波罗修的影响下,奥古斯丁开始认真地研读保罗书信。《忏悔录》八卷6章,在同乡蓬提齐亚努斯前来拜访的叙事中特别提到,这位同乡在奥古斯丁书桌上看到的唯一一本书就是保罗书信。
那天下午,同乡不仅讲到了安东尼,还讲到身边的同事在米兰城边当时就选择成为修士的故事。在同乡走了以后,奥古斯丁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大声向神哭喊:“还要多久?还要多久?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就结束我罪恶的过去?” 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童音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这声音提醒他回到屋中,翻开保罗书信,眼睛最先看到《罗马书》下面两节经文:“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12> 这里,奥古斯丁说,当他读到这话的时候,一道恬静的光直射到他的内心里,驱散了所有疑惑的阴霾。<13>
这个故事在历史上被称为“花园奇迹”。然而问题是:这个“花园奇迹”奇在何处?有人会马上想到奥古斯丁当时所听到的那个童音。其实仔细想来,更神奇的应该是伴随着他所读到的那句话语而直射到他内心的那道“恬静的光”。然而,要想理解那道“恬静的光”在他的内心中所产生的奇妙的作用,只有回到《忏悔录》八卷的叙事中,看其对保罗书信的领会才有可能理解。这也正是《忏悔录》八卷叙事的核心线索。
在《忏悔录》八卷有关这个因素的叙事中,可以看到奥古斯丁试图从保罗书信的角度来理解他所关心的人内在意志的问题。奥古斯丁从保罗《罗马书》来看自己长久以来内心的挣扎,根源都与其意志的受缚有关:“这些关系的连锁——我名之为铁链——把我紧缠于困顿的奴役中。我开始萌芽的新的意志,即无条件为你服务,享受你天主,享受唯一可靠的乐趣的意志,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压伏根深蒂固的积习。这样我就有了一新一旧的双重意志,一属于肉体,一属于精神,相互交绥,这种内讧撕裂了我的灵魂。” <14> 这里,奥古斯丁在对自己意志之挣扎的分析中,他直接引用到《罗马书》7章的描述:“我的内心喜爱你的法律是无济于事的,因为 ‘我肢体中另有一种法律,和我心中的法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顺从肢体中犯罪的法律。’ 犯罪的法律即是习惯的威力,我的心灵虽然不愿,但被它挟持,被它掌握;可惜我是自愿入其彀中,所以我是负有责任的。” <15>
与包括新柏拉图主义在内的希腊哲学传统有所不同的是,因为基督信仰的影响,奥古斯丁并不把人犯罪的根源仅仅归咎于身体的欲望,而是更深地追究到人的灵魂,具体就落在人的意志层面。由于人的意志已经被罪所腐化,所以人理性以为应该做的事情,意志却并不一定有能力做到。在此,奥古斯丁对于灵魂自律有着深刻洞察:“这种怪事是哪里来的?原因何在?灵魂命令肉体,肉体立即服从;灵魂命令自己,却抗拒不服。……灵魂命令灵魂愿意什么,这是命令自己,却不见动静。” <16>
对于人的灵魂没有能力达到自律的深层原因,奥古斯丁给出了更进一步的说明:死亡或者对死亡之畏惧带来的限制:“我再鼓足勇气,几乎把握到了,真的几乎得手了,已经到了手掌之中,入我的掌握了。不,不,我并没有到达,并没有到手,并没有掌握;我还在迟疑着,不肯死于死亡,生于生命;旧业和新生的交替,旧的在我身上更觉积重难返;越是接近我转变的时刻,越是使我惶恐,我虽并不因此却步,但我不免停顿下来。” <17>
在由保罗书信提供的有关人内在意志被罪束缚的背景下,我们来看“花园奇迹”奇在何处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忏悔录》八卷的叙事所带出来的一种解释:首先,上帝话语带进来的那道“恬静的光”具有光照与医治的作用;这股从外而来的力量(恩典)帮助奥古斯丁胜过了人性中的罪对意志束缚,使内心新生的意志有力量。这力量具体体现在:上帝的话在他内心“驱散了所有疑惑的阴霾”,不再有疑惑与犹豫。其次,被释放的具有力量的意志乃是不再疑惑、全心全意的意志,这种完全的意愿才会被灵魂所听从,从而化为人的行动。与他对恶的看法联系起来,如果恶是善的缺乏,那么当人一心二意、不能全心全意的时候,就落入到罪之中,就如保罗所说的,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18>
三、从归信叙事看奥氏神学
如果一个神学家的“归信”过程或叙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神学的特点,那么,从奥古斯丁归信的叙事,可以看到他神学救赎论的基本特征:恩典的神学。就是说,这种救赎论强调人归信的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1)通过上帝话语的光照,从人之外而来的救赎恩典;2)恩典对人里面意志的医治与更新,决定了人内心生命的重生。
如果奥古斯丁的神学救赎论具有恩典论的特点,那么从这种恩典论回顾奥古斯丁归信叙事中与新柏拉图哲学的关系,其间具有怎样的张力关系?如前所述,对布朗来说,奥古斯丁在其归信过程中同时受到普罗提诺与保罗作品的影响,两者在奥古斯丁归信过程中似乎并没有显出太大张力:“目的感和连续感是奥古斯丁‘归信’最为显著的特点。考察他在卡西齐亚库所写的作品,这次归信似乎是一个平稳得让人吃惊的过程。尽管奥古斯丁的‘哲学’生活被圣保罗(的作品)所充斥,但仍然能够用古典的语言加以表达。” <19> 或许对当时奥古斯丁本人来说,保罗书信与普罗提诺哲学、基督信仰与古典文化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正因此,他才将基督信仰(神学)看作是“真哲学”。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奥古斯丁可能也没有想到,多年后人们才认识到,他的恩典论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区别有多大。在布朗完成了他的奥古斯丁传记三十年后,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区别:“奥古斯丁的恩典论对帕拉纠的自由意志论(其根源在于古典的、斯多葛派的思想)的胜利是古代社会在西欧终结的标志……对奥古斯丁而言,借用圣保罗的观点标志着那种古典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独特认识的结束。在归信的过程中,奥古斯丁也曾公开发表过这种认识。” <20> 布朗把这种区别描述为一个更为阳光、乐观的古典思想与被原罪思想影响的更为阴郁、悲观的基督教思想的区别。
恩典论中所包含的对人自由意志的看法无疑是奥古斯丁思想与希腊哲学思想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被后代的基督教思想家所继承。如加尔文所说,希腊哲学家与基督教思想的主要差别就是:前者直接忽略人的罪,并不把亚当的堕落当作认识人及其社会历史的基本前提,仍然从人自身寻求人类进步与发展的源头与动力。<21>
然而从亚当堕落的前提下来认识人的本性并不必然导致对人及社会进程的悲观意识。其实,布朗眼中的奥古斯丁是矛盾的:“总而言之,在通过自己作品就人类总的状况发表评论时,奥古斯丁错误地表现出了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在布道和教导他的公教追随者时,他又错误地表现出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 <22> 或许站在古典哲学的立场上,确实不太容易理解奥古斯丁思想中的这种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交织。
总之,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八卷所展现出来的归信叙事中,向我们描述了三重因素,其中保罗书信(圣言)无疑占据着最为重要的角色。由此,从奥古斯丁归信叙事中呈现出来的恩典论神学特征说明:奥古斯丁归信叙事中虽然有普罗提诺哲学的重要影响,但从叙事中也能看到,奥古斯丁的思想始终与希腊哲学有着某种张力。
<1> 奥古斯丁,《忏悔录》,IV, 1, 1。中文本参见周士良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英文版参见: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Henry Chadwic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钱金飞、沈小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3页。
<3> 同上,第186页。
<4> Plotinus, Ennead, V, i, 6. 转引自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186页。
<5> 同上,第203页,注61。
<6> 奥古斯丁,《忏悔录》,VI, 1, 1。
<7> 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192页。
<8> 同上,第109页。
<9> 同上,第109页。
<10> 奥古斯丁,《忏悔录》,VIII, 1, 1。
<11> 同上,VIII, 2, 4。
<12> 《罗马书》13:13—14。
<13> 奥古斯丁,《忏悔录》,VIII, 12, 29。
<14> 同上,VIII, 5, 10。
<15> 同上,VIII, 5, 12。
<16> 同上,VIII, 9, 21。
<17> 同上,VIII, 11, 25。
<18>《罗马书》14:23。
<19> 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120页。
<20> 同上,第585页。
<21>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I,1,2,钱曜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22> 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599页。
题图:
《忏悔录》亨利·查德威克(Henry Chadwick)译本封面,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https://thebookendaz.com/confessions-oxford-worlds-classics/。
插图:
彼得·布朗(Peter Brown)《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封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https://www.ucpress.edu/book/9780520280410/augustine-of-hippo。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9期(2019年秋冬合刊)。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9期主题是“如何做研究”,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世代Kosmos);
网站(kosmoschina.org)。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