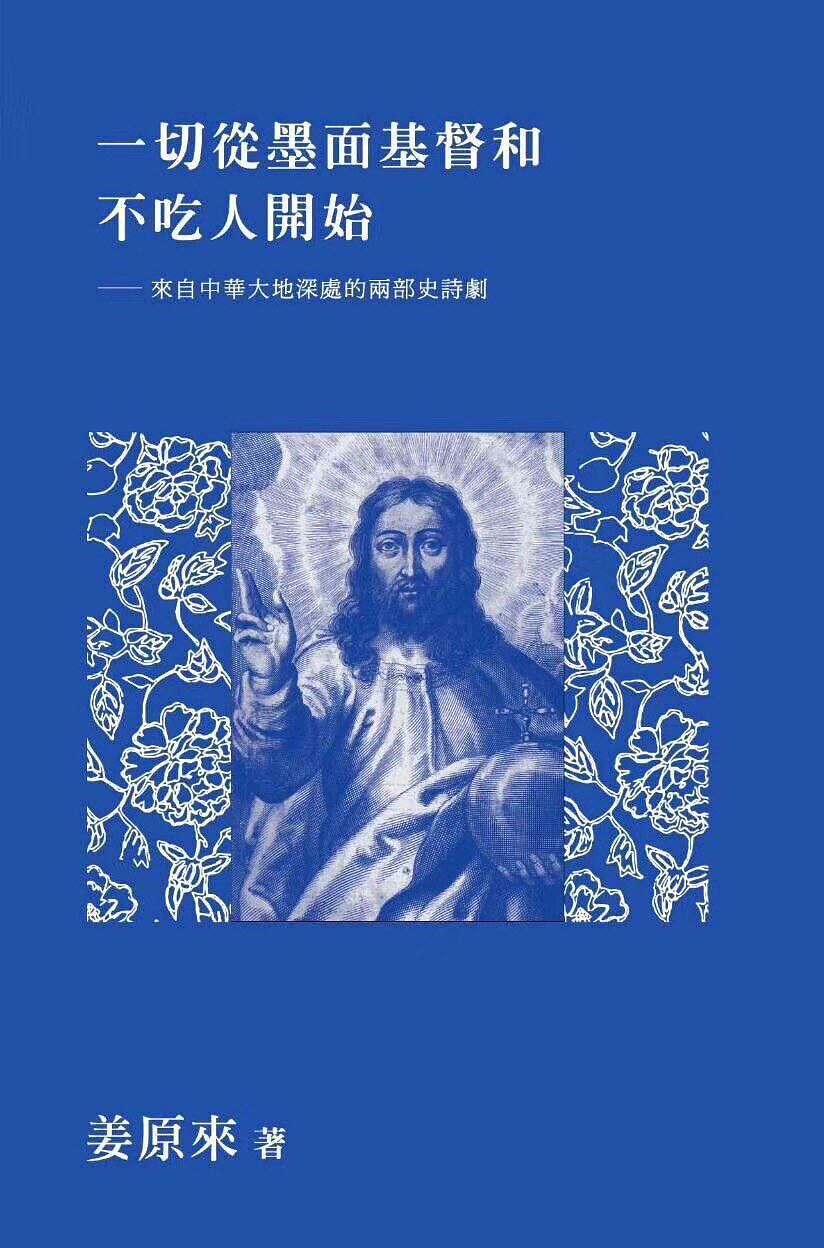
姜原来的戏剧《兰林复活节》,是近年来出现的思想与艺术俱佳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品。在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上,较之诗歌、小说等体裁,戏剧一直不甚发达,姜剧可谓难得的弥补。
尤为难得的是,姜剧承接新文学中鲁迅的宝贵传统,进一步思考当下国民性的破口与出路,既表现出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推进,也呈现出与主流文学的对话能力。
姜剧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本色化探索中也做出了积极尝试。墨面基督的塑造丰富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处境化意义,而其创作中体现的文学水准,摆脱了常见的宗教戏剧的模式化,堪称近年来中国基督教文学鲜见的力作。
一、接着说:承接鲁迅的传统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在艰难时世中,基于部分文学家和众多不广为人知的作者的努力,在诗歌、小说等领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提升了中国文学的灵性品格。
基督教作为新文学的思想资源之一,也为不少主流作家提供了创作灵感,包括鲁迅、茅盾等在内的文学家,均有取自《圣经》题材的作品留世,基督教爱与牺牲的精神也成为他们剖析国民性、思考民族出路的参照。
基督教精神对鲁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也吃过人”的忏悔意识和“肩住黑暗的闸门”的牺牲精神。《兰林复活节》中引用了鲁迅的诗句“万家墨面没蒿莱” <1> 。鲁迅对万家墨面深切的爱与痛,表现在阿Q、祥林嫂、闰土这些人物身上。几十年后他们的后代生活得如何?他们的精神问题解决了吗?他们或许在物质层面得到了某种解放,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可能成了另一种奴隶,依然在想作奴隶而不得和暂时作稳了奴隶之间挣扎。
如今这些万家墨面的出路在哪里?身处底层山野的兰林团契自建立之日起,便恪守三条做人底线:一是竭力不被人吃,二是坚决不吃人,三是要纪念遭苦害的人。这三条底线是当年建立团契的沈老牧师和钱老神父和团契成员定下的。
剧中裴牧师曾一一介绍这三条底线:“老牧师说,主造人爱人,主爱护人在祂里面活着。我们兰林人就像这树,虽然长的地方艰辛,还是盼着在主里好好站着活着。可是世界魔鬼横行,人活在这世上,第一不得不防着不让人坑不让人吃,这合情合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第一条底线—恪守——尽力不让人吃了!老牧师说的多简单实在啊。” “我们不仅尽力不让人吃……我们更要坚决不吃人!坚决不要卷入骗人坑人吃人的任何事情里,坚决不干!” <2> 如剧中戴明所说:“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吃人的本性、吃人的冲动甚至吃人的无可奈何” <3>,但兰林团契基于信仰,立志过不吃人也不被人吃的生活,这是对鲁迅精神的可贵继承。
谈及第三条底线时,裴牧师回忆他跟着沈老牧师出门救助临终流浪汉的经历,感慨“大地上的苦难太多了受难者太多了可是残酷的否定彻底的遗忘也太多了,我们基督徒不去纪念他们谁去纪念他们?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为了主的怜悯和公义,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纪念他们。” <4> 从不被人吃和不吃人到纪念遭苦害的人,体现了基督徒由己推人积极的社会担当意识,也是对圣经中“爱人如己”、“爱邻舍”信条的践行。该剧最后,作者藉戴明之口,指出从“不吃人神学”到“牺牲神学”,兰林团契有本土神学的宝贵积累,值得进一步了解。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股支流,面向中国大地上的万家墨面,藉助文学形式开出的药方并未被主流文学接受。除了沉重的现实以及“ 非基督教运动”等历史因素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缺乏与主流文学的对话。在这一点上,姜原来的《兰林复活节》呈现出对鲁迅传统的积极承继,从而使得中国基督教文学有能力回应主流文学的思考,并推动中国基督教文学摆脱文学边缘状态,主动介入对国民性的思考和建设这一历史责任,这种历史担当是值得尊敬的。
二、墨面基督:苦难中的临在
《兰林复活节》中的兰林不是乌托邦的世外桃源,而是与广大苦难世界紧密相连之地。在人类的苦难中,上帝在哪里?这是姜剧藉人物之口发出的追问。类似追问我们在日本远藤周作的名作《沉默》中也看到过。较之《沉默》中答案的晦暗不明,姜剧给出了清晰的回答,这些苦难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5> 。正如剧中裴牧师所说:“不是在神学院的林荫道上,而是在穿过这样历史现场的十字架路上——这样的路上,需要简朴清贫的生活,需要担当苦难,有时候甚至要像广锁弟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为主殉道。因为,这样的十字架路纪念遭苦害的人,也‘忍受祂所受的凌辱’、‘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6> 。这是中国基督徒的信心表白,也是以文学的形式对苦难的回应。
基督形象在中国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基督故事”作为基督教传统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背后传递出不同写作者对于基督的独特认知。包括赵紫宸、朱维之等文学家在内,都曾有过相关著述。<7> 这一问题也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回顾民国基督教史,我们会发现耶稣形象大量出现在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著述中。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以‘中国基督徒’的身份,使用民国处境中的本地叙述,将原本从西方传来的耶稣,改造或重塑为本色化的耶稣或处境化的耶稣。他们不仅关注历史上的耶稣是谁,他曾做什么,而且也同样关注对于当时当地的中国人而言耶稣是谁、他会做什么” <8> 。
考察中国基督教文学,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本色化之努力。王治心在讨论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时时,曾用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落花生”。“花生”在中国本是称为“洋花生”,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食用的花生最早是从外国进口的。但经年累月后,花生已可以在中国的土壤里培养和栽植,即吸收了中国土壤的养料而成为了中国本土培植的花生了。<9> 身为中国人,本色化似乎是一个无法完全绕开的问题。而基督形象在中国文化的扎根是本色化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
姜剧中的基督形象,为当代中国基督教文学贡献了一个处境化的墨面基督,这个墨面基督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中的基督形象是息息相通的,也是与中国的万家墨面息息相连的。他临在这片广大而苦难深重的土地,不是以得胜荣耀君王的面目出现,也“无佳形美容” <10> ,他与苦难中的生命一同叹息,一同劳苦,一同受难,好使他们从他的同在中得安慰,得力量,得盼望,如同剧中兰林团契木门上贴着的对联“登高高山林朝见墨面造物 行深深大地亲历宝血救主”,横批“永生之道十架路” <11> 。
墨面基督同在的墨面信徒,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生命状态,即有信有望有爱的天路历程。姜剧中凸显了在可怖的堕落世界衬托下的令人向往的世界。
这种凸显不是教条式的,而是基于活生生的信仰实际,感人至深,比如剧中的广锁妈这一形象。沈老牧师、广锁妈和广锁一家三代,是兰林一带专心救人的奇迹。但广锁一家又是苦难的聚集地,广锁的父亲和舅舅都是木匠,在广锁出生那年,一同到北边去干活,正赶上军队进城,广锁父亲中流弹死了,广锁舅舅也失踪了,二十几年没有下落。广锁为了给疯弟兄凑钱治病,跑到煤窑打工丢了命。遭遇诸多苦难和不幸,广锁妈依靠在苦难中与人同在的基督,对那些陷入苦难中的人感同身受,并有从主而来的安慰人、赶鬼及医治的特别恩赐。她怀着广大的爱心,接纳所有来到兰林的被世界弃绝的病人、疯子,照顾医治他们;山上山下方圆一带,谁心里有苦都会来找广锁妈倾诉,请她代祷。如同裴牧师所说,“要不是上帝的恩典,要不是亲身经历,现代城里人根本无法想象乡野底层有这样的生命” <12> 。
当然,作者并没有人为拔高,不同信众表现出灵命的状态有高有低。我们在其中看到了疯子、神经病人、中途离去又回来的人……这让我们想起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身边的人,多为人所厌弃的罪人,但正如耶稣所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13> 。其实谁不是病人呢?正如广锁妈所说:人人都是罪人。认识到有罪的人才需要救赎,就连那个打算杀人的保镖,也因听了牧师的话有所惧怕和醒悟。但若拒绝救赎,终究难免沉沦,比如叶老板发疯后的嘶喊:“这里有人吗?……还有人吗?人,死啦……”<14> 令人毛骨悚然。而整日狂喊“……打仗啦……吃人啦……见不到俺娘啦……”的疯子却最终喊出“主复活了!主果然复活了!人有救啦!” <15> 令人欣慰。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姜剧兼具历史感与现实感。
其历史感集中体现在由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十二户人家组成的大家庭——兰林团契。该团契既有明清时代天主教传教史的痕迹,也有近代以来新教史的印迹,还融入了东正教的些微果子。大家既在一个大的兰林团契中,也保留了各自平时的敬拜传统,相安无事,且互相照应,算得上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基督化社群。这一以圣爱为联结的大家庭式的基督化社群,反映了基督教会在华的久远历史和丰富遗产,也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尊重。
其现实感体现在山下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而这种现实生活又与山上信仰群体不断发生互动,从而使得山上生活充满张力,免去了一些基督教文学作品中因主题先行而常见的刻板化,也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悟能力以及基于信仰的应对能力。
三、文学性:基督教文学的立足点
基督教文学之所以为基督教文学,一个基点在于其文学性。若是没有艺术,单单成为思想的传声筒,便失去了文学的价值和力量。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上曾出现了很多作品,因为缺乏足够的艺术性,难以进入到文学史中,出现不久便被湮没了。姜剧令人振奋的是,不仅在思想上有足够高度,在艺术上也是值得称赞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16>,这是基督教文学创作者不应忘记的训言。
中国基督教戏剧较之诗歌、散文和小说等体裁,一直不甚发达。民国时期的基督教戏剧作品多散见于《真理与生命》、《女铎》、《金陵神学志》、《基督教丛刊》等一些基督教刊物,且多为应景之作的圣诞剧目。
其中有1944年圣诞节期间在沦陷区天津上演的大型清唱剧《圣诞曲——基督降生神乐》(Christmas Oratorio——Song of the Holy Nativity)。《圣诞曲》的歌词作于1944年7月21-23日,是赵紫宸根据圣诞故事,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风格。其音乐则由作曲家张肖虎于1944年9-11月间创作。《圣诞曲》借用以色列人遭受罗马侵略的历史事件,来表现中国人遭受日本侵略,实际上是一部宣扬爱国主义的宗教作品。<17>
《兰林复活节》虽然从题材上看仍是传统的基督教节日剧目,但却是在生动活泼的现实层面铺陈情节刻画人物的,因而跳出了一般节日剧的简单刻板,富于文学表现力。
就结构设计而言,该剧采用了“山上-山下”的对照结构,既有现实的也有属灵的含义。“山上”在《圣经》中有特别的寓意,常指向上帝的同在。亚伯拉罕上摩利亚山,摩西上西奈山,以利亚上迦密山,乃至基督也常常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并带领门徒到山上去,显出荣耀的本相……诗人大卫更是发出“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18> 的绝唱。
在《兰林复活节》中,信徒们在“山上”过复活节,享受上帝同在的平安喜乐;与此相对,“山下”却常常显出罪恶的狰狞面目。而那些在山下挣扎的人们,常有从“山下”到“山上”的皈依历程,“山上”显然是希望之地和盼望之所。
就人物谱系的设定而言,姜剧虽然接着鲁迅的万家墨面讲述,但这些当代的墨面们却并非简单重复以往的形象,也是具有个性化的“这一个”,而不是生硬的传声筒式的标签人物。
这得益于作者长年累月深入实际生活,细致揣摩不同人物的内在性格。不同人物有各样的语言风格,而非千篇一律的作者自说自话。比如该剧中的知识分子、牧师、村民、老板、疯子……各具特色,显示出作者塑造人物锤炼语言的功力。其中城市基督徒知识分子戴明时常充当作者的代言人,语言富有思辨和哲理意味,对家的追寻把他导向了兰林,在那里他找到了有上帝活生生同在的家,决定委身兰林团契。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作者在该剧中设置了种种冲突,有山上和山下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山下不断以各种方式侵入山上的平静生活。
一开始是山下要和山上终止山林承包合同,要把山上人迁下山,并派工程队炸山开矿。原本80年的合同,过了20几年就要随便毁约。山下的社会风气极其恶劣,村民下山卖山货,常遇到黑社会打人抢东西。
剧中也有不同人物之间的冲突,比如通过两个牧师的冲突揭示信仰的真伪。郭牧师和裴牧师曾是神学院同学,后来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郭谷看来,祝福平安才是上帝临在的唯一证明,据此他认为兰林是基督抛弃之地,兰林人是“野地刁民”、“乌合之众”。在他与戴明的对话中,他透露自己掌握了“两全其美”的处世艺术,“做一切事情都让上帝和我自己的根本利益两全其美,达到这种本来就存在的两全其美境界,这就是生活的艺术。幸运的是,我掌握了这种最微妙的艺术。” <19> 郭谷这种利用上帝为自己服务的所谓两全其美,用叶老板的话说:“说穿了,你也是生意人,拿上帝做生意,拿信徒做市场顾客” <20> 。作者藉助郭谷这一形象,讽刺了所谓的幸福神学和信仰上的投机主义。
裴牧师和广锁妈都是兰林团契的带领人,但他不同于广锁妈的土生土长,他是神学院毕业之后,跟着老牧师老神父来到兰林服事的。在带领兰林团契的过程中,他尽心竭力,赢得大家尊重。同时作者也写出了裴牧师内心的孤单与痛苦,特别是广锁遭难一事,让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深夜中的独自祈祷透露出他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灵性黑夜。郭谷实在无法理解自己的老同学,甘心情愿陷在“一群乌合之众的泥潭”。但裴牧师始终坚持和这些“一帮子跌跌撞撞认罪悔过的罪人” <21> 在一起,因为“基督就在这样的人群里服侍生活” <22> 。当郭谷指责他疯了时,裴牧师反驳说:“世界才真正疯了,只有疯子才能在这样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应付自如,只有真正的疯子才能在这样的世界里聪明成功。” <23> 裴牧师宁愿做兰林的疯子,也不愿做聪明世界里的正常人,显示了他追随墨面基督的坚定心志。最后,他经过考虑,决定不去国外神学院读书,而是继续留在兰林团契,因为他的使命在这里。无疑,裴牧师是有清晰异象与使命的年轻一代牧师的典型,也是当下教会的宝贵财富。
剧中叶老板的到来,也凸显了冲突。叶老板是萧红老乡,年轻时不但喜欢萧红,自己还写过小说,后来下岗去深圳做生意,再移民加拿大。正因为她身上的一点文学性,裴牧师一开始相信了她,劝大家接受她的开发建议,没想到她骗走了裴牧师所有的钱,还振振有词说这是“交往成本费”。她在兰林这个立志不吃人也不被人吃的地方,却肆无忌惮地继续骗人吃人。复活节前夜,她也参加了复活节活动,内心被撕裂成两部分,在爱与恨中纠结,最终还是倒向虚无,拒绝救赎,彻底发了疯,与另一个在复活节得医治的疯子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始终关注女性的命运,曾提出“娜拉走后怎样?” 他也曾被祥林嫂问过离开这个世界后会怎样?关于前者,他指出女性解放必须有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作保障,女性如果不愿作玩偶,必须赢得经济权,否则娜拉出走后要么回来继续作玩偶,要么饿死或堕落。今天女性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经济权,改善了自身地位,但经济权的获得不能代替灵魂问题的解决。
剧中的叶老板在经济上极有发言权,自以为已经生活在钱的天国,灵魂上却比祥林嫂还要贫瘠,且时常陷入疯态。复活节前夜,她嫉妒那群“可怜虫”都有爱的能力,承认“我在这个世界上钱再多也没有你们富裕,我就是用钱靠科学技术保持了美白实现了永生,也不过是一具没有爱的美丽活尸” <24> 。鲁迅当年悬置了祥林嫂的灵魂问题,或许他无力回答,或许不想回答。这一问题在《兰林复活节》中被接着问,“一个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灵魂又有什么意义” <25> ?而这个答案无疑指向墨面基督的救赎。
此外,姜剧的舞台感很强,人物对话、动作设计没有雕琢痕迹,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演出实践经验。特别是背景音乐表现力强,这与作者的音乐修养息息相关。
<1> 全诗为:“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详见:鲁迅,《集外集拾遗·戌年初夏偶作》,《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2页。关于“墨面”,参见:《淮南子·览冥训 》,“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详见:何志华、朱国藩编著,《唐宋类书征引<淮南子>资料汇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0-91页;也参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典论》,“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以为死者有知,当复见绍于地下,乃髠头墨面以毁其形。”
<2> 姜原来,《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来自中华大地深处的两部史诗剧》,香港:手民出版社,2017年,第64-66页。
<3> 同上,第91页。
<4> 同上,第118页。
<5>《歌罗西书》1:24。
<6> 姜原来,《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第120页。
<7> 赵紫宸,《耶稣传》,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朱维之,《无产者耶稣传》,上海:广学会,1950年。
<8> 王志希,《当中国遇上耶稣——1949年之前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耶稣形象研究述评》,《新史学》第26卷第4期,2015年12月,第227-258页。
<9> 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第79册,1925年1月,第11-16页。
<10> 《以赛亚书》53:2。
<11> 姜原来,《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第10页。
<12> 同上,第42页。
<13>《路加福音》5:31。
<14> 姜原来,《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第200页。
<15> 同上,第200页。
<16> 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7> 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72-773页。
<18>《诗篇》121:1-2。
<19> 姜原来,《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第97页。
<20> 同上,第72页。
<21> 同上,第110页。
<22> 同上,第111页。
<23> 同上,第111页。
<24> 同上,第176页。
<25> 同上,第180页。
题图:
姜原来《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封面:
http://www.cinezen.hk/?page_id=8020;
《世代》用图版本来自: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subject/l/public/s29849628.jpg。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世代》对收到的原稿进行了编辑,包括对正文及注脚的修订或删改或补充。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世代》文章,请尽可能在对作品内容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世代》第6期主题是“启蒙”,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欢迎访问《世代》网站:www.kosmoschina.org。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