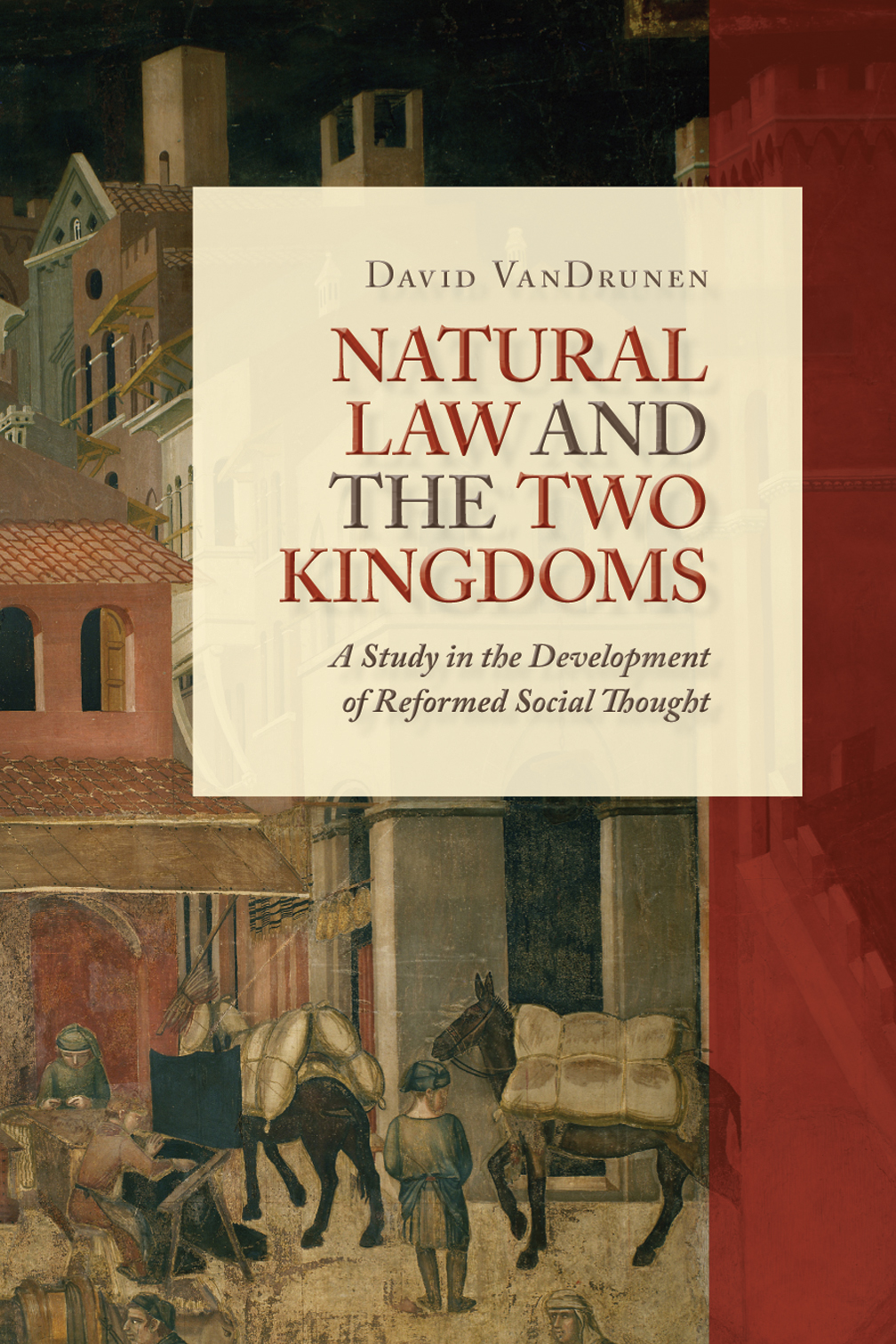
政治-神学问题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神学都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不仅和现实有关,也涉及到对于福音的理解。它对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提出了一个终极的挑战,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我们走向何方?我们期待什么,什么事物在迎接着我们?这篇文章将会大致梳理一下教会史中对此问题的一些解答,对此会专注于“两个国度”在教会历史中的演变。
在本文看来,神学在这个议题上始终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是暂时和永恒之间所造成的,一方面是此世和终末之事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基督徒,从来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在此世解决这个问题,但从下面的梳理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些过去的教训和经验指导我们如何活在当下。
奥古斯丁的“双城理论”
在教会历史上,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思想极大塑造了教会和外部世界的关系。<1> 在《上帝之城》中,他面对异教徒指控基督徒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落进行回应。他的神学是以“三一论”为基础,在实践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也就是信、望、爱。 <2> 在古代西方的背景下,人和城邦是不可分离的。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人的社会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后来逐渐发展到城,然后发展成为世界 <3> 。
在《上帝之城》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两座城”的概念,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城邦的性质取决于城邦中的人究竟所爱的是什么,人爱什么就组成什么样的社会,人所爱的事物越好,那么这个城邦的性质也就越好。因此只有爱正义,也就是爱来自于上帝的正义,敬拜上帝,才能够有真正的正义和正义的城邦。因此,对于奥古斯丁而言,没有真宗教的地方,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德行,德行是由所爱的事物决定的。对上帝的爱和对邻舍的爱构成了天上之城,而自我之爱则构成了尘世之城。特别是在第18卷的结尾,奥古斯丁写到,这两座城在人类的历史中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两座城在必朽坏的世间的历程,它们从起初到末了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其中,尘世之城,出于它自己意愿,而为自己造出各样的假神,或者是它选择其他之物中——甚至从人们中,造出假神,用来献祭;而另外那个天上之城,此世的天路客,不会去制造假神。相反,这种城自身就是被真正的上帝所造的,它自己就是献给上帝真正的祭物。在世间,两座城都同样使用美好的事物,都遭受邪恶的折磨;但是它们却有不同的信、望和爱,直到通过最终的审判而被分开,各自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地,在那里就永无止境了。<4>
上面的文字展现了奥古斯丁一直区分的两个概念,就是“使用”和“享有”(uti et frui),这点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原则,“使用”(uti)是指所用之物不是自身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手段来获得另外的目的。“享有”(frui)则是客体对象本身就是目的。这联系到了奥古斯丁的幸福论上,尘世之城并非是基督徒所享有的,但是却可以使用,直到对上帝之城的享有。
不同于早期奥古斯丁思想中将地上的国家等同于尘世之城,在《上帝之城》这里奥古斯丁思想已经有了变化,就是地上的国家是两座城重叠在一起,还没有区分开来。奥古斯丁研究学者马库斯(R.A. Markus)指出“这种新的强调部分是因为奥古斯丁更为成熟地思考了人类生活的世俗组成,和他所理解的世俗(saeculum)这个概念, ‘世俗’不是在两座城之间的无人之地,而是作为两座城交织在一起的现世生活,是复杂不清,只有世界终末才可分离的实在。” <5>
因此,“世俗”这个词在奥古斯丁的意义下,不是现代所讲的将宗教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而是指在世界终末之前人类所处在历史的尘世与时间中。在奥古斯丁的这个“世俗”概念中,包含了三方面的主题。首先,在最终的意义上它是历史的世俗化,就是在圣经救赎历史之外一切历史最终被视为同质化,也就是黑格尔后来所提出的普遍历史的问题。第二,在奥古斯丁所处的罗马帝国的背景下,将帝国的世俗化,也就是在普遍意义上,国家和社会制度不再具有最终的救赎目的(反对尤西比乌的神圣历史观)。第三,意味着教会的世俗化,也就是在教会的社会存在中(制度)并不完全如同多纳图派所想象的是“彼岸的”教会,现实中的教会依旧处在两座城的交织中(这也就是后来称之为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分)。<6>
奥古斯丁因此塑造了后来基督教对于现实政治的理解,在世俗中,现实政治是有限的,不完美的,基督徒并不是将尘世的制度与永恒之城彻底对立而否定前者,而是利用尘世暂时的和平,去规范社会的关系和可能的教会生活。奥古斯丁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在世俗中,人需要智慧的生活,区分而不是滥用人所面对的外在条件。<7>
中世纪的“双剑论”
中世纪基督教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地位已经不同于奥古斯丁的时代,在此期间,教会持有更多的是被称为“双剑论”的神学观点。这种神学可以追溯到教父时期。在公元494年,教宗吉拉修斯(Gelasius)一世致信给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休斯(Anastasius),“威严的帝王,这个世界有两个权柄所管理,祭司的神圣权柄和君王的权力。其中,祭司的责任更多地是君王在神圣审判的时候对君王的疑问提出回答。” <8> 吉拉修斯的观点已经明确地认为教会和国家是在基督中和谐共存的,而不再是奥古斯丁时期的那种对立状况。<9>
在公元751年,加洛林(Karolingi)家族开始统治法兰西,之后在公元800年由查理曼大帝在欧洲建立了除英格兰之外的基督教国,其同构的社会结构就是封建制度。在公元754年由教宗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授王权给丕平(Pepin)开始,中世纪基督教国王权和教权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像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那样。与封建制度相适应,教会制度也出现了同样的阶层分化,教会和帝国都作为基督在世界上的具体存在,分管着属灵和世俗的事务。教宗被视为是神圣属灵共和国的凯撒,主教大会也被视为是罗马议会的复兴。<10>
教宗利奥九世(Leo IX)开始了所谓的法律革命时,整个“双剑论”在欧洲从实践和思想上都被确立了起来。<11> 这一时期,该理论所基于的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路加福音》22章38节,门徒对耶稣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说:“够了”。这节经文的理解连同《马太福音》16章18-19节中对于教会权柄的解读,构成了后来天主教教会法和政治理论的基础。<12> 这种中世纪的四重释意解经原则和宗教改革以及现代对于经文解释的原则不同。中世纪对于一段经文的理解不仅仅是其字面的含义,还需要找出寓意和道德以及预言的含义。这种诠释方式决定了人们对这两节涉及到教会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解读。在教宗英诺森三世(任期:1198—1216)和其继任者教会法学家英诺森四世(任期:1243—1254)通过这两节经文的解读,最终将世俗权柄和属灵权柄都归给了基督在世上的代理者,也就是教宗。<13> 在现实政治中也就是不再进行暂时和永恒、属世和属灵之间的区分。
对于这种神学-政治理论的反对,在教会内外都没有停止过,但仍旧无法阻止教会-帝国秩序在中世纪的发展。在公元14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出现了罗拉德(Lollard)派运动,以及后来波希米亚地区的胡斯(Jan Hus)所领导的运动,与1378年教宗出现的大分裂(Great Schism)共同成为了中世纪秩序瓦解的前兆。<14>
宗教改革前,欧洲已经出现了挑战中世纪教宗绝对权力以及“双剑论”政治思想的理论家,如强调教会议会至上的代表,哥森(Jean Gerson),他曾出版《论圣职买卖》(Tract on Simony)和另一本专著讨论圣职问题和限制教宗权力。而库萨的尼古拉斯(Nicolaus of Cusa)在《论普遍和谐》(On Universal Harmony)中,专门批评了教会领袖将属灵和属世的事务进行混淆,谴责教宗的贪婪。<15>
但真正对于“双剑论”的理论基础构成挑战的,是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在1324年出版的《和平捍卫者》(Defender of Peace)一书。马西利乌斯在书中专门批判了教会使用世俗的强制权力。他认为,教会只应专注于属灵的权柄,教宗本身不应当凌驾于教会议会之上,相反基督教真正的信仰应当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刻意强调教宗的世俗权柄其实是损害了世界和教会内在的和平。而奥卡姆(Ockham)以及哥森等也都提出了类似观点,要求将教会的权柄限制在属灵而非属世的政治领域中。<16>
中世纪晚期,一方面是从教会内部开始不断有人提出质疑教会“双剑论”这种绝对权力的理论,另一方面,帝国各个地区君主日益对于罗马天主教和教宗权力产生出不满,随着各种民族意识的产生,开始酝酿着瓦解基督教-普世帝国秩序观念的种子。转变的时代和社会结构需要一种新的教会论和政治理论的出现,直到宗教改革最终展现了出来。沃格林(Eric Voegelin)对此给予了非常精辟的总结:
属世的领域和真正基督徒生活之间逐渐加大裂痕,其结果在宗教改革时才最终展现出来。世界的秩序被建立在了一个自主性的人类领域中,这个领域就严格意义而言脱离了基督教秩序,并且基督徒的生活更近一步地成为一种修道的、禁欲的生活行为。中世纪属世(temporal,更多强调时间暂时性的维度,本文作者注)-属灵双重秩序被打破成为两种秩序,也就是一种非基督教的政治-经济秩序,一种基督教的禁欲操练的秩序。结果,此世的秩序就按照它自身的原则而与基督教的生命秩序无关,要么就试图将生活的秩序限制保持在修道主义的立场上对此进行控制。<17>
路德的“两个国度”思想
1517年,以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论纲为开端的宗教改革,不只导致诸多民族-教会脱离罗马天主教的统御,而且还迫切需要有新的政治-神学理论来代替曾经在帝国领域框架下的理论。然而现实中的路德和路德宗并没有彻底脱离天主教教会法的传统。路德在两种政治张力之中,首先他要处理脱离罗马天主教-帝国秩序重新建立教会-民族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路德改教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变革,德意志地区开始出现大量的农民反抗并且在教义上持更为激进的观点,当时被统称污名化为“重洗派”。在1525年前,路德认为底层农民的诉求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他对他们的苦难保有同情,但是在1525年之后,路德厌恶农民反抗中出现的无序和杀戮,开始转而诉求君主贵族,要求镇压这群被他称之为如同“疯狗”一样的暴民。这标志着路德从“人民教会”或“团契教会”的观点转到了“君主教会”或“国度教会”上。 <18>
还有一点略有讽刺的是,尽管在1520年,路德带领德意志教会烧毁了大量关于教会法的书籍,试图禁止教会法在德国的施行。但是在十年后,面对德意志地区民族-国家秩序的需要,在1530年他开始在自己任教的维滕堡大学开始使用和赞赏传统的教会法典,并且思考教会和国家的现实问题。<19>
路德的“两个国度”理论和他整体神学观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使用的基督教传统术语表现了一种辩证性的二元对立,如属灵和肉体、灵魂和身体、信心和行为、天堂和地狱、罪人和义人、上帝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等等。他的两个国度理论至少涉及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按照维特(John Witte, Jr)的总结,首先,路德曾用两个国度的理论来区分堕落的领域和得到救赎的领域,这点类似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和人之城所进行的区分,但路德也用来区分魔鬼的统治与基督的统治。第二点是,路德两个国度的理论也涵盖了他对于罪人和圣徒、肉体和属灵、内在的人(良心)和外在的人(肉体)等之间的区别。第三点,有时路德用两个国度的理论借指可见教会和不可见教会之间的区分,也就是在世上被民法所治理的教会制度和被圣灵所管理的教会。第四点,他的理论也涉及到了理性和信心,自然知识和属灵知识之间的区分。最后,路德也用两个国度理论去论述两种义和律法的两种使用方式。<20>
在路德的观点中,按照圣经的启示存在两个国度,一个是上帝的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在最终审判之前,这两个国度一直针对人的灵魂进行着争战,路德将人比喻处在两个骑手之间的动物,当上帝是那位骑手时,人将按照上帝的意志去行动,而当撒旦是那位骑手时,人则跟从撒旦。 <21> 但是,在1523年时,路德的两个国度的理论就又有了一些变化,他说到:
这里我们必须将亚当的儿女和所有的人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属于上帝的国度,另一部分是属于世界的国度。属于上帝的国的人是所有一切在基督里,也在基督治理之下的真信徒,因为,在上帝的国度中,基督是君王和主……这些人不需世界的律法和刀剑。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由真基督徒,也就是真信徒所组成的话,那么就不再需要,也没有存在君主、国王,领主,刀剑或法律的益处……<22>
在路德看来,这就是圣灵在信徒心里运行,而其他的外在约束就失去了存在的目的。他接着说:
属于世界这个国度的是非基督徒,都在律法之下。他们中很少有真信徒,更缺乏过基督徒生活的人,他们很少人不屈从罪恶,也更少人不去作恶。因为这个缘故,上帝给他们提供了超出基督徒的范围和上帝的国之外的不同的政府。上帝让这些人臣服于这些刀剑之下,甚至于他们也喜欢如此,从而他们就不能够施行他们的恶,并且如果他们作恶,他们也无法不抱有惧怕……上帝已经设立了两种统治:属灵的,通过圣灵产生在基督之下的基督徒和义人;以及此世(temporal,时间性),限制非基督徒和恶人。<23>
然而,路德在其它的地方又指出,基督徒也是世上权柄掌管的一部分。在路德早期的神学中,存在着一种彻底的二元对立,特别是他将律法和福音完全对立。如维特总结到,“对于路德,他早期倾向于将地上国度的形象归并为魔鬼邪恶的领域,而这个地上的国就是官长统治的政治领域。这种双重的归并近乎导致路德极为危险地暗示,不仅仅是官长的法律,就是上帝的律法也成为了魔鬼国度的一部分。
此外,路德不断激烈地抨击摩西的律法,教会法和罗马法,不难看出,他的早期理论很容易导致认真的信仰追随者直接滑入反律法主义——也就是倾向于强调彻底基督教福音的自由而拒绝一切的律法。” <24> 这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何路德的同事也是“重洗派”的早期领袖卡斯塔特(Andreas Karlstadt)以及路德早期的追随者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后来都选择了更为激进的改教立场。<25>
受到德意志农民战争和“重洗派”的影响,路德逐渐调整了对于自然法和自然秩序的看法。1539年,和奥古斯丁一样,他指出家庭、国家和教会是上帝在人堕落之后设立的秩序,在尘世中三者从不同的方面代表了上帝在地上的权柄和律法,三者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在尘世中抵挡罪和撒旦的国,也预表在天国更完美的生活和律法。
他说到,“上帝想要尘世国度中的政府作为一种天上国度的象征……就如同上帝的装扮和面具一般”。<26> 显然,路德的立场已经不是曾经那种彻底二元对立的立场,尘世中的权柄成为了上帝国度权柄在此世的延伸和象征。他也重新调整了对于民事权柄和教会事务关系的看法。他开始主张世俗的权柄有责任去镇压异端、亵渎的行为,特别是镇压激进宗教改革派。1532年,路德甚至主张民事政府应该给予“重洗派”处以斩首的极刑。即便此时,路德也认为他的立场仍旧是对于两个国度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错误的教导和亵渎的行为会影响到外部的秩序,因此依旧属于民事长官的责任,属世的权柄也应当管理公共的敬拜和教导,这些领域都应当是在暂时属世政府的管理中。<27> 这点影响了路德对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理解,他认为这些都是上帝的意志所设立的,反抗统治者其实就是反抗上帝的意志。 <28>
在路德的晚年,在处理政府和教会权力的秩序上,他进而主张可见教会的教会秩序是作为尘世国度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属灵国度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他又觉得当时的民事政府对于教会进行了过度控制。路德始终没有提出一个规范性的神学来处理教会-国家的关系。
在此方面,路德的跟随者梅兰森(Philip Melanchthon)更多追随了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从而更清晰地区分了属灵治理和属世治理。<29> 梅兰森主张,对于属灵的治理是传讲上帝的道,以及与永恒公义和圣灵有关的事务,而暂时属世的政府则是外在的事务,但是世俗权柄有责任既在物质也在属灵上关注臣民的福利。<30> 在路德和梅兰森理论的影响下,后来路德宗的教会论,通常将教会纪律、教会的治理和敬拜都俯首在民事权柄的统治之下。
然而,围绕着路德两个国度的争论即便在近期的研究中也没有达成一致。一些学者如温格瑞(Gustaf Wingren)认为,路德的两个国度理论在早期和晚期,其核心是一致的,并不是一种时间顺序的演变。他特别提醒,在路德的概念中,也有一个类似于奥古斯丁“使用”和“享有”的概念,就是“使用”和“误用”,正确的对于事物的使用或者误用决定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在外在的实践中,影响了我们内在的生命。这个也就是路德所谓内在的人(良心)和外在的人(肉体)的关系。良心直接联系着上帝,而我们的身体则表达了我们和尘世中邻舍、呼召、和世界的关系。因此在路德这种辩证法中,一个人同时是罪人,被律法所管理,也同时是圣徒,活在福音之下 <31> 。一旦脱离了路德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对于他辩证法修辞的理解,很容易将路德划归为某一种立场。巴特(Karl Barth)则认为路德和此后的路德宗没有处理好国家-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律法-福音的关系,从而为纳粹的兴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2>
在我看来,理解路德不能够脱离他自己的现实,路德自身面对的时代,其主权观念和现实不同于20世纪的主权观念和现实,与奥古斯丁和我们的背景都不同,路德和加尔文仍旧生活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的背景之下,尽管此时民族国家已经开始出现,这是路德所面对的现实。然而,在路德观念中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上帝不仅仅是教会的主,也是世俗权柄的主,即使是民事权柄的持有者作为基督徒(或者名义上的基督徒)仍旧需要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如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指出的,在路德的写作中,无论教会制度还是国家,都是作为属世的制度所存在,在终末的基础中,我们不能够将这两者在此世彻底独立开来,路德所延续的仍旧是一个基督教传统的整体社会,尽管他站在现代社会和政治的门口,但是他的世界其实仍旧不等同于现代的世界。<33>
加尔文的“两个国度”思想
加尔文(John Calvin)对于后世影响力最大的著作《基督教要义》,其结构受到了《罗马书》和《使徒信经》的影响,以上帝作为创造主、救赎主和安慰主(保惠师)以及教会生活四部分构成。加尔文的“两个国度”理论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政治观点存在。一方面,他的“两个国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日内瓦这个市民和商业的城邦社会的现实思考,另一方面,加尔文是基于一种终末论基础的神学视角来作为“两个国度”理论的思想基础。此外,最近的一些学者如范德恩(David VanDrunen )和图宁格(Matthew Tuininga)也指出加尔文的两个国度的理论是以自然法为基础,联系着更为深远的基督教传统。<34> 与路德不同,加尔文的“两个国度”的理论既不是上帝的国和撒旦的国的对立,也不是上帝的国和人的国的对立,相反,在加尔文的论述中,两个国度都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但是上帝却是以不同的治理方式进行着管理。<35>
首先,加尔文思考的“两个国度”理论涉及到了律法和福音的关系。
加尔文和路德在理解律法的功用上,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关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否还需要律法。在加尔文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律法对于基督徒而言是作为生命成圣的指导。因为人堕落后被罪影响,即便是基督徒也有可能倾向于滥用自己的自由。在此世,基督徒得救后的自由中包含了良心的自由。这种良心的自由紧密联系着称义的教义,就是人唯独在基督里依靠上帝的恩典而称义,而不需要依靠律法、行为和他人强制就顺服于上帝的律法,从而基督徒就从律法的强制下获得了自由,并且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外在之事,基督徒也有可做可不做不被论断的良心自由。<36> 在这种自由之下,仍旧需要律法作为指导,而外在表现就是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两种统治(Duplex esse in homine regimen).这就是加尔文的“两个国度”的理论。在《要义》(3.19.15)中,加尔文给出了详细的表述:
一方面是属灵的,因此作为对于上帝虔诚和敬畏的指导;其次,是政治性的,给予人关于人类中必须要维护的人和公民责任的教化。这两者通常被称之为“属灵”和“现世”的法权(iurisdictio spiritualis et temporalis), 前者管理的范围是灵魂生活,而后者对于当下的生活则是必要的——当下的生活不仅仅需要衣食,而且也需要法律,使得人们与他人生活时能够虔诚、有尊严和节制地生活。属灵的治理是在内心之中,而现世的规则却是外在的行为。我们可以称前者为属灵的国度(regnum spirituale),另一个则称之为政治的国度(regnum politicum)。如我们所区分的,这两个国度需要分开来进行考察;然而当考虑一个国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将思考从另外一个转移过来。可以说,它们是在人之中的两个世界(mundi duo),由不同的君王和各异的律法具有权柄来对其治理。
对此,加尔文特别地提醒,人不能将这两个国度的权力进行混淆。他不认同激进宗教改革派彻底否定民事政府权柄,或认为因为有属灵自由而免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但是,加尔文的“两个国度”理论并不意味着民事政府就可以无关属灵实在,一方面,它的权柄对于人的良心、内在心灵是有限度的管理而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它的作用是维护人们信仰、心灵的外在条件,如外在行为、公共秩序。
加尔文的观点和路德有很大不同。他的“两个国度”在此世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相反和奥古斯丁一样,他以一种终末论的视角来理解这种状态。在圣经中,尽管基督在世的时候,曾宣告说他的国不在地上,但是在基督复活之后却宣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赋予了他,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在加尔文看来并非矛盾,而是要依靠终末论的视角对此进行了区分。基督的国度,一方面对于教会进行着属灵的治理;另一方面,对于世界进行着普遍的治理。在基督属灵的统治中,是和救赎的恩典有关,只在教会中通过圣灵和道运行在人的内心。而普遍的治理则彰显了基督对于世人的普遍的公义和关怀,上帝的护理运行在立王废王、人类社会制度和自然的各个层面。<37>
在世界终末之前,在现实中,两个国度是不能够完全进行对立和彻底区分的。加尔文延续了西方传统的宇宙论和基督教的人论来理解这两种国度的关系。在其《以弗所书》、《哥林多前后书》的注释中,加尔文都是用了灵魂和身体的关系来类比内在和外在的、属灵和世界的关系。<38> 对此,加尔文写到:“肉体和灵都是属于灵魂的部分,但是灵是被更新的部分,肉体仍旧保留着它自然的特征……内在的人不仅仅是灵魂,而是其属灵的部分已经被上帝重生。” 在此,基督徒的生活存在着内在和外在的区分,内在的生命是“老我”的死去和重生,而外在则是在苦难和试炼中,学会谦卑,忍耐和顺服。只有从终末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这种两个国度的关系。因为世界被罪所败坏而使得人绝望,基督徒要轻看这个世界而高举基督这位荣耀君王 ,而另一方面,基督徒仍旧在这个世界上,尽管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却仍旧需要爱他们的邻舍,如同在战役中的战士持守他们在世界上的岗位。加尔文的“两个国度”指出,在此世,基督的国度是尚未完全实现的,因此在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张力中,需要有智慧的区分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暂时的事物,什么是外在的事物,什么是内在的事物,因此加尔文说,“人所使用外在的事物……对于今世的生活是必要的,却也如影子一般很快就过去”。<39>
属世的政治秩序,依旧是被上帝所设立的,在加尔文看来,这个世界的终结也意味着尘世统治的终结,唯独上帝执行着他的权柄和统治。<40> 然而,这点并不意味着加尔文认同激进宗教改革者的观点,对此世的政治生活完全的否定和拒绝。相反,加尔文诉诸于良心的自由,即基督徒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是实践对于邻舍之爱的这条诫命。民事政府尽管不属于基督属灵的国度,但是却属于基督普遍的主权治理之下。在加尔文看来,“重洗派”主张的基督徒退出公共事务的领域,禁止公共宣誓,放弃私有财产等等在现实中颠覆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加尔文在1555年的《马太福音》注释中写道:
然而,基督让普通的人明白他所传讲的,一方面足以让人认识到上帝属灵的国度和政治秩序之间的差别,但是另一方面政治秩序又是今世生活的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差别,上帝希望是掌管灵魂的唯一立法者,敬拜上帝的规则只能来源于神自己的话语而不是其他,并且我们也应当享有着独一、纯粹的敬拜;而刀剑、法律和法庭的权力则不能够拦阻我们全然地敬拜上帝。然而,这项教义可以进一步延伸,每一个人,根据他的呼召,应该履行他对于他人的责任;孩子应当愿意顺服他们的父母,仆人应当顺服主人;根据仁爱的法则,人们应当殷勤好客,彼此乐于相助,这些都是以上帝始终拥有至高的主权为条件,从而,世上万物对人而言都应当从属于上帝的主权。因此,那些想要破坏政治秩序(politicum ordinem)之人,就是对上帝的反叛,因此,顺服君主和官长通常关联着对上帝的敬拜和敬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君王夺取任何属于上帝的权柄,那么我们就不应当顺服,并且这也不是违背上帝。<41>
尽管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是作为救赎主,而施行了属灵的权柄,但基督并没有废除世上统治的权柄,而是彰显了他的怜悯。民事权柄一方面可以被圣灵使用,作为维护此世正义和秩序的工具;另一方面,基督属灵国度和世上国度之间权柄的基础是有差别的。因为人被罪的败坏,民事的权柄是基于强制和权力来约束罪,而基督的国度其特征则是恩典、怜悯和自由。<42>
基于以上论述,加尔文区分了两种义。一种是基督的义,具有属灵的目的,唯独这种义能够使得人重生、成圣。而政治的领袖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义”,有时也被称之为“公义的君王”,是指他们能按照公平来进行治理,政治权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外在的正义,但是却不具有属灵的权柄,因此这两个国度具有两种义,加尔文在《腓立比书》注释中写到,“律法的两种义。一种是属灵的——是对上帝和邻舍完全的爱。它被包括在教义中,在任何(有罪的)人生命中都不会有这种义。另一种是字面意义上的,就是在人眼中表现出来的,然而在其内心中与此同时是被假冒为善所支配,这在上帝眼中依旧是邪恶的。” <43>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加尔文对于两个国度以及律法的理解,两个国度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代表了永恒和暂时,享有和使用之间的关系,律法在属灵的方面,是指导人们明白真正的义,并且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而在社会秩序和政治事务中,法律所起到的作用是对人外在行为约束,表明了上帝普遍的护理。正如,霍普夫(Harro Höpfl)指出的,加尔文早期和晚期的写作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并且也深受其法学训练和罗马自然法的影响。此外,加尔文的两个国度的理论并不完全等同于在日内瓦的真实的政治状况,但是显然,加尔文的政治理论更为适用于当时作为市民社会的日内瓦的基础而非法国和罗马。<44>
在17世纪初被称为改革宗正统的神学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加尔文“两个国度”理论的延续,如特伦廷(Francis Turretin)和卢瑟福(Samuel Rutherford)的神学著作,以及阿萨修斯(Johannes Althusius)的《政治》(Politica)的理论中。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特伦廷指出:“我们必须在所有事物上区分出两方面的国度,这些都属于基督:一个是自然的或实质的;另一种是中介性或救赎过程性的……自然或实质的国度是涵盖了一切受造物,而中保性或救赎过程性的国度是则专指教会”。在他看来,对前者的掌管是基督作为永恒的圣子,是因为上帝的普遍护理;而对于后者则是基于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在上帝拣选的旨意之下,基督行使他君王的权柄……因此,前者的治理是因为自然的本性,而后者的治理则是处于上帝的恩典。<45> 与此同时,基督作为君王的权柄所统治的属灵国度在此世只显现在教会中,它由四部分组成,也就是对于教会的呼召和聚集,对于教会的治理和保守,对于教会的维护,以及赋予教会的荣耀。因此基督作为中保,是教会唯一的君王,而教会则是唯一属天国度在地上的展现方式。
慈运理和其他改教者的观点
在苏黎世,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首先反对的就是罗马和欧洲诸国使用瑞士雇佣兵彼此战争。瑞士,特别是苏黎世更如同日内瓦而不同于德意志,更趋向于贸易城邦而不是封建领主制。和路德一样,慈运理反对罗马天主教对于世俗政权的染指,但是不同于路德的在于,慈运理认为瑞士的各个城邦和教会是联合一体的,作为基督教的共和国为敬虔的官长所领导,而不是早期路德和晚期路德所处的德意志封建君主和诸侯的环境。
在1523年的讲道中,慈运理区分了神的义和人的义,前者出于上帝的恩典,是完全的,而人的义则是仅仅满足属世的法律要求,对于上帝的义,人凭自己是无法实现的。慈运理通过这两种不同的义也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律法。一种是上帝的律法,是对于内在的人的要求,就是十诫中的爱上帝和爱人,除了人通过信心在基督里获得,没有人能够完成这种律法的要求。还有一种就是外在的律法,用强制力来约束外在的行为。对于慈运理而言,教牧人员的职责是传讲上帝的道,让人明白救恩之道,而民事权柄则是给予教牧人员自由传讲福音,而禁止迷信。慈运理主张,民事长官对于教会的秩序是必要的,也是教会体系的一部分。在教会关于教义事务和公共敬拜,以及教会纪律中,民事政府有权柄去监督教会的决策。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教会是隶属于民事政府之下,而是两者同处于基督的共同体之中,承担着不同的属世的职能。因此在慈运理的两个国度理论中,他不认同路德早期的观点,即认为基督属灵的国度完全不与此世相关,相反,慈运理认为在此世,民事长官和教会牧职的关系如同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不可分割,如同旧约时代的君王和先知,民事长官和教牧人员共同分享了基督在此世的权柄,不同的只有教会事务和城邦事务之间的施行职分上。因此,在慈运理看来,正是早期路德过度强调了基督的国不与这个世界相关,才引起了当时“重洗派”的骚乱和政治的无序。从慈运理到布灵格(Heinrich Bullinger),从而发展出一种非常不同于德意志的两个国度理论,在现实的瑞士宗教改革中,民事政府则直接干预和管理着教会事务。<46>
在斯特拉斯堡,布歇(Martin Bucer)的观点和慈运理在教会和民事权柄的关系上非常接近,他们同样都是受到“重洗派”的冲击,而更强调民事政府和民事法律的重要性,坚持认为民事政府是基督徒社群的一部分而不是对立的存在。布歇影响了后来加尔文两个国度理论的形成。<47>
不过,布歇和慈运理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分歧,就是对民事政府是否执行教会的纪律和惩戒,以及它的基础在哪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改教的背景,就是当时的教会秩序法令和信仰告白的颁布不是由教会,而是通过城市的议会。1533年,斯特拉斯堡的牧师恩格布勒特(Antonius Engelbrecht)诉求于早期路德的理论,认为在新约时代,基督唯独靠话语治理他的百姓,因此他主张民事政府和教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度,要彻底的分开,因此,民事政府既不能够去捍卫福音,也不能够执行教会的纪律。而布歇则诉求于路德后期的思想,并且解释《罗马书》13章4节和《提摩太前书》2章2节,认为民事权柄是上帝所设立用于保障和平及人敬虔生活的公共秩序。他和慈运理观点不同,在于他认为,基督教具有两种特性,就是内在的信仰和外在的公共敬拜,民事政府并不是作为教会职分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上帝所设立的监督,有责任按照十诫来作为外在行为的准则来监督公共敬拜。并且,布歇进一步细化了教会内在的职分,他开始区分使徒、教师,帮助者和管理者不同的职分,并且也指出教会对于穷人的看顾(这点在许多改教者看来是属于民事政府的责任)。最为重要的,就是布歇指出,教会纪律的惩戒唯独属于教会之内,而不是属于民事政府,因为教会的纪律是天国的钥匙,所以应当由教会的长老和执事来行使而不是通过民事政府。这点对于后来加尔文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48>
激进宗教改革的“两个国度”理论
在宗教改革时期,尽管激进宗教改革运动没有一个中心性的起源,而是分散在各个地方,并且他们所持有的教义各不相同,但是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和改革宗都直接将其称之为“重洗派(再洗礼派)”。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却指出,在这些激进改革运动中,即便是“重洗派”都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除了“重洗派”还有“灵性派”和“理性主义者”,而这些很多时候都被不加区分冠之为“重洗派”。<49> 在早期传播的书籍中,可以看到伊拉斯谟、路德对他们的影响,还有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和平捍卫者》,以及约阿西姆主义(Joachimism)也在他们中广为流传。<50> 其社会构成,更多的是农民和新兴的城市手工业者,带有中世纪晚期弟兄会的组织印记。<51>
在宗教改革早期,路德在维滕堡大学的同事,卡斯塔特就提出了不同于路德的改教观点。在路德被流放到沃特堡期间,卡斯塔特一开始呼吁地方政府应当改革教会,祛除异端,他认为按照路德的福音观,显然要反对中世纪的教会-社会传统,就应当彻底地进行社会改革。在1522年,卡斯塔特迫使维滕堡当局接受了他的宗教改革计划。在这个改革计划中,不仅包括简化圣礼,还涉及到社会救济等多方面。此外,卡斯塔特还发起了圣像破坏运动,并鼓励教牧阶层衣着简朴,和劳动阶层一样。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激发了人们的狂热。对此,卡斯塔特主张,一切真正的基督徒都直接受到圣灵的教导,而不再需要民事政府管理,直到路德返回维滕堡才平息了动荡。<52> 在卡斯塔特影响维滕堡的这一期间,闵采尔受到路德精神的影响,宣称茨维考(Zwickau)的三个先知直接领受了上帝的启示和异象传讲预言,他们强调属灵的浇灌,废除婴儿洗,认为当时入侵欧洲的土耳其人就是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而新的千禧年马上就要来临。1522年,闵采尔来到维滕堡会见了卡斯塔特,此后他们两人的思想开始广泛地在德意志地区传播,成为德国农民起义的一个思想根源。<53>
在苏黎世,有戈瑞博(Konrad Grebel)等领导的运动不同于慈运理这些改教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约对于门徒的要求是不依靠国家和城邦的强制,而是唯独圣经和圣灵来指导基督徒的生活。教会不应当和国家产生任何联系,要彻底分离,教会的成员应当本人亲自认信告白加入教会,从而拒绝婴儿洗礼。教会不应该依靠政府税收资助,牧职人员应当不接受城邦的俸禄。<54>
从闵采尔到门诺·西门(Menno Simons)这些被称为“重洗派”的激进改革派,并不一定是革命反抗运动的领导者,他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从主张革命反抗到彻底的和平主义者都有。如门诺·西门就主张,基督徒唯一的武器就是属灵的武器,即上帝的话语,而不是世俗的武器。<55> 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主张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以此来否定过去的教会传统,主张属灵和属世的彻底分离。真正的基督教会不是外在的制度,而是认信的真信徒在基督里的团契。因此,为了受洗的真信徒不被外在教会这个巴比伦所俘获,信徒的团契和世俗的组织要进行彻底分离。在此基础上,他们普遍拒绝在城邦中进行宣誓和婴儿洗礼。有些也主张,在洗礼前的婚姻是无效的,信徒夫妇应当在洗礼后重新缔结神圣婚姻,这些都无疑否定了当时民事政府的权力和其他婚姻的神圣有效性,对民事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都起到了颠覆作用,甚至瓦解了维系社会的结构。
在瑞士各城市,这些所涉及的不仅是神学问题,更是城邦公民权以及税收、服兵役等一系列民事权利。因此,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宗教改革的路德宗和改革宗地区,“重洗派”都被视为颠覆者和反叛者,尽管并非所有的“重洗派”都反对三位一体、自由意志等教义,如门诺·西门认同三位一体的教义,专门为此写了《关于三一上帝的告白》(Confession of the Triune God)来进行澄清。他对于道成肉身这个观点也在辩论中不断修正。但是,这更多是因为直接的政治原因而非神学观点。在宗教改革时期,“重洗派”遭遇到了最为严重的宗教迫害。
在激进改革派中,由德国修士萨特勒(Michael Sattler)起草的《施莱塞姆告白》(The Schleitheim Confession),代表了普遍的激进宗教改革派所持有的两个国度的看法:
应当从魔鬼所撒播在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和恶人中彻底地分离出来,以免我们和他们一同沉沦到令人厌恶的地步……就这些事情而言,我们应当知道一切不与我们的上帝和基督联合的都是我们应当逃避的令人厌恶的事物。在这个世界和受造之物中只有善恶之分,信徒和非信徒,黑暗和光明,属世界的和不属世界的,上帝的殿和偶像,基督和彼列,彼此无法相交……<56>
在关于论述刀剑和宣誓的条款中,《施莱塞姆告白》宣称,上帝所设立世上的权柄是针对非信徒和恶人的而不是基督徒,在基督里是要废止,因此它明确拒绝了使用强制暴力和宣誓这两项16世纪欧洲城邦的秩序基础,并且认为基督的国度是和这些彻底对立和分离的,基督的国与黑暗的国是对立的。
未尽的微声?
显然,即便是这样一片冗长的文章也无法详细概括“两个国度”在宗教改革之前和其中的复杂演变。限于篇幅,不得不舍弃讨论很多重要的人和议题,比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不同的立场和政治神学的观点,诸如胡克(Richard Hooker)和不从国教者之间理论的张力,而荷兰地区也存在着多种复杂的观念。
但是,至少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妥善地得到以下的结论。首先,教会历史上,政治-教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到各部分神学教义的影响,也被当时的社会结构所塑造。属世-属灵权柄之间在现实中始终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即便是在同一时期,教会中仍旧存在着对此不同的看法。就连同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如路德,其思想也是处在一种和现实互动的动态过程,而非在这方面获得了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理。很大程度上,属灵-属世权柄确立的政治神学问题是和人们对于终末的理解和教会所处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此世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如同说明书般的答案机械地指导基督徒按部就班的处理一切问题。正如路德在自己的处境下不能完全仿照奥古斯丁来处理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加尔文不同于路德,激进改革派不同于使徒那样,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需要面对的政治-神学问题。
在现代中,有一种需要惧怕和警惕的情形,那就是将“两个国度”的理论彻底意识形态化为自己所用,却主张认为这最基于启示的原则。相反,奥古斯丁对于“享有”和“使用”的视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式,让我们有智慧地区分什么是暂时,什么是永恒。
其次,暂时权柄的问题涉及到了社会结构和时代的变化。除了上帝至高的主权,在各个时代,权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在城邦中、在民主制、在封建制、在帝国中,它的内核根本就包括着不同的含义,正如奥古斯丁使用“世俗”和我们今日的概念已经不同。今日人人诉求传统来确立权威,此世的传统却在时间中消逝,众声喧嚣中唯独上帝的道指向必然的未来,也许此文算是尚未完成的微声?
<1> Joanna Scott, “Political Thought, Contemporary Influence of Augustine’s” in Allan Fitzgerald, ed., Augustine through the Ages: An Encyclopedia, (Grand Rapids and Cambridg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 第658-60页。Jean Bethke Elshtain, Augustine and the Limits of Politics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对此进行详细总结的文献,见:Eric Gregory, Politics & the Order of Love: An Augustinian Ethic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第1-29页。以及:Eugene TeSelle, Living in Two Cities: Augustinian Trajectories in Political Thought (Scranton: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1998). 以及:Oliver O’Donovan, The Desire of the Nations: Rediscovering the Roots of Political Th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201-03页。
<2> Augustine, Teaching Christianity. Translated by Edmund Hill (New York: New City Press, 1996).
<3>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edited by R.W. Dy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924页。
<4> 同上,第907-08页。
<5> R.A. Markus, Saeculum: 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Theology of St. August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71页。
<6> 同上,133页。
<7> Jean Bethke Elshtain, Augustine and the Limits of Politics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第91页。
<8> 转引自:Matthew J. Tuininga, Calvin’s Political Theology and the Public Engagement of the Church: Christ’s Two Kingdo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第24页。
<9> David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ed Social Though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10 ), 第32-36页。
<10> J. H. Bur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350-c.14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第210-33页。
<11> Harold 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 I: The Found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 对中世纪属灵和属世权力比较详细的讨论,可参见:J. H. Burn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367-421页,特别是对于“Unam sanctum”发表后对教会权力的影响。
<13> Harold 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 I. 49-84. 也见:John B. Morrall, Political Thought in Medieval Tim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第28-58页。
<14>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II: The Age of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34-37页。
<15> 同上,第37-39页。
<16> 同上,第37-50页。
<17> Eric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 III: The Later Middle Ages (Columbia :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8), 第119页。
<18> 毕尔麦尔等编著,《近代教会史》, 雷立柏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第21-23页。
<19> John Witte, Jr., Law and Protestantism: The Legal Teaching of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87-88页。
<20> 同上, 第89页。
<21> 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Devil, trans. Eileen Walliser-Schwarzb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对此的详细分析见:Witte, 第90页。
<22> 同上,第90页。
<23> 见《路德文集》11:249-52。转引自:Witte,第90-91页。
<24> Witte,第92页。
<25> 具体讨论路德早期思想和激进宗教改革派之间的渊源,见:George Huntston Williams,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1962), 特别是第三章。
<26> 转引自:Witte,93页。
<27> Tuininga, 第36-40页。
<28> Skinner, 第18-19页。
<29>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James M. Estes, Peace, Order and the Glory of God: Secular Authority and the Church in the Thought of Luther and Melanchthon 1518-1559 (Leiden: Brill, 2005).
<30> Tuininga, 第38-40页。
<31> Gustaf Wingren, Luther on Vocation, trans. Carl C. Rasmussen (Eugene, Or: Wipf & Stock Publishers, 2004),第90-94页。
<32> Karl Barth, Community, State, and Church: Three Essay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 Herberg,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68).
<33> Wolfhart Pannenberg, Ethics, trans. Keith Cri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1), 第130-31页。
<34> VanDrunen, 第63-86页。Tuininga,第37-41页。
<35> VanDrunen,第70-71页。
<36> Institute, 3.19.1-9。鉴于《要义》版本多样,本文参考了多个版本,指注明其段落出处,方便参考。
<37> Tuininga, 第149-150页。
<38> 同上, 第151-53页。
<39> 同上,第151-53页。
<40> 同上,第157页。
<41> Commentary on Matthew 21:21. 也见:Tuininga,第170页。
<42> Tuininga, 第172页。
<43> 也参见:Tuininga, 第172-73页。
<44> Harro Höpfl, The Christian Polity of John Calv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207-17页。
<45> Francis Turretin, Institutes of Elenctic Theology, Vol.2, trans. George Musgrave Giger (Phillipsburg: P&R Press, 1994), 第485-87页。
<46> 具体的讨论,见:Tuininga,44-46页。Bruce Gordon, The Swiss Reformation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47> David F. Wright ed., Martin Bucer: Reforming Church and Communit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uininga, 第56-57页。
<48> Tuininga, 第57-60页。
<49> Williams,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第xxiv页。
<50> 同上,第xxxi页,以及第19-20页。
<51> 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第431-434页。
<52> 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第313-17页。
<53> George Huntston Williams, The Radical Reformation,第45-48页。
<54>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I,第446-48页。
<55> Williams, The Radical Reformation,第764-77页。
<56> Karl Koop ed., Confessions of Faith in the Anabaptist Tradition 1527-1660 (Kitchener: Pandora Press), 第28页。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4期(2018年春季号)。题图为此文其中一本参考文献封面,来自:https://www.eerdmans.com/Products/6443/natural-law-and-the-two-kingdoms.aspx。
《世代》第4期主题是“帝国”,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欢迎访问《世代》网站(www.kosmoschina.org)。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