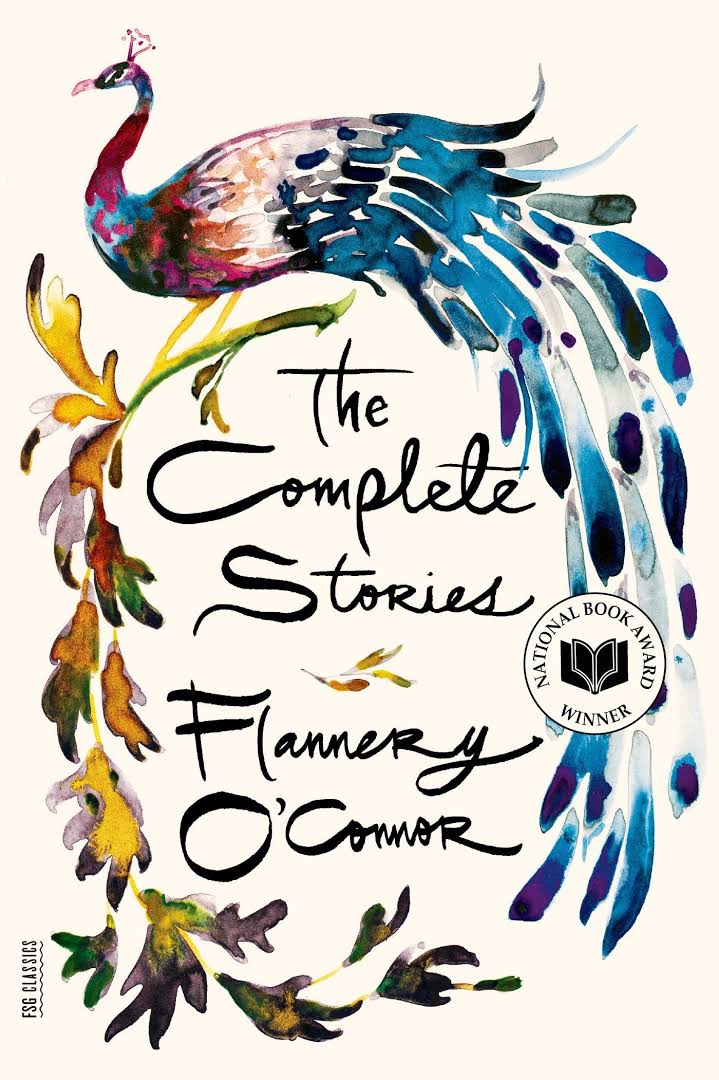
整个周末,两个女孩都在互称圣殿甲和圣殿乙,笑得浑身乱颤,面色红热,弄得她们越发难看,尤其是那个满脸雀斑的乔安妮。她们来时穿着棕色修道服,那是在圣斯考拉思蒂卡山必须穿的制服,一打开手提箱,她们马上扔掉修道服,换上红色短裙和花里胡哨的衬衫。她们涂口红,穿上一般在周日才穿的高跟鞋,在屋子各处走来走去,时不时地从大厅的那条长镜子边慢慢行过,就为了看一眼自己的腿。她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个孩子看在眼里。如果她们当中只来了一个人,就会和她一起玩儿;这次既然来了两个人,她就躲在一边,满腹怀疑,远远地看她们。
她们两个14岁了——比她大两岁,不过,她们都不够聪明,所以才会被送到修道院去。如果去普通学校,她们除了一心想着男孩子,什么也做不了;她母亲说,在修道院,修女会看着她们。孩子观察了她们几个小时后,认定她们确实是百分百傻瓜,想到她们只是她的远房表亲,她不会遗传她们的愚蠢基因,她甚为高兴。苏珊叫自己“苏赞”,她细瘦无比,有一张漂亮的尖脸和红头发。乔安妮的头发是黄色的,天然鬈曲,她用鼻子发音,大笑时,脸上会出现一片片紫斑。她俩一句聪明话也说不出来,每句话都这么开头:“你知道跟我很熟的那个男孩,有一次,他……”
她们整个周末都要待在这儿,她母亲说,不知道应该怎么招待她们,因为与她们同龄的男孩子,她一个也不认识。听母亲这么说,孩子突然来了灵感,喊道:“有骗子呢!<1> 带骗子来!让柯比小姐把骗子带来,领她们逛!” 她差点儿被嘴里的食物噎着,笑得直不起腰,用拳头敲打桌面,看着对面两个一脸糊涂的女孩,她笑出泪来,眼泪从胖乎乎的脸蛋边滑落,嘴里的牙套像白锡一样闪闪发光。她以前从没想到这么好笑的事。
她的母亲笑得相当谨慎,柯比小姐羞红了脸,把叉子上的一粒豌豆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她长脸、金发,是一位教师,借住在她们家。奇特姆先生倾慕于她,这位有钱的老农每个周六下午都开着一辆15年车龄的浅蓝色庞蒂亚克,车外蒙了一层红土,车内坐满了黑人,他收每人10美分,周六下午送他们去镇上。把他们卸下来之后,他就来拜访柯比小姐,总会带个小礼物——一袋煮花生,或者一只西瓜,或者一截甘蔗,有一次带的是一盒批发的“Baby Ruth”(宝贝路得)牌巧克力棒棒糖。除了一小撮铁锈色头发,他几近全秃。他的脸和没铺过的路面颜色差不多,也像路面一样被冲刷出道道沟壑。他穿一件浅绿色带黑细条纹的衬衫,蓝色吊带裤,向前挺起的大肚子越过长裤,他时不时地用胖乎乎的大拇指轻柔地敲按两下肚皮。他一口牙颗颗镶金,他盯着柯比小姐,顽皮地转转眼珠,嘴里发出“呵呵”声,坐到她们家门廊的秋千上,两腿叉开,高帮靴子的脚尖在地板上指着不同的方向。
“我想骗子先生这个周末未必会进城。” 柯比小姐说,丝毫没意识到这只是一个玩笑,孩子又笑得浑身直颤,重重地靠到椅背上,又从椅子里滑下来,滚到地板上,躺在那儿直喘气。母亲警告她别再胡闹,不然就得离开餐桌。
昨天,母亲安排阿伦佐·迈尔斯开车73公里去梅维尔的女修道院,把两个女孩接过来度周末,星期天下午雇他再把她们送回去。他18岁,体重110多公斤,在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工作,他能载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他吸烟,更准确地说,他嚼一种短短的黑雪茄。透过他身上那件黄色尼龙衬衫,可以看到他的胸部圆滚滚、汗涔涔的。他开车的时候,所有的车窗都得打开。
“还有阿伦佐!” 孩子躺在地板上大喊,“让阿伦佐带她们逛!让阿伦佐去!”
两个女孩见过阿伦佐,她们立时尖叫着表示不愿意。
母亲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笑,但她马上说:“行了,闭嘴吧!”然后转移话题。她问两个女孩为什么彼此称呼对方是“圣殿甲”和“圣殿乙”,一句话引得她们咯咯地笑个不停。最后,她们尝试着解释。梅维尔慈善修女团年龄最大的波佩图阿修女,曾教导她们说,要是一个年轻男子想要——刚说到这儿,她们就忍不住大笑,不得不重新开头——要是一个年轻男子想要——她们把脑袋埋到大腿上——要是他想要——她们终于把那句话嚷了出来——要是他“和你们一起坐在汽车后座上,他的举止不够绅士的话”,波佩图阿修女告诉她们要这样回应:“住手,先生!我是圣灵的殿!”然后就会没事了。孩子从地板上坐起来,一脸茫然。她没看出来这有什么好笑的,真正好笑的是奇特姆先生和阿伦佐·迈尔斯拉着她们四处逛,这个想法让她快笑死了。
听她们说完,母亲也没笑,她说:“我觉得你们这些女孩真够傻的,你们的的确确是——圣灵的殿。”
两个女孩抬头看着她,很礼貌地压抑住咯咯的笑声。不过,她们脸上的惊讶表明,她们似乎刚刚意识到她和那位波佩图阿修女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柯比小姐仍然板着脸,而孩子想,她满脑子都在想,我是圣灵的殿,她对自己说。她特别喜欢这句话。这让她感觉好像是有人送给她的一份礼物。
晚饭后,母亲颓然倒在床上,说:“要是不能给两个女孩找点儿乐子,我会被她们逼疯的。她们真让人受不了。”
“我敢打赌,我知道你可以找谁。” 孩子冷不丁冒出一句。
“听着,不准再提奇特姆先生,”母亲说,“你让柯比小姐难为情了。他是她唯一的朋友。哦,主啊,”她坐起来,向窗外望去,眼神悲伤,“那个可怜人太孤单了,她甚至会去坐那辆闻起来像地狱最底层的汽车。”
她也是圣灵的殿,孩子反应过来了。她说:“我想的不是他,我刚才想到的是维尔金家的那两个——温德尔和科里,他们来布彻尔老太太农场做客呢。他们是她孙子,帮她干活。”
“这倒是个主意。” 母亲喃喃自语地说道,并满怀欣赏地看了她一眼,但马上,她又倒在了床上,“他们只是农场里的小男孩,这俩女孩可能看不上他们。”
“嘿,” 孩子说,“他们穿长裤了,他们已经16岁,还有一辆车。别人说他俩都会去教堂做传道人,因为做这个不需要懂任何事。”
“她们和那俩男孩在一起肯定会很安全。” 母亲说,过了一会儿,她坐起来,给他们的祖母打电话,跟老太太聊了半个小时,准备请温德尔和科里来吃晚饭,之后让他们带两个女孩去游乐集市玩。
苏珊和乔安妮特别高兴,她们洗了头,用铝制通孔发夹把头发卷起来。孩子盘腿坐在床上,看她们拆发夹,她心里想,哈,等着吧,温德尔和科里会让你们大开眼界!“你们会喜欢那两个男孩的,”她说,“温德尔高达1米8,红头发;科里高达2米1,黑头发,穿一件运动衫,他们有辆车,车前挂着一条松鼠尾巴。”
“像你这样的小孩子对那些男人怎么会了解这么多呢?” 苏珊问,而后把脸凑近镜子,仔细观察眼睛里放大的瞳孔。
孩子躺倒在床上,开始数天花板上的窄扣板,一直数到弄不清位置为止。我当然了解他们,她对某种存在物说。我们一起参加过世界大战。他们听我指挥,我从日本人的自杀式潜水中救过他们5次,温德尔说,我以后要娶那个孩子,另一个则说,哦不,你不能娶,我要娶,而我要说,你们一边去,因为在你们没来得及眨眼之前,我要让你们全都俯首听令。孩子说:“我不过是看见他们总在周围转悠。”
他们来了,两个女孩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又开始咯咯地笑,还说起修道院。她们并肩坐在秋千上,温德尔和科里则一起坐在楼梯栏杆上,坐的姿势像猴子那样,膝盖与肩膀平齐,手臂垂在膝盖中间。他们两个又矮又瘦,脸膛红红的,颧骨很高,眼睛像浅色的种子。他们带了一支口琴和一把吉他。一个男孩把口琴放在嘴边轻轻吹响,一边吹一边抬眼看两个女孩;另一个男孩抚弄了两下吉他,开始唱歌,他没看她们,而是朝某个角度昂着头,似乎他只对听自己唱歌感兴趣。他唱的是一首乡村民歌,听起来既像情歌又像赞美诗。
孩子把一只木桶推到房子侧边的灌木丛里,站到桶上面,她的脸和门廊的地板在同一水平线上。太阳正西沉,天空慢慢现出瘀青的紫色,似乎和甜蜜又忧伤的乐音连在了一起。温德尔一边唱一边微笑着看两个女孩。他用小狗一样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苏珊,唱道:
耶稣是我良友,
他是我的所有,
他是谷中百合,
他使我得自由!
而后,他用同样的眼神看着乔安妮,唱道:
虽有火墙围我,
我今不再恐慌,
他是谷中百合,
他永在我身旁!
两个女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抿住嘴唇,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但苏珊还是没忍住,她急忙用手捂住嘴。歌手皱皱眉,接下来拨弄了几秒钟吉他,随后唱起《古旧十架》,她们礼貌地听着,等他一唱完,她们马上说:“我们来唱一首!”还没等他开始,她们就用受过修道院培训的嗓音唱起来:
皇皇圣体尊高无比,
我们俯首至钦祟。
古教旧礼已成陈迹,
新约礼仪继圣功。
孩子看见两个男孩本来一脸的严肃正经,此刻却皱紧眉,满脸疑惑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不确定自己是否被耍了。
五官之力有所不及,
应由信德来补充。
赞美圣父赞美圣子,
欢欣踊跃来主前……
在灰紫色的光线下,男孩子们的脸现出深红色。他们看起来既暴躁又震惊。
歌颂主德浩无边。
圣神发自圣父圣子,
同尊同荣同威严。
阿们——
女孩子们把那声“阿们”拖得长长的,而后一片寂静。
“一定是犹太人的歌。” 温德尔说着,给吉他调了下音。
女孩子们咯咯地傻笑着,孩子却在木桶上跺脚,喊道:“你这头大笨牛!你这头要进教堂的大笨牛!” 他们从楼梯栏杆上跳下来,想看看是谁在嚷嚷,她大叫着,从木桶上掉了下来,爬起身,迅速绕过了屋角。
母亲安排他们在后庭院吃晚餐,她在几只日式灯笼下面摆好餐桌,从前只在举办花园舞会时她才会拉起那些灯笼。“我不跟他们一起吃饭。” 孩子说着,从桌上抓起自己的盘子,端到厨房,坐在一个身材瘦削的黑人厨子旁边,吃自己的晚餐。
厨子问她:“你干嘛总和别人过不去啊?”
孩子说:“他们都是大傻瓜。”
灯笼把与其平齐的树叶润染成桔色,灯笼上面的叶子呈墨绿色,下面的叶子则现出各种暗淡柔和的颜色,这让坐在餐桌边的女孩子们看起来比平时更漂亮。孩子时不时地扭头,冲着厨房窗户下面的景象狠狠地瞪上一眼。
厨子说:“上帝会把你变成又聋又瞎,那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聪明了。”
“那我也比某些人聪明。”孩子回应道。
晚饭后,他们要去游乐集市了。孩子也想去,但不想和他们一起去,所以,虽然她们来问过她,她也不愿去。她上了楼,两手绞背在身后,在长长的卧室里踱来踱去,她的头向前伸着,脸上露出又暴躁又恍惚的神情。她没开灯,任凭黑暗慢慢聚合,让房间越发显得狭小和隐密。每隔一段时间,光线会穿过开着的窗户,将影子投映在墙上。孩子停下来,站在窗边,目光越过黑黝黝的山坡,越过闪动银色微光的池塘,越过一排树林,望向光怪陆离的天空,那里有一道长长的光,像手指似的正在不停地四处移动,探向空中,似乎在搜寻那颗已然下落的太阳。那是游乐集市的灯塔发出来的光。
她能听到远处风琴的声音,仿佛看见金色锯末一般的灯光下,所有的帐篷都支起来,闪着钻戒光泽的摩天轮在空中一圈一圈地上去又下来,发出吱吱尖声的旋转木马在地上一圈一圈地旋转。游乐集市持续了五六天,有一个专为学龄儿童办的下午专场和一个专为黑人办的夜场。去年,孩子去了那个为学龄儿童举办的下午专场,看见一群猴子和一个胖子,还坐了摩天轮。有些帐篷不开放,因为里面的东西只能让成年人知道,但她还是满有兴趣地浏览了那些帐篷上的广告。帆布上穿紧身衣的人像已经褪色,人像绷着脸,面容沉静,仿佛是等着被罗马士兵割舌头的殉道士。她想象着,帐篷里面的东西与药物有关,决心长大后要做一个医生。
她后来改了主意,决定当工程师。但是,当她望向窗外,目光随着一边旋转一边变宽变短沿弧形绕圈的探照灯时,她觉得仅仅当医生或者工程师还不够,她应该做个圣徒,因为这个职业囊括了你所能知道的一切;但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成为圣徒。虽然她不偷窃不杀人,但她天生爱说谎,又懒惰,还顶撞母亲,而且故意地跟所有人过不去。她还深陷骄傲的罪中,这是最糟糕的罪。她取笑那位在学校毕业典礼上祷告的浸信会传道人,她撇着嘴,手托前额,仿佛很沉痛的样子,呻吟着:“父啊,吾们感谢汝!” 那姿态跟他一模一样,别人告诉她多次,不准再这么模仿。她永远也成不了圣徒,但她认为,如果他们杀了她,她还有机会做个殉道士。
她能忍受被枪杀,但被烧死在油中就不行了。她不知道能否受得了被狮子撕成碎片。她开始为自己的殉难做准备,想象自己身穿紧身衣裤,站在巨大的角斗场上,那些最早的基督徒被吊在火笼子里点燃,一道翻滚着尘灰的金色光柱映在她和狮子身上。领头的狮子扑了过来,然后匍匐在她的脚前,归顺了她。一只又一只狮子,都是同样的结果。狮子们喜欢她,她甚至可以睡在它们中间。最后,罗马人不得不把她烧死,但他们大为震惊,她居然烧不死;他们发现很难把她弄死,最终,他们用一把剑,飞快地砍下她的头,她立时就上了天堂。她把这一幕排演了好几次,每一次都在天堂门口返回了狮子群。
最后,她从窗边离开,没做祷告,就准备上床睡觉。房间里有两张沉重的双人床,俩女孩睡其中的一张。她谋划着,哪有那种冷冰冰、粘乎乎的东西可以藏进她们的被子里,但基本是白费脑子。能想到的东西,比如一只褪完毛的死鸡或者一块牛肝,她都没有。从窗口飘进来的风琴声让她睡不着,她想起还没祈祷,就爬起来,跪下祷告。她开头就很流利,一口气背完《使徒信经》的两面文字,然后下巴搁在床沿上,大脑一片空白。她记得自己的祷告,通常都是漫不经心地念一遍,偶尔,当她做了错事,或者听了音乐,或者丢了东西,再或者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她会激动得狂热不已,会想到走在通往各各他漫长苦路上的基督,在粗砺的十字架上被压三次。她的大脑会在此暂停片刻,而后变得空白,一旦有什么事触动她,她就会发现自己在想某件完全不相干的事,小狗,或者女孩,或者将来某天要做的什么事。这个晚上,她想起温德尔和科里,竟然满怀感恩,几乎要喜极而泣,她说:“主啊,主啊,感谢您没让我进教堂做事,谢谢您,主,感谢您!” 她回到床上,一遍遍地重复着,直到睡着。
两个女孩进门的时候已经11点45分了,咯咯的笑声吵醒了她。她们打开戴着蓝色灯罩的小灯,开始脱衣服,她们瘦骨嶙峋的影子爬到了墙上,折断,又继续在天花板上无声地移动。孩子坐起来,听她们谈论在游乐集市上的所见所闻。苏珊买了一把塑料手枪,里面装满了廉价糖果;乔安妮买了一只纸板猫,上面布满红色圆点。孩子问:“你们看到猴子跳舞了吗?看到胖子和那些侏儒了吗?”
“看见了各种各样的畸形人。” 乔安妮说。然后,她对苏珊说:“我玩得挺开心,除了——那个东西。” 她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表情,好像她咬了一口什么,却不确定自己是否爱吃。
另一个女孩静静地站着,摇了下头,朝孩子那边微微示意,压低声音说:“人小耳朵长。” 孩子还是听到了,她的心急速地跳起来。
她从床上下来,爬到她们的床尾板。她们关上灯,钻进被子,她却一动没动。她坐在那儿,死死地盯着她们,直到她们的面孔在黑暗中变得轮廓分明。她说:“我虽然没你们大,但我比你们聪明一百万倍。”
苏珊说:“有些事,你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懂的。” 她们两个开始咯咯地笑起来。
乔安妮说:“回你自己的床上去。”
孩子一动不动。“有一次,” 她说,声音在黑暗中听起来空空荡荡,“我看见兔子在生小兔。”
一片沉默。一会儿,苏珊问:“怎么生的?” 听着语气漠然,苏珊知道她在养兔子。她说,除非她们告诉她“那个东西”是什么。其实,她从没见过兔子生小兔,可当她们开始谈论在帐篷里的见闻时,她就忘了这一点。
那是个畸形人,名字很怪,但她们没记住。那人待的帐篷被一条黑色帘子隔成两半,一边给男士,一边给女士。那个畸形人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先对男人说话,然后对女人说,但两边的人都能听见。前面一圈都是舞台。两个女孩听到那个畸形人冲着男人说:“我要给你们看看这个,你们要是笑,上帝有可能让你们受同样的罪。”畸形人说话有乡下口音,缓慢,带点儿鼻音,声音不高不低,呆板平直。“上帝把我造成了介么样,要是你们笑,他有可能让你们受同样的罪。他就想让我长成介样,我不反抗他的方式。我展示给你们看,因为我要好好利用它。我希望你们的行为举止能像绅士和淑女一样。我从没向自己做过,也没用它做过,但我得好好利用它。我不反抗。” 然后,帐篷那边出现长时间的沉寂,终于,畸形人撇下男士,走到女士这边来,说了同样的话。
孩子感觉身上的每块肌肉都绷紧了,好像她听到了谜底,但这个谜底却比谜语本身更难以理解。“你是说那人长了两个脑袋?” 她问。
“不是,” 苏珊说,“它既是男人也是女人。它把裙子撩起来给我们看。它穿了一条蓝裙子。”
孩子想问那人怎么会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却没长两个脑袋,但她没问。她想回到自己的床上,好好想个明白,她便沿着床脚板爬了回去。
“兔子是怎么生的?” 乔安妮问道。
孩子停下来,只有脸还露在床脚板上边,她心不在焉,一脸茫然。“它把它们从嘴里吐出来,” 她说,“整整六只。”
她躺到床上,试着拼画出那个畸形人从帐篷一边走向另一边的情景,但她实在太困了,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样。她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些乡下人凝神观望的脸,男人们比在教堂里还庄重正经,女人们严肃端庄,眼神静穆如画,他们站立着,仿佛在等待赞美诗第一个音符在钢琴上奏响。她能听到那个畸形人说:“上帝把我造成了介么样,我不反抗。” 下面的人说:“阿们。阿们。”
“上帝这么对待我,我赞美他。”
“阿们。阿们。”
“他可能也让你们受介样的罪。”
“阿们。阿们。”
“但他没这么做。”
“阿们。阿们。”
“振作起来,圣灵的殿。你们!你们是上帝的圣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圣灵已经住在你们里面,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阿们。阿们。”
“要是有人亵渎了圣灵的殿,上帝就会让他毁灭;要是你笑,他有可能让你们也受介样的罪。圣灵的殿是圣洁之地。阿们。阿们。”
“我是圣灵的殿。”
“阿们。”
人们开始拍起手,但声音不太响,伴随着一声声“阿们”,有节奏地拍打着,越来越轻,好像知道附近有个孩子,正在半梦半醒之中。
* * *
第二天下午,两个女孩重新穿上那套棕色修道服,孩子和母亲把她们送回圣斯考拉思蒂卡山。她们说:“哦,天哪,哦,可恶!又得回去受苦了。” 阿伦佐·迈尔斯开车,孩子坐在副驾驶座位,母亲坐在后排两个女孩中间,絮絮叨叨地说见到她们有多高兴,希望她们以后一定再来,还说起少女时代,她和她们的母亲一起在修道院度过的美好时光。孩子对这种废话毫不在意,她贴紧锁好的车门,把头伸出窗外。她们原以为,到了星期天,阿伦佐身上的气味能好闻点儿,可惜没有。她的头发拂过脸颊,她直视着那团象牙色的太阳,镶嵌在蓝色下午的天空中间;当她把头发从眼前拨开时,就只能眯起眼来看了。
圣斯考拉思蒂卡山是坐落在镇中心花园后面的一座红砖房。一边是加油站,另一边是消防站。四周围起一道高高的黑栅栏,在古树和山茶丛之间,有一条窄砖铺成的小路穿过。一个面如满月的修女匆忙走到门口,让她们进去,拥抱孩子的母亲,也想抱抱她,但她只伸出了手,冷冷地皱着眉,目光从修女的鞋子移动到墙裙上。她们对那些不够漂亮的孩子都会亲一下,但修女却只是用力地握握她的手,甚至能听到轻微的指节响,让她们一定要去礼拜堂,祝祷仪式刚刚开始。当她们快步走过那条干净雅致的长廊时,孩子想,只要把脚一放进门里,她们就让你祈祷。
你还以为她要赶火车呢,当她们迈进礼拜堂时,她继续沿着这种不够虔诚的思路想着。修女们跪在礼拜堂的一边,穿着统一棕色修道服的女孩子们跪在另一边。礼拜堂里弥漫着薰香的气息,淡绿色和金色的飞拱一个连一个,一直延展到圣坛上方,神父跪在圣体匣前,躬着身子。一个穿着白色法衣的小男孩站在他后面,摇动香炉。孩子跪在母亲和修女之间,她们已经开始唱“皇皇圣体”了,她仍未停止那种不够虔诚的念头。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在上帝面前。帮帮我,别这么邪恶,她开始机械地跟着唱。帮帮我,让我别总和她顶嘴。帮帮我,别用那种口气说话。她的大脑渐渐平静下来,而后一片空白;但是,当神父举起圣体匣,中间的圣饼闪着象牙色,她竟然想起游乐集市的帐篷,里面有个畸形人。那个畸形人说:“我不反抗。他想让我生成这样。”
她们将要离开修道院大门时,一位大修女突然扑过来,顽皮地拥她入怀,黑色的修道服让她差点透不过气。她的半边脸蹭着修女带子上挂的那个十字架,然后修女松开她,用一双小螺形的眼睛看她。
在回家的路上,她和母亲坐在后排。阿伦佐独自在前面开车。孩子发现他后脖子上有三圈肥肉褶,注意到他的耳朵尖尖的,有点儿像猪耳朵。她母亲和他找话说,问他是否去过游乐集市。
“去过,”他说,“我去的正是时候,啥都没错过,因为他们本来说下周还有,但下周就没有了。”
“为什么?”母亲问。
“他们把它取缔了。” 他说,“有几个传道人从镇上出来视察,就让警察给取缔了。”
母亲没再接话,孩子的圆脸上露出怅然若失的神情。她转向窗外,向远处望去,一大片牧场泛着绿意,起伏绵延,直到黑黝黝的森林边。太阳是一只巨大的红色火球,仿佛浸透鲜血、被悬挂起来的圣体,当它渐渐下沉时,在空中留下了一道线,像一条红色的土路,高悬在树林之上。
<1> “骗子”原文为“Cheat”,即下文提到的奇特姆先生(Mr. Cheatam)。这里,孩子是在拿奇特姆先生的名字开玩笑。——译者注
题图:《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封面。《圣灵的殿》(A Temple of the Holy Ghost)为此全集其中一篇。
《圣灵的殿》,作者是美国作家马利亚·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1925—1964),最初跟奥康纳其它几篇小说结集出版于1955年。该小说有不同中译本。这里是新译本,译者为张鹤。《世代》接下来会分享张鹤对这篇小说的评论。
此译文首发于《世代》第2期(2017年夏季号)。 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既有思想类文章,也有诗歌、小说、绘画。《世代》第2期的主题是中产阶级,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世代》并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译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