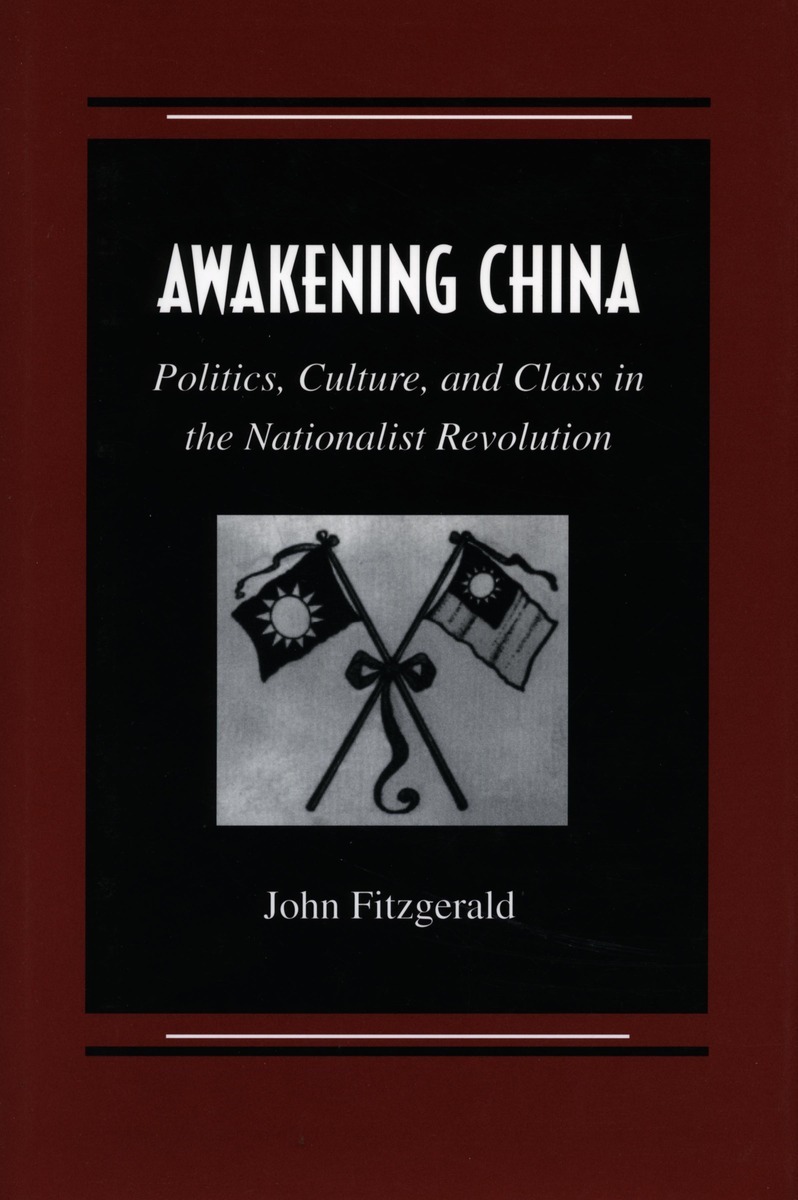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这本《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1>, 因其涉猎之广,难以归入惯常的学术分类。本书介绍了诸如革命建筑、服饰以及修辞,但却不停留在文化史;书内包含大段有关清末民初学者的讨论,却不单单是思想史;而本书钻研最细致的部分是国民党政权的党化,以及其宣传机构的形成和对民众组织的管控——就此来说,本书似乎也是制度史。
如此“汉学式”的进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书的架构和信息,但这并不妨碍传达其核心主题,即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换,和随之而来的“觉醒”和“唤醒”的滥觞。前者作为世界观的转换是清末民初的时代大背景。短短几十年间,基于儒家宇宙观的“天下”观念,与其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影响一道,被以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系统所替代。后者来自西方,同时也带来了对时间以及进步的线性观念。这也是十九世纪末少数中国学者“觉醒”后所发现的通往国民解放的道路。这个角度也应和了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思考,即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本书中对“中国佬”(John Chinaman)的人类学式的追述,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偏见,同时也反映了其对国人自身有关何为“现代”、“体面”的影响。
如书名所示,本书最核心的比喻和主题当为“觉醒”和“唤醒”。在这一点上费约翰继承了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法,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理解为两种方式的交汇,即读书人自发的觉醒,和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通过宣传而对民众的“唤醒”。本书中着墨最多的,不是自发式的觉醒,而是宣传式的觉醒;尤其在后者如何与党国体制结合,以党化政府和群众运动为手段,不断在社会中深化一个观念,即民众需要被改变,且可以被改变。启蒙也好,唤醒也罢,在职业革命者看来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如孙中山在1923年所说,“感化就是宣传”。<2>
这并不是说清末民初的国人就只能从发现“世界”和“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到“一个政党、一种声音”。不过,从历史上看,世纪之交的观念变革,从进步发展、启蒙、以及发现新的世界秩序,经过了大同式的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宪政的探索尝试,进入对同一民族和强力中央政府的理想化憧憬,最终定格在对统一革命政党及其领袖的单一话语的追求上。在此过程中,个人选择被与群体志趣挂钩——诸如衣着(如中山装)已不止于私人的范畴,而成了在公共领域彰显社群理想的方式;民族命运也与国民革命的前景相重合,一方面画出文明与进步的前景,同时又将其与某一政党的谋划相等,最终拟人化在类似孙中山的个人领袖身上。而谁又不愿有一个弃绝私利、超越党派、一心为民且以民族为最高价值的政治领袖呢?
这样一位领袖,一方面继承了帝制中国的历史传统,推崇政治独立和统一的国家体制,一方面拥护主权在民的思想。但这种主权似乎不是自由主义政治下公民社会的民权,而类似现代欧洲开明君主的自由与权力——若不开明,就有害于主权,也就无自由可予。在民初的背景下,领袖既是民众的代表、民族的英雄,又身肩“唤醒”或“启蒙”国民的重任。只有被唤醒的国民,才不会在世界上被划为沉睡的民族,才能守住主权,才能获得自由。
而这里,“沉睡”这一意象也不仅仅出现在民族主义的宣传画上。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达尔文主义使人更加清楚的意识到,人类本身也可以分为不同的支系,而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比较。无法区别理智与梦境的、“沉睡”中的族群被视为原始人。而启蒙哲学正将这样“非理性”且“原始”的心志看作“白纸一张”(tabula rasa),静待西方人以唤醒者的形象出现。殖民地地区的民众多有反抗这样西方的自赋天命,但当地人也同时在接受启蒙哲学以理性和实证为标准,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启蒙在“白纸一张”上的立场,力图发现、唤醒、改写本国民众。
若觉醒的自我源自欧洲的启蒙时代,一个孕育了理性、自主和进步的时代,其所带来的自由就既是特别的,又是普世的——前者在于只有经历启蒙的地区才有自由,后者则将实现启蒙式的自由看作全人类的使命。而这种蒙拣选的宿命感也同样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身上。在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看来,政治领袖有责任将民众从“沉睡”中唤醒,而为此需要将国家主权转移给这些“先觉者”。
有趣的是,这些政党中的“先觉者”在民众运动上并不是先行者。西方宣教士,和与其合作的中国教会,在诸如公共卫生和道德宣传上常常被后来的民族主义活动家视为模仿对象和竞争者。如书中所记,在1915年,差会的医疗工作者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参加有关肺结核的公众教育集会:杭州来了七千人,长沙是一万人,上海则有两万余人到场。由此看来,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也视图在某些领域“唤醒”或改变民众。不幸的是,他们一方面为后来的民族主义革命者提供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大部分的科学技术,但也成了后者攻击的目标。类似帝国主义与文化侵略这一类的指控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原罪。更何况,若是能让全体中国人民归信革命主义而非其他宗教信仰,岂不是一条通往富国强兵的更加直顺便捷的道路?
而孙中山一系的革命者也正是这么做的。若我们观看其对“感化”这个词的用法,不难发现一个宗教用语被纳入政党意识形态的过程。而这个词对理解孙中山最后十年组建党国的宣传十分重要。起初(1912-1919),与大环境中的宗教—道德意味相符,他在演讲和写作中对该词的使用不外乎传统精英的教化—统治观。其后(1919-1923)则渐渐变为一种对革命归信(revolutionary conversion)的表述,并有意与基督教和佛教的宗教传播相提并论。但孙中山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宗教或虔信本身,而是其所伴生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和一传十、十传百的宣传手段。若基督徒能为信仰舍身,那么革命者不也能为革命主义献身吗?若举国上下皆信仰革命主义,革命还有难成的吗?
革命归信带来胜利——这种可能性恰恰是孙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所看到的。这也是他所愿见的,一种以政党意识形态“感化”民众所带来的世俗化的、政治性的结果。若布尔什维克能成功地“感化”其军队,使之成为革命的军队,并“感化”其民众乃至全国,那么国民党在中国亦可效法,通过群众宣传“感化”国内的敌人。“苟为国人所信仰,苟我党员能尽其聪明能力,说之使明,则当无不受其感化者”。<3> 至此,孙已定下党国的规划:化党员为革命主义的虔信者,再由其通过宣传带领全国归信。
1924年六月,孙中山在建立黄埔军校之后,为同在广州的宣传讲习所致开幕辞。“感化”是他演讲的核心主题。他讲到,如果军校是教学生用枪炮斗争,该讲习所就是教人以文字作斗争。在这里,学员的目标就是宣传,即“感化”民众,使其对三民主义“心悦诚服”。为此,这些党员同志们需得自己先达到“至诚”——“要能够牺牲世界一切权利荣华,专心为党来奋斗”,好使革命事业“大告成功”。<4> 在这次演讲中,孙既没有提到宗教也没有提到苏俄。他似乎已拆下了这些脚手架,准备带领党员去使整个国家归信了。但他在短短九个月后于北京突然去世,却打乱了他的计划,直到其以意识形态和群众运动为基础的革命事业在中共那里找到了真正的继承者。
“感化”,作为“觉醒”或启蒙的一种形式,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一直坚持在个人道德提升与社会建设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曾一度有多种解释。事实上,宗教、道德、现代化等因素在解释和指导个人行为与社会意义之间的关联上常常难以分割。例如1910年前后所兴起的感化院,就多作为少年管教所,以期用宗教感悟提升少年犯的道德水准,“化莠为良”,助其重新融入社会,建设国家。但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个人的改过自新在国民层面被赋予极强的重要性。个人行为与国家强盛挂钩。以忠于政党意识形态为准的政治救赎,也开始垄断对改过自新的解读。二三十年代的感化院,已成为国民党在思想上改造政治犯的场所。于是,政治正统代替罪,成了悔改的内容;而革命也就取代救恩,成了感化的目的。
<1> 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2> “国民党奋斗之法宜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1923年,《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392-401页。
<3> “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1923年,《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379-384页。
<4> “言语文字的奋斗”,1924年,《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479-482页。
此文题图:
《唤醒中国》英文版封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年,https://www.sup.org/books/title/?id=2106。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7期主题是“和合本圣经、五四运动”,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欢迎访问《世代》网站:www.kosmoschina.org。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