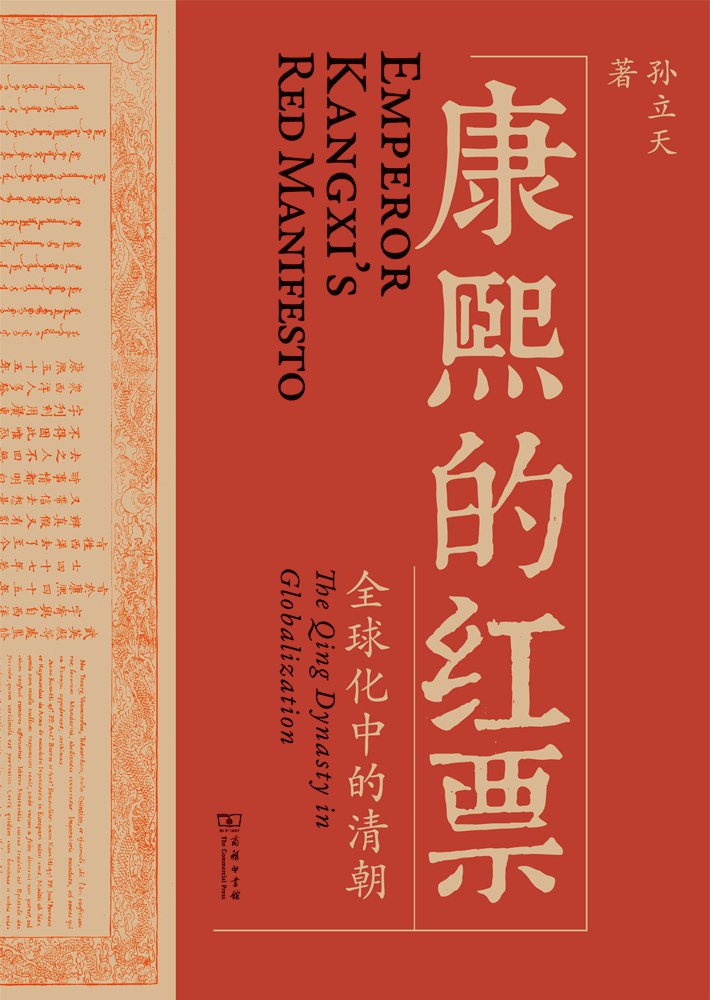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来源: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794613/]
西谚云,魔鬼藏于细节中,暗指细节隐藏陷阱或神秘元素,忽视之将有麻烦。这句谚语的早期版本,名为上帝藏在细节中,告诉人们一旦投入精力做某事,就当彻底认真完成。一反一正,意思都是说细节很重要。后来,这句谚语还出现一些新的版本,其中一种就是真相(如果有的话)藏于细节中。<1>
对于以求真为目标的历史研究来说,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发现问题,挖掘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挑战陈说,别有新解,已属不易。除此之外,还能够让读者获知新解时感到兴味盎然,引人入胜,这就难能可贵了。《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正是这样一部难得的佳作。
一
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清初西洋传教士深受皇帝信任?他们与康熙是什么关系,又以什么身份在宫廷行走?作者认为这些清初行走于宫廷的西洋传教士,与清帝是主奴关系,主奴关系是他们得到康熙信任的基础(第77—80、124页)。所谓主奴关系,原是满人游牧传统中军事等级关系和社会等级关系的基础,奴隶和牛、马、衣服同为主人的私有财产。随着满人势力兴起,对外扩张中出于对劳动力的现实需要,这种主奴关系虽然范围扩大,仍被置于家庭关系的框架中。主奴之间推崇以家为纽带,和睦相处,用努尔哈赤的话说,就是要形成一个“奴才爱主子,主子爱奴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主人负责奴才的生活,奴才对主人尽忠。主人和奴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奴才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主子的社会地位(第114页)。主奴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可以世袭,而且即便取消奴籍,这种关系包含的派系源流依然存在并且有效(第124页)。
满清入关建立大清,沿用明朝体制的同时,保留原有的主奴关系,于是满清统治的权力运作方式就呈现出两种模式,即君臣名分的官僚体制(公)和主奴名分的私人网络。这样,清初皇帝的权力运作就出现汉人传统的“王者不受私”<2>和满人重私家关系之间的张力(第116页)。在作者看来,由于西洋来华传教士与清帝是带有“私家”特点的主奴关系,那么围绕传教士与皇帝的关系,比如清初历狱、康熙与教皇使节关于天主教礼仪问题的争议、雍正禁教等天主教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新解。
本书共七章,分三部分展开论述。我们或许可以用家奴、家事、出家分别概括这三部分的内容。这里的“家”,相对于朝廷官僚制度的“公”与“外”,突出的是满人主奴关系的“私”与“内”这一属性。
家奴。第一部分(1—4章)追溯西洋传教士如何进入满清权贵圈,成为清帝奴隶。原来,明清鼎革之际,清军西征,原本任职于张献忠朝廷的来华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做了清军统帅、也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俘虏,沦为满人奴隶。后来豪格在政治斗争中死于狱中,利安二人的奴籍身份转入正蓝旗汉军都统佟图赖名下。因交涉大炮生意,佟家与传教士相善,而佟图赖又是康熙外公,于是传教士自然被划入清初外戚集团。相比于从明廷转投满清,做了大清官员的汤若望,利安二人佟家奴才的身份,在清初政治斗争中展现出更大能量。比如1664年由杨光先发起针对天主教神父的历法之争,汤若望等传教士经过历狱最终能全身而退,其实有利安二人背后的佟家势力暗中相助。此案让传教士明白一个道理:关键时刻与汉人士大夫的关系不但作用不大,还可能招致灾祸,满人权贵圈才是应该接近的目标(第63—64页)。
康熙继位后,无论是铲除鳌拜、平定三藩、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还是征剿蒙古准葛尔丹,都可以看到西洋传教士的影子。后来入华的传教士,无论是第二代的南怀仁,还是第三代的张诚、白晋,其实都继承了利安二人之于清室的主奴关系。他们不仅受康熙委派办事,同时也教授康熙西学。康熙对于西学发生极大兴趣,用功研究,在作者看来并非出于自然,而是身受周围传教士的影响。也就是说,康熙先是自幼接触传教士,与其先有私交,受其熏染教导,才有西学兴趣(第108页)。而传教士能接触康熙,获得信任,就是因为他们是内务府的人,是归内务府管理的皇帝的包衣奴才。内务府就是清帝的“私家官僚系统”、“私家政府”,本身独立运作于整个国家官僚系统之外,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人事任免、案件审理权、军队,以及遍布全国的通讯系统,还可以接待外国使团,朝廷礼部和理藩院均不得干涉(第116页)。靠着从内务府发出的印票,传教士得到地方官员优待。而传教士也凭借与康熙的主奴关系,得到信任并进入其私人关系网络,享有特权,受差完成康熙分配的任务。当康熙要绕过朝廷处理一些事务,把“国事”操办成“家事”的时候,就会交由内务府来办。比如两次接待教皇使节和彼得大帝使团,因为绕开礼部,史官没有记载,因而不见于官书史料。
家事。第二部分(5—6章)是全书的核心,围绕康熙的红票叙述了相隔10年康熙两次接待教皇派来的使节,彼得大帝派来的使团先于教皇第二个入华使团一周入京。家奴的身份交代清楚后,接下来就转入家事部分。1704年,教皇签署教内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的祭祖和祭孔礼仪,并于1705年派遣首位来华特使多罗前来中国沟通。康熙最初没有兴趣接见多罗,经在京耶稣会士恳求,并看在“豢养尔等多年”的分上最后同意接见(第161页)。所以,康熙这次接待多罗使团,从始至终并没有将其当作外交使团,没有让朝廷部门参与。从接待规格和礼仪来看,康熙其实是把多罗当成在京耶稣会士的远房亲戚。直到辞行会见的当天,惮于耶稣会士在清廷巨大能量的多罗,都没有公布教皇禁令,避免将康熙卷入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直到他所推荐的福建主教颜珰面见康熙闯了祸,回程途中的多罗才在南京公布禁令,反对天主教神父向朝廷领票,最后多罗在澳门遭到软禁,客死中土。
但是康熙要求在华传教士领票,其实不是为了限制天主教,而是拒绝对利玛窦规矩的改变(第194页),并没有因此关闭与教皇交往的大门。所以在1706年6月多罗离京之后,当年10月康熙就派出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代表他出访罗马,不幸二人在途中遭遇海难。1707年10月,康熙又派耶稣会艾若瑟和陆若瑟两位神父出使,艾若瑟最后抵达罗马见到教皇,却被教皇要求留在欧洲,不要返回中国。在1706年到1716年这十年中,康熙一直在打探四位“洋钦差”的下落(第207—211页)。一直到1716年康熙从北京耶稣会神父那里看到教皇1715年签署的谕令,重申1704年所签署的禁约,于是决定主动出击,让内务府印刷红票,交由广东官员发给往来的西洋船只带回欧洲,实际上等于向欧洲发了一封兼有寻人启事意味的公开信。
红票也确实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艾若瑟被允许回大清,同时教皇派了第二个使团前来解释。碰巧彼得大帝派来的使团也来到北京。这两个使团的接待都是由内务府操办,没有走正式的朝廷渠道,因此不见于后来的官方史书。经过双方的谈判交涉,教皇派出的第二个使团终于拿出通融条款,康熙表示满意。作者从史料的细读中得出结论,历来广为引用的康熙对教皇禁约的批注,并非其禁教的铁证,其实是康熙的谈判技巧:说狠话,兼略施政治手段,最终成功叫对方亮出底牌(第236—240页)。
出家。第三部分(7章)叙述了雍正登位后禁教,一度辉煌的天主教自此陷入沉寂。在作者看来,雍正禁教并非许多人所以为的是康熙禁教政策的延续,因为康熙本身就没有禁止天主教。雍正禁教,是因为深入满人权贵圈的西洋传教士卷入了夺嫡之争。雍正登上大宝后,立刻换掉原有内务府人马,将传教士逐出内务府,意味着传教士失去了新皇的信任,不再享有康熙朝经常面圣的特权。这对于天主教在华传播确实打击沉重。西洋传教士走到这一步,其实反过来说明他们与清帝的主奴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当这种关系得以存续时,作为家里人的传教士就能享有各种特权,在华教务可谓无往不利;一旦他们在专制皇权继承的权力斗争中站错队、押错宝,等待他们的就是失势者被扫地出门的命运。那么,既然康熙朝的传教士对于主奴关系的重要性心知肚明,为何不趁早在当年的皇四子身上下足功夫呢?作者认为这是后见之明对传教士的苛评,因为传教士并不知道历史后来的演进,只是基于当时的观察做出最好的选择(第257页)。与从小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兴趣浓厚的康熙不同,雍正年轻时候就开始佛教修行,造诣颇深,登位之前就是佛教界的风云人物(第279页)。他本人对西学也没有兴趣。所以,雍正禁教与其说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不如说是出于政治斗争背景下个人意志的决定。尽管如此,与新皇的私交仍然左右在京传教士的命运。比如做过雍正音乐老师的传教士德里格,能够在禁教期间解除软禁,在北京建立教堂,依靠的正是与雍正曾经的师生关系(第282页)。
二
在论述传教士与清帝的主奴关系,呈现皇帝的私人权力运作特点时,作者深入史料,挖掘历史细节,使得论证有理有据。兹举数例。比如本书开头,作者注意到1655年利类思和安文思写给顺治皇帝的奏本,其中提到他们被佟图赖“豢养”(第3页),其实就是承认他们与佟家的主奴关系。尽管二人的奴籍两年前已经解除,但满人传统主奴间的派系政治纽带并不会解除(第25页)。“豢”一词最初表示喂猪(豕),满人主奴关系之下,最早奴才和动物一样,主子负责他们的吃喝,像动物一样养奴才(第201页)。康熙之所以答应接见教皇派出的多罗使团,也是看在对传教士“豢养尔等多年”的情分上(第161页)。内务府江宁织造曹寅,在给康熙的密折中就自称包衣奴才,说自己“从幼豢养,包衣下贱”(第122页)。
又比如叙述清帝与传教士的亲密关系时,作者多从称呼和交往细节入手。顺治帝几次拜访汤若望的教堂,公开用满文喊汤若望爷爷(玛法)(第31页)。南怀仁死后,康熙钦赐谥号“勤敏”,将之与军功卓著的佟图赖(“勤襄”)并立为“勤”字档,其墓碑文字除汉语外又有满语,说明康熙把南怀仁当成自己人,备极恩宠(第98—99页)。康熙与南怀仁的私交,最令人称奇的大概是1682年东北祭祖的旅行。根据南怀仁的记载,随行的南怀仁与众人在河岸等船,没想到先渡河的康熙带着太子和几个权贵把船调头回来,专门折回接南怀仁。这让在场的满人切实感受到了南怀仁与康熙不一般的关系(第91页)。而南怀仁在写给欧洲的信中,把康熙当作自己的一个聪明学生看待,字里行间对康熙流露出真感情(第90页)。康熙在家训里还制止过大皇子拿传教士徐日升的大胡子开玩笑(第99页),并且还借给传教士一万两银子修教堂,说“伊等皆为外国之人,除朕之外,又有何人照顾伊等?”俨然是满人大家族主子对奴才的做法(第324页)。传教士似乎也把内务府当作自己的娘家,想修教堂就写申请到内务府要求拨地,请内务府发信给工部借库存的杉木;需要马匹出远门,又是内务府开条子到兵部借马。他们生病了,康熙就给他们找中医,骑马摔伤了则给他们找满人或蒙古人的医生;春节时,康熙还会按照打赏包衣奴才的惯例给传教士发红包(第130页)。康熙在教皇使节和耶稣会的争执中,明确说自己无条件支持耶稣会士,把他们比作自己养的狗,说的是打狗欺主的满人游牧文化。而传教士也知道投桃报李,在与俄国人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过程中,始终忠于清廷,维护中方利益。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与清帝的关系是主奴关系,所以传教士白晋给康熙的满文折子中,也称康熙为“明主”“大主”和“仁主”(第131页)。
再比如叙述康熙接待多罗使团时,作者认为康熙从头到尾都没有把多罗使团当作外交使团,没有通过朝廷部门来接待,而是基于他和传教士的关系,用私人家庭会见的形式和多罗使团见面,相当于作为一家之主的康熙接待其他奴才的亲戚。整个接待过程由内务府一手包办。作者特别提及,接待多罗一行安排在下午两点,由内务府专用通道故宫西门进入,会见地点是皇帝平时游玩的一处园子。与此相对的是,正式的朝廷接见,则是从故宫南面过午门进太和门入太和殿来拜见皇帝,时间安排在上午。从接待多罗使团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安排来看,都符合康熙最初对整件事情的定位:一次私人聚会(第166页)。因为是私人聚会,康熙允许多罗可以选择用欧洲屈膝的方式行礼,他自己还盘腿坐在垫子上用满人方式接见,并告诉多罗在座的耶稣会神父都是自己人,让他放松不要拘谨。客套之后还端出点心招待客人。完全是满人接见家人亲戚的方式(第167页)。这种由内务府操办,把国事变为家事的方式,好处就是绕过朝廷部门的各种礼仪和牵制,便于皇帝根据个人意志直接行使权力。此后在接待彼得大帝入华使团和教皇第二次来华使团时,康熙都是采用这种私人会见的形式。作者花了相当篇幅叙述这三次接待的路线安排和会见时的场景细节,除了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明清帝在朝廷官僚制度之外,另有一套私人权力运作机制。
这种从小处(细节)切入,着眼大处(比如制度),挑战陈说的研究路径,确实呈现出细节之于历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及魅力。比如时间上的细节。作者引用前人研究,从礼部当天把杨光先的奏本转到议政王大臣会议那边,推测杨递这个奏本是满人上层提前安排好的。因为速度之快,审理机构又是满人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均表明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第46—47页)。整个历狱事件围绕的争议其实与天主教教义无关,而是风水问题的政治化。历狱审理前后持续八个月,同样由议政王大臣会议主理的鳌拜案却仅用短短八天即告结案,前者久拖不决的背后有满人权贵势力暗中帮助(第60页)。作者还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1690年康熙会见传教士的记录表中,发现康熙在军务繁忙中不忘学习西学,可见他对西学不是一般的兴趣,而是相当深入(第83—84页)。更精彩的是,作者注意到,多罗辞行会见康熙到第二天临时增加的会见之间,有一个下午,由耶稣会士编写的《北京纪事》(Acta Pekinensia)有意忽略之。而恰恰是这个下午,康熙找来耶稣会神父会谈如何回信教皇,第二天在临时增加的会见中就突然提到中国礼仪问题。这说明康熙卷入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责任不在多罗,而在耶稣会神父(第181、185页)。
三
这些基于历史细节的合理推论,不但让人们更为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显示了作者对材料的细读功夫和辨析能力。这同样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比如关于红票的内容。一般人读过之后得到的印象就是康熙两次派出传教士出洋无果,红票仅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但是经作者点出,读者才恍然康熙此举其实是向教皇讨个说法,这是他早年与西藏统治者打交道的故技。作者还发现,红票文字经由满语翻译为汉语,全是口语,显然未经内阁大学士润色,有些地方读起来不通顺,说明康熙一直坚持他与罗马的联系是他的私事,不牵涉朝廷官僚(第212—213页)。如果没有前述康熙接见多罗一行当作私人会面的知识,单从红票的内容和用词,很难看出此中深意。
作者细读材料的功夫,还体现在把局部的材料置于整体环境中解读,避免断章取义,被材料的字面意思误导。这方面精彩的例子就是对康熙批注教皇禁约的解读。1721年1月,教皇在接到康熙的红票之后,派遣嘉乐一行来京进一步沟通礼仪问题。嘉乐向康熙呈上教皇禁约全文,希望康熙指出哪些条款可以在中国施行,哪些不行。康熙明白嘉乐是在试探自己的底线,没有逐条回复,而是在禁约背面用红色御笔写了一段批注,全面否定禁约:
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第237页)
这句话常被引用当作康熙禁教的铁证。但是作者发现,康熙当天让宫中奴才把禁约批文递给嘉乐时,随附谕旨说以后不要见面,但可用文字沟通,如果嘉乐不能与在京耶稣会神父达成共识,他会再印红票,让俄罗斯使团带回欧洲讲明道理。康熙的谕旨显然不是“免得多事”的举动。而且当天康熙还下令逮捕潜入北京的利安国,他是罗马派到中国的巡视官,来督促北京耶稣会神父遵守教皇禁约。将利安国带到嘉乐面前审问,意在给嘉乐一个下马威。果然,第二天嘉乐就亮出了教皇的通融条款,康熙读后表示满意。所以,康熙禁约的批注不是真的“免得多事”,而是谈判老手的策略(第236—240页)。
作者对材料的细读功夫,也表现为情景代入,替历史人物说话(第128—129);搜罗零散材料,以类相从,呈现较为完整的事件图画(第130、207—211页)等方面。在从细节入手接近历史真相的同时,本书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呈现,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身临其境的代入感。这也是细节之于历史写作的独特魅力。比如作者根据耶稣会士留下的多罗使团访华的记录《北京纪事》,不吝笔墨叙述当事人的举止神态以及接待细节,让读者仿佛亲自体验康熙私人会见传教士使团的情景。类似的场景刻画也见于作者对康熙接待彼得大帝使团和嘉乐使团的叙述。除此而外,作者刻意从传教士留下的记载中,抉出丰富的细节,让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皇帝形象。比如从汤若望的记载中,我们知道顺治会为了喜欢的妃子打过后者的丈夫(第50页);康熙会在浩瀚的夜空下听传教士讲星星,趁机卖弄自己的天文学知识(第91页)。
四
可以理解,作为一部从学术著作改写为面向公众的著作,对细节和代入感的追求有着市场化的考虑(第380—381页)。因此在叙事中有时难免有因追求戏剧化并未忠实于史料的个例。<3> 这似乎也无伤大雅。毕竟作者对历史场景的想象还未脱离材料的限制。而基于材料对历史细节的合理想象,既满足了读者对代入感的需求,也是历史写作中常用的手法。比如司马迁没有亲历鸿门宴,但是后世的读者并不会认为《史记》是在编造。同样,南怀仁的《鞑靼旅行记》没有记载康熙和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围坐看星星时有篝火,但是读者大概不会认为作者把这个场景与今天的户外野营作类比,加入篝火这个细节就显得不合理(第91页)。<4>
本书为了照顾现代读者的阅读体验,所下的另一层功夫,就是使用现代语言和例子来解释历史现象。比如解释明清之际传教士称呼满人为“鞑靼”(意即蛮族),作者联想到现在一些欧洲餐馆的菜谱还能看到一道菜叫“鞑靼牛肉”(Tartar Steak),非常形象地刻画出欧洲人印象中“鞑靼”的原始感(第30页);满人最初的八旗结构,某种程度上类似现在的股份制,各旗是因为各自“私”利联系到一起,最后大家共同分配得来的利益(第117页);无论从康熙规定领票的初衷还是后来的实际操作上看,康熙要求领票其实跟今天开车需要领驾照相类似,目的是为了规范,不是为了限制(第200页);雍正不是大众认知中一般烧香拜佛的佛教信徒,他和普通佛教徒的差别,就像一个偶尔打打乒乓球的人和国家队一线球员的差别(第275页)等等,不一而足。作者还用“摸着石头过河”,来描述罗马最初处理中国礼仪之争的谨慎态度(第189页),以及顺治皇帝平衡满汉传统的政策多变(第35页)。但是这些及类似的其他举例和用语,并没有充斥于一般历史通俗读物中的肤浅对比和哗众取宠。
总体上,本书做到了雅俗共赏。普通读者在享受阅读快感的同时,也能从作者提炼的史识中得到启发。比如作者谈到对清初历狱的发起者杨光先的评价时,就认为历史人物评价有两种,一是当时的人,历史参与者流露出的主观感觉,二是后来人综合历史上下文的评判。两种评判可以不同,但后来的历史评判不能无视当时人自身的感受(第42、300—301页);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中理解(第148页);历史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书写的,它同时也是一个素材库,无论什么理论,在其中总能找到所需的材料。但材料的质量高下有别,新出现的材料可以起到纠正陈说的作用(第216、289页);如果对历史脉络没有完整了解,就只能看到字面意思(245页)。而对于想继续深究相关议题的读者来说,本书则提供了原始材料的出处,有些材料已制作成电子版,可从相关网站查阅。<5>
以上主要从材料的细读和历史写作的角度,说明细节之于历史的独特魅力。本书在叙事中对历史细节的呈现比比皆是。事实上,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使用“细节”一词共39次<6>,其中有4次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将要叙述的细节(第59、185、240、282页)。但是,如果以为作者只是从技术的层面(材料解读与历史写作)来看待细节,则忽略了作者还赋予细节历史哲学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在作者看来,历史并没有什么规律,也不抽象,它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共同演绎出来,忽视历史中的个人和那些有血有肉的细节,就否认了个体生命中展现出的偶然性和不确性,可能会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第309页)如何挖掘,又如何呈现,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至于最后挖掘出来的是“魔鬼”还是“上帝”,是推翻陈说,还是别有新解,又或者是其他,这趟探索历史真相的旅程总是充满令人难舍的魅力。
<1> Gregory Titelman,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Popular Proverbs & Say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119.
<2>如《史记·孝文本纪》:“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闲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见司马迁,《史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5页。
<3>比如作者写道,利类思和安文思在战场上遭遇豪格大军,赶来补刀的满人士兵在手起刀落的一瞬,因为发现二人的西洋面孔,就突然停止砍向两位神父的刀。两位神父为此感谢上帝,认为是上帝救了他们(第6、27页)。作者引用的资料来自英文版利类思写的安文思传记(Buglio, “An Abridgement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F. Gabriel Magaillans”, 345)和古洛东写的《圣教入川记》。然而查考所引资料,关于二人生死瞬间的记录仅出自《圣教入川记》,其中的叙述是,利安二神父落入满兵手中,满兵见其面目为泰西之人,打算引往营棚。正行间突然来满兵二人,抽刀欲杀神父,幸亏又来一满兵操满语阻止。后来另一种说法是,满兵二人举刀欲杀神父之际,突然一兵飞至吼阻,言二人系汤若望之友。二兵闻言,即收刀入鞘(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页)。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没有出现满兵欲杀二神父,忽然看见其欧洲面孔,于手起刀落之际刀下留人这样的情节。这种戏剧化的情节是各种小说、影视戏剧常见的桥段。
<4>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见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5>比如1661年编订的士大夫给汤若望的祝寿文集《碑记赠言合刻》,作者介绍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有电子版(现在用谷歌图书搜索已可取得该书电子版)(第38、316页);康熙1692年发布的容教诏书最早抄本,可从内阁大库资料网站调阅(第322页)等等。本书叙述清初历狱依据的主要史料《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以及关于康熙接见多罗使团的原始材料《北京纪事》(Acta Pekinensia),作者均有简介(第317—318、323页)。
<6>参见全书第24、316、46、57、59、62、70、77、104、111、128、166、180、182、184、185、187、201、210、223、234、240、241、258、259、263、282、284、287、300、305、309页。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4期的主题是“晚清教案”,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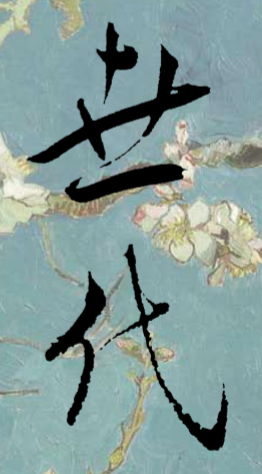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