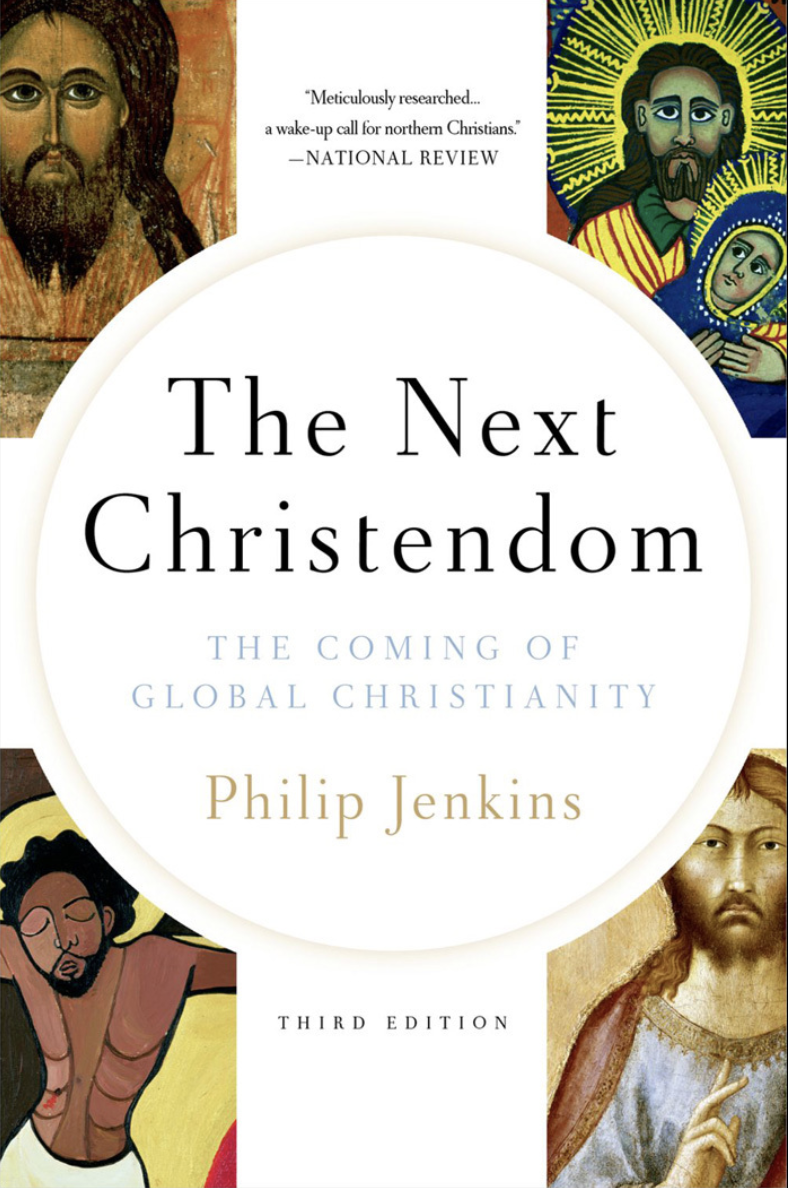
[题图:菲利普·詹金斯 (Philip Jenkins),《下一个基督教王国》英文版封面(2011年)]
20世纪也许是基督教发展史上最跌宕起伏的时期。世纪初那非凡的宣教热潮,曾放眼世界,誓要将福音在一代人之内传遍全球,其后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民族革命的冲击,逐渐归于沉寂。然而,20世纪下半叶,当宣教和宣教学在西方反殖民话语的抨击下挣扎图存时,基督教信仰在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社群中已经扎下根来。在许多地方,基督教传统首次通过回应人们的真切需求,成为无数归信者鲜活的传统。
本文旨在探讨基督教如何回应当地社会在公共层面上对医治和救赎的需要。具体来说,即初来乍到的基督教,如何在不同的程度上启发并满足了不同处境中人们对尊严的愿景。人们之所以加入信仰社群,通常是因为基督教传统帮助他们构建了复兴的盼望,使他们从危机中获得某种救赎。而这些当地人的需要,或者说他们归信的原因,常常被划分为物质与属灵、公共与个人这样相互对立的领域。这样的分类虽然有用,但人们如何以及为何接纳新信仰,其中的复杂性却无法用二分法简单解释。个人危机通常是更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的产物,而物质和属灵的动机往往相互作用,共同带来归信和转变。
除了满足个体的需要,我们还可以看到个人的敬虔和操练如何推动社区倡议和公共运动。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新兴的本土基督教——尤其是灵恩教会——正在为当地社区带来重要的医治和重建。他们也勇于考虑在更大的层面上寻求救赎,即社区乃至社会层面的救赎。尽管基督教并没有使当地民众摆脱宏观的历史潮流,并且各地情况也不尽相同,但基督教信仰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可以更好地应对当下的危机。
一 贫乏的人有福了
正如菲利普·詹金斯 (Philip Jenkins) 在他的著作《下一个基督教王国》中所说,自宣教事业成立之初,当地人就常常将基督教看作“令人振奋、甚至陶醉”的信息。<1> 这是因为当地人的属灵干渴在信仰中获得了确实的满足。这种干渴当然与个人因素有关。与此同时,这种对拯救和尊严的渴望也复兴了诸如弥赛亚、千禧年和乌托邦运动这种更大层面上的传统。从殖民统治下的拉丁美洲到晚清中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墨西哥独立运动中的神父和太平天国中的洪秀全(1814—1864),都以基督教上帝的名义寻求社会平等。<2>
出于其在社会救济方面的出色表现,灵恩运动对当代拉美社会尤其具有吸引力。众多对拉美灵恩主义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詹金斯也以此来解释南半球教会的飞速发展。<3> 詹金斯认为,第三世界城市中的数十亿人口已经沦为“后工业时代的流浪者”,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伴生物。许多人从原本熟悉的农村或部落中被连根拔起,大量涌入大城市打工。而大城市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或基础设施,来满足流动人口急剧增长所催生的需求。鉴于民众需求与社会供应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即使是最保守的教会也难以忽略社会慈善。而这类事工往往成了政府体系之外的医疗、社保和教育领域的社会服务。这也意味着,当这些人不得不告别过去的农村生活,教会就成了他们新的人际网络,而牧师也就扮演了旧时关系中类似于村长的角色。<4>
教会在社会救助上的努力,在有效加深人们委身当地基督徒社区的同时,也超越了经济、种族和性别的隔阂。<5> 通过为社会边缘群体(例如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和中美洲的玛雅人)带来家庭感和团契感,教会在最穷的人中发展迅猛。如果不是教会,这些人就无从学习那些必要技能,来帮助他们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谋得生存。这种社会资本为巴西的黑人、混血族裔 (mestizo) 以及妇女提供了重要的上升渠道。詹金斯举了一则质朴而感人的例子:一位被西班牙男权文化 (machismo culture) 压伤的灵恩派妇女,在遇到了一个“从不抽烟喝酒、讲礼貌、有稳定工作” 的敬虔男子后,在生活中找到了医治。<6> 教会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其非凡的社群性容易给人带来信赖和安慰,以及具体的社会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施与受的良性循环。这通常与充斥着冷漠与贫富差距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不论外界是公元250年的罗马帝国,18世纪工业化进程中的英格兰,还是当下的尼日利亚或秘鲁。<7>
除了肯定教会在社会职能上的作用,詹金斯也提醒我们不要抛开问题的核心:这种特定的社会参与来自于对超然上帝的信仰,相信祂是“直接掌管每日生活”的神。<8> 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归信的基督徒得以抓住医治和更新的应许。这其中既包含属灵层面,也包含身体层面。由于公共卫生机构的条件所限,新兴教会无法只顾属灵医治而忽略身体医治。这两种医治的观念原本就相辅相成:剥削和暴力本身并不在邪灵的范畴之外,同属于需要更新之物。<9> 总体而言,人的归信会带来人际关系和自我认识的改变,进而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使他们对尊严和团契有了更高的期望。
二 服侍那卑微的和骄傲的
不久前过世的拉明·珊拿 (Lamin Sanneh,1942—2019) 在他的《谁的宗教是基督教?》一书中认为,教会正面临不可避免的挑战,即“打破宗教私人化的传统,好对公共伦理产生影响”,同时留意避免落入教会过度参与政治的陷阱。<10> 他进而提议,信仰规范辅之以具体行动,就有能力为众多不同的社会指明出路。基督徒应该谋求公共福祉,帮助受苦的人找到救助和盼望。<11> 同样,在全球化的阴影下,当地的价值观和经济、社会错位和边缘化、家庭的重要性和社群的意义,都应是本土基督教运动所应当回应的目标。<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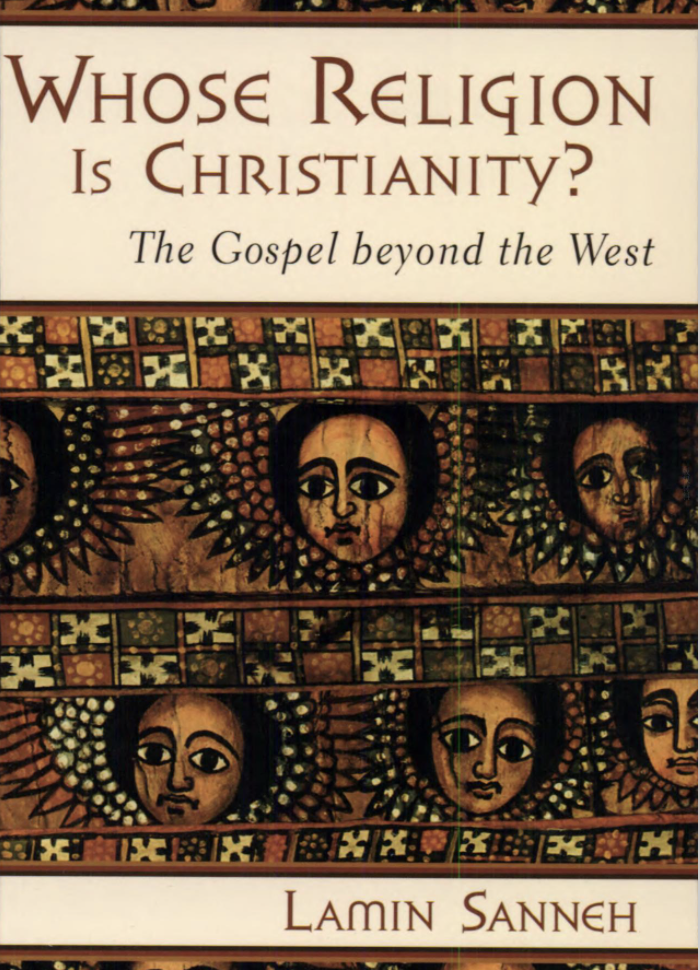
[插图1:拉明·珊拿 (Lamin Sanneh) ,《谁的宗教是基督教?》英文版封面(2003年)]
不过,本土基督教运动的一些侧面,有时会让最支持世界基督教的人也感到惊讶。珊拿大概并不赞成国家或民族救赎的概念,因其与乌托邦主义太过相近。但在殖民地枷锁下生活的许多人,依旧不断地在基督教中发现自由和拯救的信息。例如,魏乔康(Wi Jo Kang)在《近代朝鲜的基督与凯撒》一书中提到,以美北长老会派往中国的宣教士倪维思 (John L. Nevius,1829—1893) 命名的“倪维思法则” (Nevius Method) ,对朝鲜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广泛采纳了建立自养、自传和自治的本土教会这一目标。朝鲜在数百年间一直受制于儒家体系和意识形态,在政治上臣服于中国。宣教运动所提倡的平等思想使一些朝鲜人重拾盼望:他们同样配得摆脱帝制,享有独立。<13>
有时,公众领域的宣教事工也会被本地人整合成社会乃至国家层面的救赎设想。语言和字母对于发展民族认同至关重要。还是以朝鲜为例。谚文 (Hangul, 也称“音文”、“朝鲜字母”等,是朝鲜语所使用的表音文字) 虽然在数百年前就已被造出并下旨推广,但直到19世纪末基督教宣教士到达朝鲜时,才在翻译和印刷圣经这一过程中被实际使用。就这样,谚文的普及,作为最初促进宣教事业的语言工具,帮助唤醒了朝鲜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精神。在之后日本殖民化的威胁下,谚文具有特别的意义象征。<14> 尽管力量有限,但在反抗日本强加的国家神道教时,朝鲜基督徒还是反映出宗教尊严鼓舞了人们对抗军事强权。<15>
在日本,类似内村鉴三 (1861-1930)的本土基督徒领袖,也试图从国家救赎的层面来理解初来乍到的基督教。这种解读往往与西方宣教士的神学和宗派立场不同。在基督教传统和武士传统的双重影响下,内村认为,虽然武士道无法拯救日本,但若换成儒家化的基督教信仰,或是嫁接到武士道传统上的基督教,就不仅可以拯救日本,还可以拯救世界。<16> 这其中不乏日本中心主义,但寻找基督教信仰和日本文化之间的接触点,对信仰进入当地文化而言是必要的。只针对当代个人生活的基督化是不够的。如果基督教传统确实是普世和大爱的,它就能够并且也需要救赎日本的过去,并回应上帝是如何在日本历史中做工这一问题。一旦认识到这种新兴的价值或尊严,没有哪种文化会因为太落后或太异教而无法接受基督。<17>

[插图2:日本基督教作家内村鉴三(1861—1930)肖像(摄于1928年)]
在当时像内村这样的失意武士,往往能在基督教中找到新的尊严和社群感。但是,正如马克·穆林斯(Mark R. Mullins)在《日本制造的基督教》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日本,成为基督徒的代价太高,这似乎是拦阻人们接受基督教的一个巨大障碍。这一新信仰最初所吸引的主要人群,多属于被边缘化的群体(被排除在明治政府之外的武士)或特权阶层(地主或小工厂主)中的少数群体。前者已经失去了先前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本就需要自谋出路;而后者则并不容易在传统风俗上(例如祖先崇拜、神道教参拜等)受到社群的制裁。<18> 然而,这两个群体并不能代表日本社会的大多数。
穆林斯认为,与朝鲜的经历相比,日本从未有过让基督教褪去“反常”或“外来”标签的历史机会。<19> 朝鲜人在殖民时期所面对的国际敌对势力(即日本)与基督教信仰的来源(西方国家)不同。因而,基督教不仅脱去了其外来的身份,也与朝鲜民族本身产生了正面的联系:大多数朝鲜人认可基督教在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维持朝鲜民族身份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认知的转变并没有在日本发生。当日本成为殖民大国,其帝国冉冉上升的优越感以及军国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让追求尊严和社群的基督教缺少发展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长期经历贫困的拉美和非洲不同,日本迅速的工业化只给了基督教相较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更短暂的机会窗口。对日本人而言,世俗领域似乎已经兑现了民族救赎这一承诺。
三 民族医治的构想
对于那些在二战后没有继承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因为缺乏公共空间和经济稳定,基督教对尊严和社群的强调也吸引了社会光谱中更多的人。例如,在阿尔韦托·藤森 (Alberto Fujimori) 时期的秘鲁(1990—2000),福音派社群一直积极参与被称为生存组织的事工,例如“牛奶委员会”,即由成千上万备受经济危机打击的福音派妇女发起,与她们的非基督徒邻居一同解决社会问题。出于爱和尊严的缘故,她们彼此合作,将关怀事工延伸到教堂之外,借此活出自己的信仰。通过在一个排斥她们的社会中通力合作,她们秉持在威权主义环境中人的尊严。正是在这种城市边缘地带,她们找到了新的团结。<20>
这种对公共美德和公民身份的道德贡献,特别是在系统性腐败的情况下,超越了经济需求的领域。社会科学的学者们早已在思考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这一概念。该概念描述了宗教实践(其原意在于使信徒内化信仰价值)赋予信徒以一些必要技能和行为,可以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本地基督徒在参与教会时往往发展出一些带领的技能,例如演讲、事务协调、有效沟通等,他们也因此能够在教会内外获得更高的地位。这也通常伴随着自尊和名声的提高,以及在社会中活出信仰的新责任感。对于许多人来说,归信基督教和随后的信仰生活为人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来构建、表达个人以及社群的尊严。在一个充斥着经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世界,弱势群体同样可以为捍卫和传播自己的信仰发声。<21>
拉美福音派团体虽然在微观层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他们通常对政治领域没有直接影响力。其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往往作用在政治项目之外。大多数福音派在事工上仍然以信徒为导向,而非首先考虑社会政治现实的挑战。<22>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福音派在国家层面的参与立场不同,他们是否促进了公民社会和民主化进程尚不明确。<23> 同时,福音派对尊严的追求,有时也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即追求如天主教那般在媒体、政治及其他社会层面的特权。福音派团体常常无法超越现行的权力规则。<24>
对于中国而言,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催生出可观的中产阶级,以及根深蒂固的财富和权力阶层。在这方面,中国同样面临许多新兴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所面对的尖锐问题,例如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缺乏、对移民和边缘人群的不平等待遇等等。而许多正遭遇存在危机的中国人,在基督教里看到了救赎。
与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地区类似,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使许多人不得不自谋生路。为了替代旧有的社保体系,农村地区的人们往往期待基督教能够填补公众需求与公共卫生水平之间的落差。由于不平等加剧和人口迁徙,城市人群也在宗教市场中发现了基督教。与其他古老的宗教传统相比,基督教能够坚固那些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现代性威胁的人。通过紧密相连的信仰群体、切实的互惠互助、在信仰群体中得到的尊重,还有对公义审判的应许,那些饱受折磨和边缘化的人们往往在教会中找到医治。在一切终结之时,世界上的压迫性权力会被根除,而信者可以进天国。<25> 自明清以来,基督教所应许的尊严和盼望对贫困卑微的人而言振聋发聩。太平天国运动和耶稣家庭虽然在规模和信息上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在愈发混乱无序的世界建立一个平等的乐园。两个运动都受到基督教价值观的启发和驱动,对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尤其具有吸引力。<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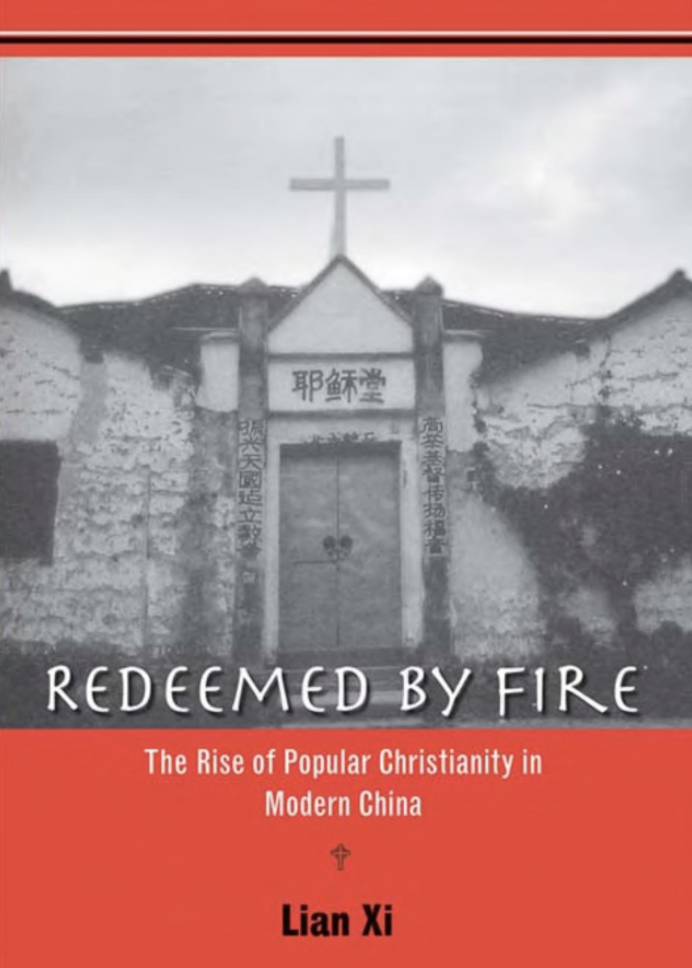
[插图3:连曦,《浴火得救: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兴起》英文版封面(2010年)]
同时,边缘化人群并不是唯一被基督教所吸引的人。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基督教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尤其在20世纪初的中国。那时,被外国支配的阴影和世纪之交的乐观进步主义交织在一起,带动了对救国的热烈追求。那些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基督徒精英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了救国,他们强烈关注“人格和技能”这一显著主题。一方面,他们呼吁基督徒更多地参与公共领域以感化社会良知。同时,除了改善人民的道德品格,他们还提供例如扫盲培训这样的实用社会训练。同余日章(1882—1936)一样,那些认同社会福音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在基督教的信息中发现了兼顾内在和外在的医治。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信仰可以通过改变基督徒的个人品格来实现民族救赎。对于公众而言,由于基督教也被认为是西方文明进程的源泉,因此中国的基督化和现代化正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的拯救同时蕴含了个人和国家两大层面。<27>
我们现在不难看到,当时这种令人迷醉的筹划,在后几十年的历史漩涡中是如何化作了虔诚的泡影。但不能否认的是,基督教赋予了不同的个人和社群以巨大的价值,回应了他们在不同层次上对医治的需要。其关于痛苦和苦难的核心信息,以及上帝不息的爱与保护的安慰,给那些在身体、经济、文化、民族上受苦的人们带来了更新的尊严和社群感。诚然,这种对人和社区的重新认知,并不能使他们免疫于神学或历史的误区。然而,当我们看到信仰群体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时,我们依旧会感叹福音转变的大能。
<1>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9.
<2>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Lian Xi,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3>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92-94.
<4> Ibid.
<5> Ibid, 95-97.
<6> Ibid, 97.
<7> Ibid, 95-97.
<8> Ibid, 98.
<9> Ibid, 98-100.
<10> Lamin Sanneh, Whose Religion is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29.
<11> Ibid, 33.
<12> Ibid, 75.
<13> Wi Jo Kang, Christ and Caesar in Modern Korea: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7), 30.
<14> Ibid, 31-32.
<15> Ibid, 66-68.
<16> Mark R. Mullins, Christianity Made in Japan: A Study of Indigenous Movemen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62.
<17> Ibid, 61.
<18> Ibid, 169.
<19> Ibid, 170-172.
<20> Dario Lopez Rodriguez, “Evangelicals and Politics in Fujimori’s Peru,” in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d. Paul Frest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5-147.
<21> Felipe Vazquez Palacios, “Democratic Activity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of Evangelicals in Mexico,” in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d. Paul Frest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6-57.
<22> Ibid., 60.
<23> C. Mathews Samson, “From War to Reconciliation,” in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d. Paul Frest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1-92.
<24> Roberto Zub, “The Evolution of Protestant Participation in Nicaraguan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Parties,” in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d. Paul Frest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7-128.
<25> Lian, Redeemed by Fire, 230-232.
<26> Ibid., 24-25, 81.
<27> Ibid., 36, 119.
图片来源:题图、插图1、插图3:Google Books; 插图2: 维基百科。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3期(2021年春季号)。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13期的主题是“基督教民族主义”,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包括上一期“基督教教育”号pdf下载),详见:
微信(世代Kosmos);网站(www.kosmoschina.org)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