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最近,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相继爆发,正在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很多来自各种不同视角及来源的消息,我们的心被这些消息与看法所牵动,不知道这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会将我们带到哪里。确实还需要时间,才能看清这个世界最终会有多么大的变化。然而要能够看清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需要有可靠的世界观,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需要对自己的世界观有所反思,以明确自己是否真正站在基督信仰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个正在变动的世界。
本文是有关世界观之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主要关注世界观的转变与形成。后续的文章会陆续关注世界观的内容(对自然世界及社会生活的看法),以及世界观的实践(日常生活多个领域中的应用)。世界观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主题,特别是在这个世界快速变动的时代。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的探索与思考,我们既难以对这个变动的世界有完整与真实的认识,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难以活出整全的福音真理。按照哲学家的看法,每个人都活在某种世界观的支配之下,就看我们是否对这种支配我们的世界观有所意识,并用基督信仰给予更新。
一 门徒之世界观的转变
让我们先从圣经新约书卷中所记载第一代门徒生命的转变,来看世界观的转变与形成。这里特别涉及到对路加神学思想的理解。在《使徒行传》1章6—8节,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向将要与他们告别的耶稣问到:“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1>初看这两节经文时我们可能会想,在基督复活后门徒还在问这个问题,难道他们所经历到的那么大的变化——耶稣的被钉与复活,对他们之前的观念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吗?
按照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曾三次向门徒预言,他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会被捕且被审判,最后会被害。<2>然而,门徒并没有听懂他话的意思。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们还在争论谁会在将来复兴的以色列国中得到更高的地位,坐在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右边或左边。<3>门徒的这种表现,表明他们还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深受1世纪犹太人中流行的弥赛亚观的影响。这种成功的弥赛亚观,即要来的君王弥赛亚要带来以色列国的大复兴,这种观念构成了当时门徒下意识具有的世界观的主要因素。
然而,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事件,彻底破灭了他们想要复兴以色列国的理想。更让门徒们陷入到深深的黑暗与绝望之中的是,他们以为的这位弥赛亚的被杀,让他们对这位拉比或夫子的相信归于无有。用今天生存论的语言来说,这让他们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直接危及到他们已有世界观的核心,即成功地战胜敌人的弥赛亚观。
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复活后的耶稣在地上停留四十天,多次向门徒们显现,主要目的就是向他们讲解圣经,证明弥赛亚一定会受害,向他们陈明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观, <4>并且再次用他爱的呼召来恢复彼得及门徒们的生命,让他们从之前的黑暗与绝望中走出来。面对复活且数次向他们显现的耶稣,多马的认信,“我的主,我的神,” <5>代表了门徒对耶稣弥赛亚身份的再次确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门徒们向耶稣问了上述的问题。
耶稣并没有否定门徒的问题,而是从正面回答了门徒的问题。首先,他要门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所期待的那国(上帝的国)的复兴马上就要来到了;其次,无论是那国的临到——圣灵的普降,还是那国的最终实现,那日子(复数)都不是他们能够知道的,只需要安心预备与等候;第三,这国将要广传,直到地极。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那国就要最终完成。
《使徒行传》随后对五旬节事件的记录表明,门徒们不仅遵守了耶稣给他们的指示,并且他们也理解了耶稣给他们的解答。彼得清楚地将圣灵在众门徒身上的临现,看作是末后的时代已经在地上开始的表征,并且宣告,这个末后时代的开始,表明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的那个国已经在这里开启了。<6>因着这样一种确信,门徒们随之就用一种新的生活样式来回应这个国的来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7>
在新约圣经的这个叙事中,我们可以讨论两个问题:其一,门徒所在的世界变化了吗?其二,门徒的世界观发生相应的变化了吗?
首先,门徒所在的世界,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变化就是末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意味着上帝的国已然来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且在持续地扩展之中。
对这个变化之更具体内容的描述来自保罗。上帝的国来到这个世界意味着打开了地上通往天上的路。之前,在《约伯记》的描述中,天上掌权的耶和华神与生活在地上的约伯之间,往来其间的是那位撒但。“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8>撒但不仅成为上帝面前对人的控告者,亦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 <9>、 “空中掌权者” <10>, 整个世界都伏在他的控制之下。<11> 可见,撒但所在的无形领域对有形领域的控制达到怎样的程度。但在基督十字架受死与复活的胜利中,保罗特别强调了基督对无形领域中诸种权势的得胜:“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12> 这里所说的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名的”,都是指在无形领域中掌权的诸种权势,它们都在基督的复活升天中被打败,从而使撒但对这个世界的权势被严重挫败,其所控制的无形领域被撕开一个口子,使上帝的国透过这个无形领域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借着基督及圣灵在教会的同在而显明出来。
如果用今天哲学性的语言来表达世界的这一变化,也即浸透于这个世界的精神(spirit)、理念或价值观念(相应于无形或属灵的)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13>这个世界不是单由可见的物质构成,同时也包含着那不可见的普遍精神、理念或价值观念领域。
其次,门徒们的世界观确实发生了变化:从之前关切以色列国变为关切以基督为主的国。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生活在上帝的国的复兴进程之中。凡物公用的生活样式,即是对这个国已然来临且在完全的进程中的一个见证。
这个世界观的转变将他们的生活指向了将来。将来这个国要扩展到地极。《使徒行传》以保罗到达罗马结束,对于作者——一个外邦基督徒的路加来说,他已经由此充分地表达了这个指向:这个国要达到地极,就要先到世界的中心。既然已经来到外邦世界的中心,那么扩展到地极的进程就完成了重要的一步。
二 哲学上看世界观转变的特点
“世界观”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康德在其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认为,人的心灵对世界(无限物)有种感知与直观的能力。<14> 按照后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解释,康德的这个概念是指“人们对世界的直观,即深刻地思考呈现于感官的那个世界。”<15> 由此,世界作为一种世界图景在人的心灵中呈现出来。
今天,如果我们简单地解释世界观这个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对实在和人生的基本解释。”<16> 或者说,“它是一套全面而自洽的信念体系,用以理解实在之本性、人性、道德及意义之最深层的要素。”<17> 希伯特(Paul G. Hiebert)在他所著的《世界观的转变》一书中,把世界观定义为:“一个群体对事物的本质给予认知、情感及评估的基本前提,并以此规范他们生活的秩序。”<18> 希伯特的这个定义,有助于我们理解五旬节后门徒世界观的转变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如果我们要用这种哲学的语言,特别是20世纪生存哲学的语言,来表述我们上节从新约圣经中看到的有关世界观转变的叙事,那么基本的思路如下:
第一,人生活于其世界之中。人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被现代哲学家们称为“周围世界” <19> 或者“生活世界”。 <20> 人是其生活世界的存在者,意思就是,他持有怎样的观念、活出什么样的形态,乃与他所在的世界密切相关。他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其所在世界流行观念(世界观)的支配,就如1世纪的门徒被当时流行的弥赛亚观所支配一样。
人的生活受所在世界的支配,具体表现就是:每个人生来就活在这个世界已经形成的观念及习俗中,其中每件事情都有确定的习以为常的做法,以及从习俗来的解释。最初,人是非反思地进入到一个现成的生活世界(世界图景)之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事物之间的关联似乎是给定的,“大家”怎样做,个人也会怎样做。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某种世界观,只是这种世界观既是“大家”(大众)的世界观,又是个人尚未反思的世界观。
第二,世界观的转变发生于人在其生活世界中遇到危机。当人和这个生活世界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人开始对自己有所怀疑,进而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所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就是世界观的转变。就是说,之前人不是没有世界观,其实是不知不觉地照着习俗给予的世界观生活。但反思让人思考这种世界观,并开始形成与习俗不同的自己的世界观。
不过难点在于,心灵对世界整体的直观,与一般意义上的感知有很大区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感知,很难达到作为无限物的世界(整体)层面。在通常情况下,认知者被流行的、大众的感知或解释所包围,这种感知或解释构成了这位认知者的未经反思的世界观,这流行世界观的厚度足以屏蔽那真实的实在。也即,这时还不存在认知者与实在之间的现成关联。在这个前提下,如何从其中突围出来,而在心灵中有对那无限世界的直观呢?在海德格尔看来,生活于这种非本真状态中的人,只有经历与死亡的相遇,才有可能从中突围出来。<21>
与死亡相遇,让人将自己从已有流行的世界(观)中分离出来,其实就是从已有的解释中分离出来。这似乎是让人第一次独自地面对这个世界。这时,对世界的直观就不是从流行的说法或经验感知层面而来,而是直接从个体自身的心灵中出来的。超越了经验层面的碎片化,而上升到对世界整体的直观。就如当年门徒经历了十架事件带给他们生命的黑暗与绝望,在复活的基督面前痛切悔改之后,似乎整个世界都变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不只是对世界的知识,在根基处是对世界的一种态度。通常情况下,虽然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常人”中,但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将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或者以自己作为世界的代表,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开始,不只是经验到自己与世界的不同,而是在惊异中经验到他者的存在。而对世界的更完整的认识,源于认知者在油然而生的敬畏中产生一个转向:这世界是比自己更基本的实在。
第三,世界观的转变,会涉及到人关于世界与人生的深层信念与图景。这就意味着,人们无法直接将这种世界观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对其给予命题式的概括。其实在康德那里,就已经说明,如果我们是基于经验的认识,对世界的命题式描述必然会出现二律背反。<22> 毕竟,我们是切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并且,这个世界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世界观的描述,很难用所谓客观的、命题式的方式进行,而只能用一种故事的叙事方式对其加以描述。在这种描述中,会出现比喻或象征的形式。
英国文学家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1973)对鲁益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的影响正在于此,即帮助鲁益斯认识到,神话叙事并非是人心灵虚假的想象,而是对重要真理的象征性描述,因为这种真理很难用字面意义或命题方式来表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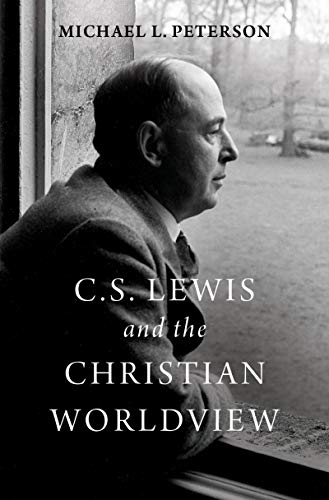
英国思想家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曾有过类似的描述,即用某种神话的或故事的方式,才有可能描述与我们生存切身相关的世界。<24> 这种故事的叙事方式具有不可约化为简单命题的特点。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一种世界观,通常是借着少年时读过的童话,以及成年后听到的故事而了解到的。而基督徒乃是借着圣经中大量的历史叙事了解圣经所展现的世界。这些历史的叙事所包含的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每一代释经家都只能诠释出其中的某些侧面。
第四,世界观的转变涉及到人们话语体系的转变。围绕着世界观之深层信念所形成的故事性叙事,通过一些象征符号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从而形成了一个时代的话语体系。<25> 虽然世界观的叙事很难约化为一些命题,但这种叙事往往可以被约化为一些核心概念或符号体系,其中一些核心观念或符号已经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领域中产生共鸣,形成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也就是说,世界观的话语体系渗透到生活世界中的多个阶层及领域。由这些基本观念为纲目,形成了生活世界中一般人的话语体系与含义,就如今天我们还会下意识说“解放前”与“解放后”一样。
这里涉及到的认识论因素,是我们作为现代人不能不面对的维度:对于自然、世界或实在的任何认识与述说,都是借助某种符号体系进行的,如数学公式或文学叙事。问题是,人们习惯将文字描述与现实世界看作两种存在形式。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种存在的两个面向。当我们说到世界的时候,它既指我们用符号表述的那个世界景观,同时又指现实的世界。面对这两个面向的张力,一个极端是,直接越过符号体系,以为自己说的就是自然或世界本身。另一个极端是,干脆就停留在符号体系层面,认为所说的不过是符号体系本身要表现的,而不是其所指向的。上节中我们已经看到,门徒们对他们世界观的描述与他们所在的世界的变化是一致的。
第五,世界观的转变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世界观作为信念体系与话语体系,形塑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生活方式,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下意识地对一种事物给予反应的基本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被社会普遍遵行的生活方式,就成为文化中的社会习俗。
三 基督教世界观在现代的可能性
当我们用启蒙运动之后产生的世界观概念,来描述新约圣经中门徒之世界观的转变时,我们已经预设了基督教世界观的存在,也即,现代所产生的世界观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圣经带给我们的基督信仰。不过,《世界观的历史》这本书的作者诺格尔(David K.Naugle)也提出警告,当我们思想基督教世界观在当代的可能性时,基督教群体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重要问题:“首先,随着历史的发展,‘世界观’有了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含义,基督徒了解这种情况吗?其次,由于这些新的含义的出现,世界观概念已不再能服务于基督徒了,是这样吗?不一定。”<26> 虽然诺格尔给出的答案还是肯定的,但他所提出的问题仍然需要考察。
在启蒙运动时期产生的世界观概念,在将其看作是人对世界的直观及基本看法时,同时也将人看作是其所在世界的主体。在人心灵中所构建的世界图景面前,人似乎成了主人。这使得世界观概念天然地具有一种现代人文主义的色彩。不过回到这个观念产生的背景,对于如康德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来说,人在心灵中能够立于世界之外而对其整体有所直观或感受,唯一的立脚点就是人所具有的普遍与先验的理性。如果拿去这个前设,人凭什么认为自己对无限的世界整体拥有直观能力呢?但后来的人们在放弃普遍与先验理性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世界观这个概念,就使其具有相对主义的色彩。在世界之中的有限的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对世界形成的看法,一定带有自我中心的限制,从而形成从各自不同视角出来的不同世界观。
其实,回到世界观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来看,不是基督信仰在搬用一个与基督教无关的概念,而是应该颠倒过来,这个概念的产生,其实是在一种基督教普世观念的背景之下。也就是说,在启蒙运动时期,这种普世观念(主要以普遍理性的形态表现出来)无疑是以基督教有神论为其背景才有可能。因此,描述一种基督教世界观,只需要重新回到世界观产生的源头,就可以看到关键所在。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大致概括基督教世界观得以可能的三个基本前提。
1 作为世界创造者的上帝的自我启示
立于世界之外依然存在的,可以称之为终极实在。因为其存在不是以这世界为前提,而是以其自身为前提。显然,人不是这样的存在者。如果我们要承认有一种普世的世界观存在,那么我们就要承认有一种立于世界之外的终极实在存在,使人们有可能依于其中而对这个世界有种直观。并且其次,既然这位实在(者)是我们认识世界及其自己的前提,那么这位实在就不是我们能够认识的对象。我们得以认识这位实在只有通过启示。这就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出发点:圣经对这位创造者上帝的启示,是基督教世界观内涵与形成的源头。
就如复活后的耶稣亲自向门徒讲解圣经,启示出受苦的弥赛亚观,从而使门徒的世界观有可能改变一样,除非借着圣经对所启示的三一上帝有所认识,否则人不可能对无限的世界整体有所直观。

借用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的表达,认识人自己与认识上帝关联在一起;同样,认识这个世界就与认识上帝关联在一起。只有借着这位超越的上帝以及他带来的启示,人才得以站在这个世界之外对世界整体有所直观。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世界观乃是站在上帝(启示)的地位上对这个世界形成的看法。
既然基督教世界观的内涵及形成,均与对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的认识相关,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一下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有些什么特征。首先,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有位格的上帝。他的位格生命使他既超越于这个世界之外,同时又内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他的位格生命虽然有自己的性情,却可以和他用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相通。他认得他子民的声音,而属他的子民也能够认得他的声音。他位格生命中具有的慈爱、公义与良善,成为基督教世界观之内涵的标准。其次,这位上帝是一位创造者,他出于爱,在其自由意志的选择中,从无创造了这个由天与地共同构成的世界。在创造的过程中,他借着道赐给万物以法则;同时他也借着灵赐予万物生命的气息。第三,他也是一位愿意为人承受苦难的上帝,作为上帝之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被人的罪所充满的世界,降卑成为人,甘心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且三天后复活。总之,对圣经所启示的具有这些特征的上帝的认识,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基本前提。
2 人里面的光照对教会传统的更新
基督教世界观的第二个基本前提是:人因着被基督救赎,里面有重生的生命,恢复人被造时所具有的上帝形象,从而有可能被圣灵光照,得着可以对世界整体有所直观的能力。就如当年在五旬节事件中,门徒被圣灵光照,彼得直接就认出末后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观确实是基督徒对世界的一种直观感受。不过,这种直观感受发展为一种世界观,还需要经过教会这个群体的共识与实践。
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一开始可能是某些人对世界的崭新看法,就如当年宗教改革家们对其所在世界的崭新看法,经过理论的诠释与出版,不仅形成思想体系,同时落实到实践中,被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接受,成为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基督教世界观。无疑,在这个过程中,教会群体是基督教世界观孕育、发展、保存及传播的地方。通过这个群体,基督教世界观不仅影响到身在教会中的每个人,同时也借着这些人,影响到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在历史的长河中,基督教世界观真正有生命力的载体不是个人,而是教会这个群体。只有借着教会这个群体,它才会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种理论体系。
当我们把基督教世界观与教会这个群体关联起来,将其看作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对他们所在世界的看法的时候,基督教世界观的时代性就呈现出来。如果说,圣经对上帝启示的记录与表述是超越时代的,那么,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处境中的教会群体,因带着这个时代的印记,对圣经的诠释及实践方式则可能会有不同。这个印记是在这个时代的教会所传递的世界观中表现出来。确实,基督教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就如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一样,在不同时代都是一样的。但对这种核心内容的表达方式,特别是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方式,则可能会有区别。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使命,即回到起初,回到使徒时代,回到基督信仰的源头,用现代这个时代有生命力的语言,重新表述这个信仰的核心,将这个信仰的精神在当下的处境中,用一种有生命力的生活再次见证出来。这也正是当年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如果基督教世界观具有这种时代性,那么与基督教世界观相关联的认识论,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批判的实在论。按照这种批判的实在论,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那位上帝及其所造的世界,确实是客观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实在,只是因着圣经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才有可能认识这位上帝,并因此对这个世界有某种整体的认识。这是“实在论”的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即批判的层面则意味着,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这种启示的诠释以及所形成的相应实践方式,则可能会因为处境的变化而会有变化。N.T.赖特这样描述批判实在论:“这是一种描述‘认识’过程的方法论,认同被知事物是存在的实体,且在知觉者本身之外(所以称作实在论),并在同时完全认知到:若要通往这实体,惟一的方式只有透过某种螺旋而上的通道,意即知觉者与被知事物之间的全宜对谈或谈话(因此称为批判性)。这条通路让我们以批判的态度,反思我们探索‘实体’时所产生的想法,以致当我们提出关于‘实体’的陈述时,也承认自己的有限。”<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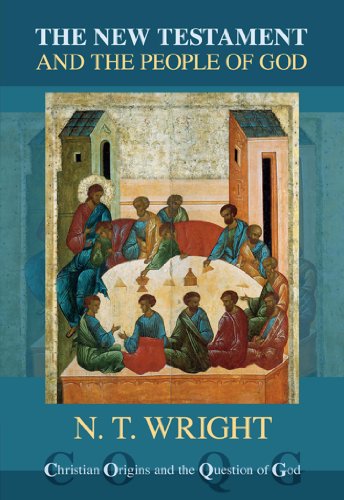
虽然圣经上所记载的上帝的命令对每个时代都是不变的,但是生活在地心说时代的人们,或者生活在中世纪社会结构中的人们,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与今天的人们还是会有某种不同。这并不是说,每个时代的基督教世界观是相对的,具有不可比较的特点,而是说,在迎接终末来临的过程中,我们都力求对实在更加接近,对实在的认识更接近真实。当然,我们要达到对这位实在者的完全认识,需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
3 普遍恩典的普世适用性
基督教世界观的第三个基本前提是,由于上帝对所有人之普世恩典的存在,基督教世界观所涵盖的内容可以适用于教会内外不同的人群,以及人们生活世界的每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世界观是对普世真理的一种表达。
基督教世界观虽然是源自上帝的启示、以及教会的诠释与实践,但当它形成一种世界观体系的时候,它则适用于教会以外的其他群体。这是由上帝作为创造这个世界的终极实在者的身份与权能所决定的。正如福音书中所说,上帝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28> 这里涉及的上帝的普遍恩典是指,上帝在他的创造与护理中赐给每个人的祝福,虽然无关于人的救赎,但却关系到人的基本生存、社会秩序、普遍价值、文化素养等多个方面。<29> 而这些方面都可以是基督教世界观体系的构成部分。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在其《伦理学》一书中,专门用一章谈到基督信仰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揭示了历史上展现出来的这样一种逻辑关系:首先,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追求的那些普世价值,诸如理性、公义、宽容、自由、仁爱与民主等,这些观念最初都是基督徒群体为着信仰的缘故,在持续付出代价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然后才在社会中逐渐成为普世流行的观念。不过,当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导观念之后,却被人们转过来用以反对教会之权威,以为这些观念可以立于人们为它们所构想出来的根基上。不料,当这样做了以后,人们很快就发现,在信仰基督教的群体被逼入困境、教会的权威被消解之时,他们自己连同这些普世价值观念也都无家可归,失去自身站立的根基或基本含义。结果是,教会在任何艰难环境下始终都可以站立,倒是这些普世价值观念处在岌岌可危、极需要寻找保护的地位。<30> 这个描述正适合今天世界各地思想界的状况。今天正是这些观念四处寻求保护的时期。

四 基督教世界观与社会苦难
从新约圣经角度,说这个时代是上帝的国已然来临的时代,和说现在是末后的时代,二者是同一个意思。从末后时代的角度看,福音书认为这是一个各种灾难与不法之事日渐增多的时代。<31> 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身处这些灾难与不法的事情之中而无处逃避。从根源上讲,这些灾难与不法的事情都源自人自身的罪性,是罪在现今这个时代日益明显、无所约束而带来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人的罪借着日益向前推进的国家主义与技术主义,而生发出更大范围之伤害的结果。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罪带来的后果:破坏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让人生活于虚假之中。病毒先把人与人隔离开来,让人们处在彼此孤立无助、无法信任的状况。然后,一方面把人驱赶到由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中去,让人们在这个虚拟世界所构造出来的、自己为主的自由王国中得以发泄;一方面让人在现实生活中放弃自己的责任,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的管制以及技术的突破上,以至于难以看到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恶性循环:由国家主义及技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又不能不寄希望于国家主义与技术主义去解决。
在这世上的人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基督不会喜悦他的门徒只做一个旁观者。他自己就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愿意放下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被罪恶充满的世界,甘愿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为这个世上有罪的人们承担罪的刑罚。在今天疫情泛滥的时候,基督徒参与这世上苦难的最好方式,就是与这个世上哀伤的人一同哀伤,去经历他们所经历的,并且在这个一同经历的过程中,看到我们所信奉的那位上帝,并不只是坐在高天之上施行惩罚的审判者,更是亲自来到人间与人们一同承担这世上苦难的受难者。他在那些因着病重而呻吟的人们当中,也在那些因为失去家人而痛哭的人们当中。
在这末后的时代,当整个人类社会处在不义的苦难之中的时候,人类的那些普遍价值同样受到威胁。其实在此之前,这些普遍价值观念无论是在左派还是右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诠释中,都已经失去其基本含义,因而在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更显得苍白无力,让一盘散沙的个人无奈地听任国家主义与技术主义对自身的控制。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好消息是,我们生活在上帝的国已然临到的时代。在今天,上帝的国已然临在现今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持守基督信仰并有生命见证的教会,除了向人们传递拯救的福音,同时也成为在苦难中无处逃避的人们及其所追求之普世价值的可以栖身的避难所。这些普世价值,诸如理性、公义、宽容、自由、仁爱与民主等,只有在基督信仰的根基上才有可能恢复其原本的含义,并因此在人的心灵及现实生活中产生出应有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普世价值观念是上帝的国在今天借着教会给这个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普遍恩典。
按照朋霍费尔,那些在苦难中愿意为他人承担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实践出这些普世价值的人,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中。如果他们还不是基督徒,那么这种生活让他们更容易与基督相认同;如果他们已经是基督徒,这种生活会让他们更容易明白自己是属于基督的人。<32> 他在解释耶稣所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时强调:“不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遭迫害,而是为了一件正义的——我们可以补充说:一件真正善的、合乎人文的——事而受迫害的人受祝福(比较《圣经·彼得前书》3:14,2:20)。”<33> 也就是说,为义受苦,或许在深层来看是为基督的名、为了人自己的信仰而受苦,但在具体社会处境中,则可能是为了社会公义、为了他人而受苦。
总之,在这个末后的同时也是上帝的国已然来临的时候,向基督教世界观的转变越发显出其重要性。因为基督教世界观可以让人们更完整和真实地看清这个世界的实况,并且找到既不同于左派又不同于右派的、既可以实践自己信仰又能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道路。
<1> 《圣经·使徒行传》1:6—8。注意英文圣经新国际版(NIV)第7节经文It is not for you to know the times or dates the Father has set by his own authority,其中times or dates使用了复数形式。(本文正文所引圣经经文出自中文和合本圣经,下同)
<2>《圣经·马可福音》8:31,9:31,10:33—34。
<3>《圣经·马可福音》10:37、41。
<4>《圣经·路加福音》24:26—27、45—46。
<5>《圣经·约翰福音》20:28。
<6>《圣经·使徒行传》2:36。
<7>《圣经·使徒行传》2:42。
<8>《圣经·约伯记》1:7。
<9>《圣经·约翰福音》出现三次“世界的王”,见《约翰福音》12:31,14:30,16:11。
<10>《圣经·以弗所书》2:2。
<11>《圣经·约翰一书》5:19。
<12>《圣经·以弗所书》1:20-22。
<13>这里的“精神”与“理念”粗略地对应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并非指现代人通常理解的人主观的精神或观念。
<14>转引自大卫·K·诺格尔,《世界观的历史》,胡自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65页。
<15>诺格尔,《世界观的历史》,第65页。
<16>诺格尔,《世界观的历史》,第289页。
<17> Michael L. Peterson, C. S. Lewis and the Christian Worldvie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4.
<18> Paul G. Hiebert, Transforming Worldviews: An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How People Change(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8), 15.
<19>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78页。
<20>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86页。
<21>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等译,第305页。
<2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62页。
<23> Michael. L. Peterson, C. S. Lewis and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29.
<24>切斯特顿,《回到正统》,庄柔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49—65页。
<25> N.T.赖特,《新约与神的子民》,左心泰译,台北:校园书房,2013年,第287—297页。
<26>诺格尔,《世界观的历史》,第287页。
<27> N. T. 赖特,《新约与神的子民》,第55页。
<28>《圣经·马太福音》5:45。
<29>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3,3。中译本见钱曜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68—269页。
<30>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7页。
<31>《圣经·马太福音》24:8—12。
<32>朋霍费尔,《伦理学》,第52页。
<33>朋霍费尔,《伦理学》,第51页。
题图:
《耶稣升天》(Jesus’s ascension to Heaven)(1775年);
作者:
约翰·辛格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1738—1815),美国画家;
原作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MA, USA.)
《世代》用图版本来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cension_of_Jesus#/media/File:Jesus_ascending_to_heaven.jpg
插图1:
迈克尔·L·彼得森,《鲁益斯与基督教世界观》英文版封面
(Michael L.Peterson,C.S.Lewis and the Christian Worldvie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此图来自https://www.amazon.co.jp/Lewis-Christian-Worldview-Philosophical-Theological-ebook/dp/B0844XKKS7
插图2:
《去往以马忤斯》(Gang nach Emmaus)(1877年)
作者:罗伯特·赞德(Robert Zünd,1826—1909),瑞士风景画家;
原作藏于瑞士圣加伦艺术博物馆(St.Gallen museum of art)
《世代》用图版本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Z%C3%BCnd_Gang_nach_Emmaus_1877.jpg
插图3:
N.T.赖特,《新约与神的子民》英文版封面
(N.T.Wright,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92])
插图4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1939年)
摄影者未知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0期(2020年春季号)。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10期主题是“基督教世界观”,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世代Kosmos);网站(www.kosmoschina.org)。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