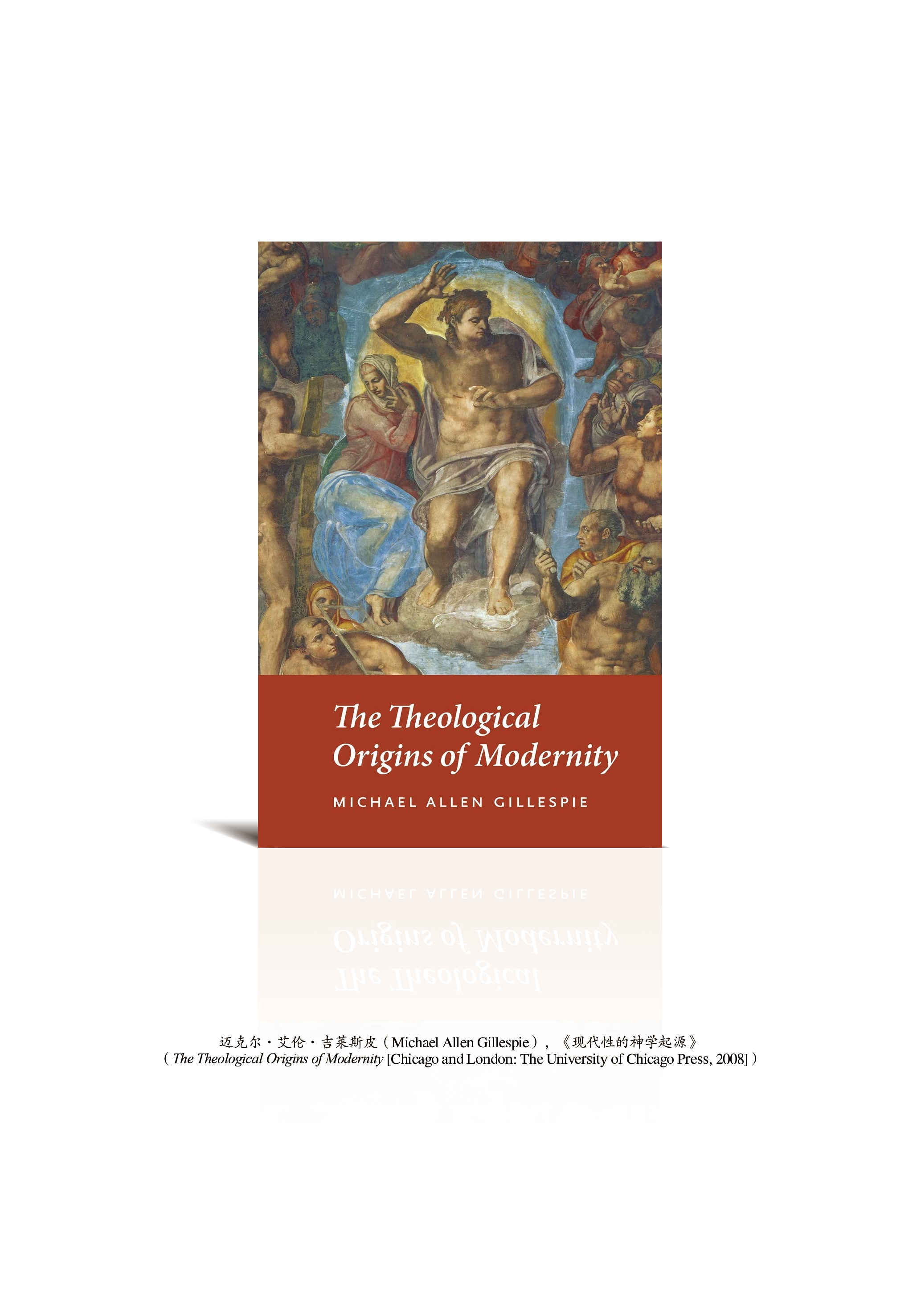
[题图: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英文版封面。此图为《世代》2020年夏季号总第11期封三图片;美术编辑:陆军]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对世俗化的定义影响深远,认为其指的是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或理性化,这一过程不仅导致社会组织尤其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理性化,也深刻影响人的心性结构或心态。具体言之,世俗化进程不但使得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也导致宗教本身不得不适应世俗价值,或者退回到私人领域,甚至是个人内在宗教性的丧失。<1>
类似的观点被加拿大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讽刺为“世俗化主流权威论述的霸权” <2>,早已受到西方学术界广泛的质疑和挑战。批评者认为,即便在现代西方,宗教信仰并未因科学和民主的进展被边缘化,反而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世俗也并非与宗教截然对立的概念,而是与自由、人权、民主化、现代性、终极关怀等议题密切相关。美国学者吉莱斯皮(Michael Allen Gillespie)的《现代性的神学起源》(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2008)一书,可以归诸这一类批评的行列,试图证明上述对世俗化的理解是一种被夸大的神话(myth),因为“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实际发生的并不是神的简单消除或消失,而是将他的属性、本质力量和能力转移到其他东西或存在领域中。因此,所谓的祛魅过程也是一个返魅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并通过它,人和自然都被赋予了以前被归于神的若干属性或能力”。(第355—356页)<3>
本书从反思9·11事件开始,认为这一恐怖袭击是对西方现代性所提供的平等、自由、繁荣、宽容、多元化、代议制政体等等的质疑与攻击,并以粗暴的方式迫使人们反思现代精神和现代世界的源头。通过考察现代性的起源,吉莱斯皮试图阐明宗教和神学在现代性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那种认为现代性就起源和核心而言是无神论的、反宗教的甚至是不可知论的观念,是错误的。现代性从一开始不是要消灭宗教,而是试图发展一种关于宗教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之新看法,更准确说,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种努力,试图为神、人和自然的本性和关系问题找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答案。(第4页)
按照作者的说法,该问题源于中世纪晚期基督教内部关于神的存在本性之形而上学/神学危机,这一危机最明显地表现在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名论革命。(第22页)经院哲学在存在论上主张实在论,相信共相是真实的,世界是神的理性范畴的例示,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和神的形象,处于受造的顶峰,受自然目的和神启的超自然目标所指引。与此相反,唯名论在存在论上主张所有真实存在的事物都是个体的或特殊的,共相只是虚构,受造物完全是特殊的,没有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目的。神无法被人的理性所理解,只能通过圣经启示或神秘体验来理解。这一观点强调神的大能、不可预测,以及对善恶漠不关心。于是,人失去了在自然秩序中的尊贵地位,被抛入一个无限宇宙漫无目的地漂泊,没有得救的道路。此外,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期间爆发的黑死病、罗马教会大分裂和百年战争,使得人们产生各种焦虑和不安,也就更容易相信唯名论的世界观。(第22—23页)这就是中世纪晚期思想的神学危机。
现代性的产生就是源于摆脱由唯名论革命所引发危机的努力,尝试在特定的形而上学基础上构建世界观。也即,唯名论力主存在论(ontological)层次上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为后经院哲学时代的思想形态提供有关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的思想框架。
是故,14—17世纪之间最根本的思想分歧不是存在论层次的,而是存在者(ontic)层次上的,不是关于存在的本性,而是关于人、神、自然这三个存在领域中哪一个具有优先性。在唯名论与现代世界之间,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虽接受唯名论所宣称的存在论层次的个体主义,但对于究竟是人还是神具有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则存在根本分歧。人文主义者将人放在第一位,在此基础上解释神和自然,这以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第二章)、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第三章)为代表,而改教家从神出发看待人与自然,这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第四章)为代表。故此,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与改教家(马丁·路德)产生激烈冲突(第五章)。吉莱斯皮将这些冲突与帕拉纠主义(Pelagianism)关联起来,后者被正统基督教判为异端,主张人并未被原罪完全败坏,因此在没有上帝扶助的情况下,也能过道德生活,成为道德主体,故此,人们要为其自身的得救与否负主要责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并非拯救的基础。许多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受帕拉纠主义影响,在得救议题上倾向强调人的自由和道德责任。与之相反,改教家的神学强调神的大能和人的顺服。
现代性试图解决这一冲突的结果,其断言,不是神也非人,而是自然具有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第24—25页)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等思想家不再把人或神,而是把自然置于优先地位,不把世界理解成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的自由产物,或者一个彻底全能的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理解成物质的机械运动的产物。(第六、七章)不过,虽然现代形而上学开始于从人和神转向自然,但却是通过用自然主义的方式重新解释人和神才做到这一点。它将早期神与人的冲突,重新转变为自然的必然性与人的自由之间的矛盾。(第八章,第341—342页)也就是说,现代性既未克服也未解决神与人之间的早期争论,而是在形而上学范畴之内隐藏了这一争论。
作者证明,对宗教和神学的表面拒斥,其实掩盖了神学议题一直与现代性关联在一起。认为世俗化或祛魅过程等同于现代性的说法并非事实。上帝并非死了,也从无退隐,上帝的属性逐渐转移到人(一种无限之人的意志)、自然界(普遍的机械因果性)、社会力量(公意、“看不见的手”)和历史(进步的观念、辩证的发展、理性的狡计)之上。(第354页)
问题是,把上帝的属性归给人,就会倾向把人神化,赋予人某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改变世界的角色,这是人文主义者曾经期待的;把神的属性归给自然,则人沦落为提线木偶、自然欲望的结合体。在此意义上,启蒙运动其实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把人看作神,一条是看作兽。以隐藏的神学(concealed theology)角度来解读西方知识史和政治史,可以矫正长期以来人们以世俗化理论对西方经典的误读,这种误读未能理解西方思想深刻的神学根源。
如果把西方近代历史看作“由圣入凡”的世俗化历史,且这种世俗化历史借着殖民扩张表现为一种“普遍历史”,那么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仅是自身传统与现代的古今问题,还包括中西之间的冲突问题。对于百多年前的中国士人而言,现代性问题无异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随着近代以来儒家理念和帝制王权的衰落解纽,20世纪的中国以追求西方科学、民主的名义推进现代化,“由圣入凡”,结果却以革命的名义组建“主义”政党,构建民族国家,“由凡入圣”。借助吉莱斯皮对现代性神学起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主义”宗教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现象,且并非中国所独有。<4>
通过回溯西方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吉莱斯皮努力让他的西方同胞不要盲目自大,而是要借助历史认识自己,理解过去如何塑造现今的西方文明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差异。也即,历史感可以让现代人懂得珍视现代文明诸如自由、权利、科技等成果,同时明晓现代社会的不完全乃至危险之处,从而在审视全球化和现代性时保持警惕和谦卑。这启发我们在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特别是世俗化议题时,不可忽视自身历史的维度及具体的文化处境。
<1>孙尚扬,《宗教社会学》(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5、169页。
<2>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34.
<3>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355—356页。(下文引文页码直接以夹注方式在正文中标出。)
<4>有关现代中国的“主义”宗教,可参考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82—487页。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1期(2020年夏季号)。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11期主题是“基督教与现代性”,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世代Kosmos);网站(www.kosmoschina.org)。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