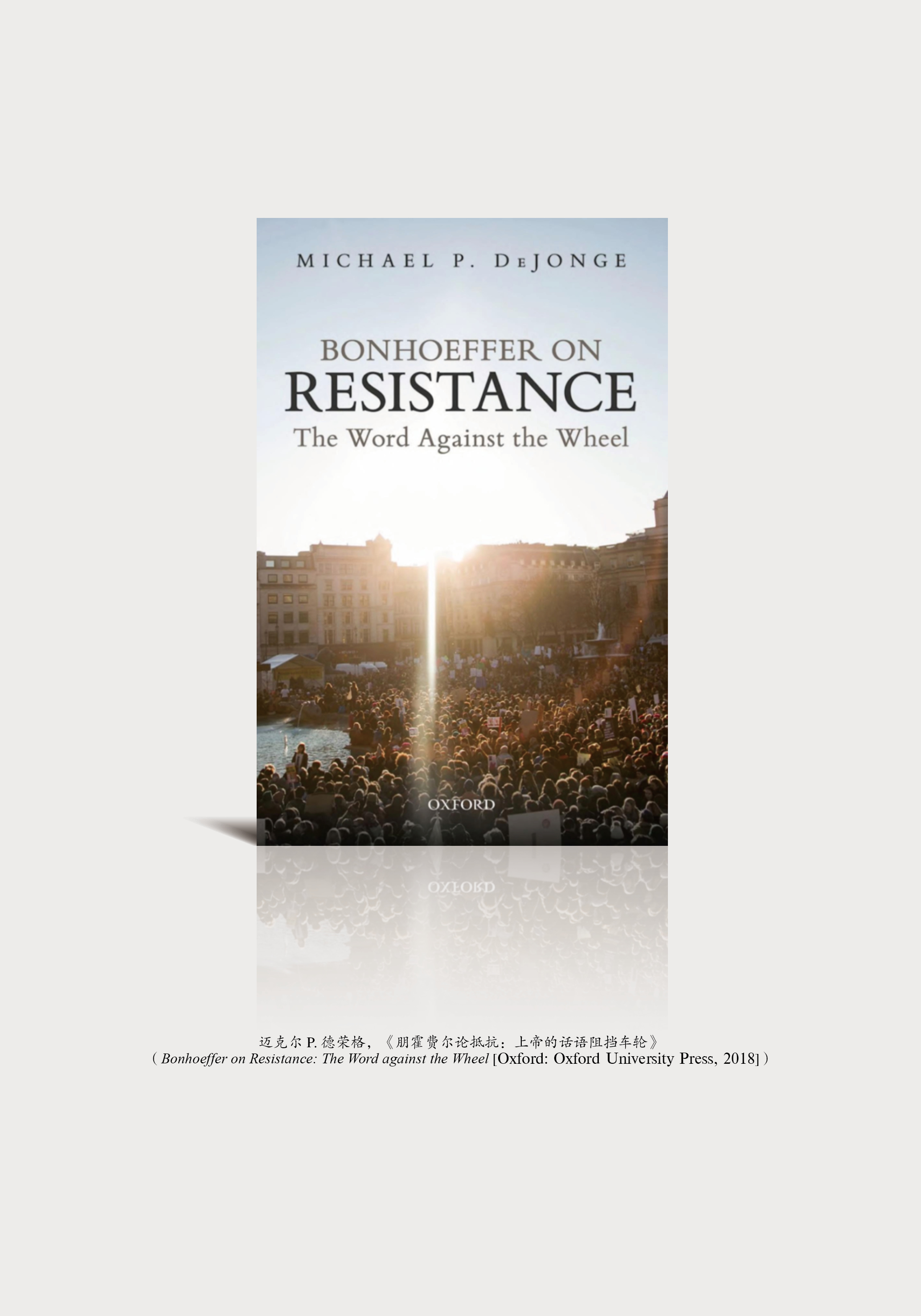
[题图:迈克尔·P.德荣格,《朋霍费尔论抵抗:上帝的话语阻挡车轮》英文版封面。此图为《世代》2021年夏季号总第14期封三图片;美术编辑:陆军]
朋霍费尔生前的学生和密友埃伯哈德·贝特格(Eberhard Bethge,1909—2000)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一次谈话:有一次,一名同样被关进特格尔(Tegel)监狱的意大利囚犯趁放风期间问朋霍费尔,你既然是基督徒和牧师,怎能参与这场政治密谋呢?因为放风时间有限,朋霍费尔简短回复说:“当一个疯子驾车冲向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 译按:指柏林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大街,简称为Kudamm)的人行道时,如果我当时在那里,作为牧师,我不能仅仅埋葬死者,安慰死者家属,而是必须跳进去把司机从方向盘上拉下来。”贝特格补充说,朋霍费尔这一想法很早就出现在一篇题为“教会与犹太人问题”(Die Kirche vor der Judenfrage)的文章中:“(教会采取的)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为车轮下的受害者包扎伤口,而且要落入车轮本身的辐条中(dem Rad selbst in die Speichen zu fallen)。”<1>
贝特格提到的这位意大利囚犯名叫加埃塔诺·拉特米拉尔(Gaetano Latmiral,1909—1995)。他原本是意大利一名工程师,到柏林替德军安装军事设备,后因意大利投降盟军而沦为战俘,被关进特格尔监狱,从而有机会和身陷囹圄的朋霍费尔长时间相处。多亏这位工程师的回忆和记录,朋霍费尔的家人,当然也包括今天的我们,才有机会多少了解朋霍费尔在这段被囚时期的生活情形和思想心境,特别是他把参与政治密谋看作身为牧师所履行的责任之一。在他看来,牧师并非仅仅只要安慰那些沦为国家不义之下的受害者就可以问心无愧了。<2>
贝特格对这次谈话的记载大体是真实的,仅仅是在文字表达上与拉特米拉尔最初的表述略有不同,<3> 但其解读,也就是将朋氏的回答与他在1933年4月写下的“教会与犹太人问题”一文关联起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从纳粹上台之初,朋霍费尔就有了参与政治斗争,从事反抗极权统治活动的想法。这种解读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1)混淆了不同的抵抗主体;2)忽略了朋霍费尔抵抗思想的多层次、分阶段的内涵;<4>从而有可能倾向于3)将朋霍费尔塑造成刻板的反抗纳粹的英雄志士形象。
首先,朋霍费尔在“教会与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提到的第三种可能的抵抗方式,也就是“抓住车轮”(seize the wheel itself)<5>使其停下,主语或者说抵抗的主体是教会而非个人。贝特格在引文中以括号注明主语是教会(der Kirche),但似乎并未澄清其中表达的含义。
在朋霍费尔对抵抗的早期思考乃至整体思考中,教会始终是抵抗国家(state)不公义最重要的主体,原因是在朋氏看来,教会对上帝话语的宣讲和祷告是最根本的行动,是最有力的政治抵抗形式。这里涉及他对上帝话语和教会本质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面对国家的不义,教会可以通过福音的宣讲,以及帮助国家不义行为之下的受害者(即便这些受害者不信主),来间接表达反对立场,只有当国家的行为危及教会自身的存在本质和福音宣讲——按照路德宗传统的两国论教义——同时也危及国家自身的本质和存在时,教会就不能仅仅替车轮下的受害者包扎伤口,而要抓住车轮使其停下。在这样的时刻,教会将发现自己处于认信状态(statu confessionis),与国家处于矛盾对立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此时教会采取的政治行动(主要是借着话语的宣讲和祷告这两种方式),不是由个别地方教会(遑论个人),而是由某个普世合一教会的“福音派会议”(evangelical council)决定,而且其最终目标不是推翻国家,而是帮助国家重新回复到上帝所赋予的秩序地位。<6> 因此,将朋霍费尔后期参与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计划,追溯到这里所说的第三种可能的抵抗方式,显然混淆了抵抗的主体。
确实,大概从1939年开始,朋霍费尔就加入了刺杀希特勒的地下抵抗组织,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用萨宾娜·德拉姆(Sabine Dramm)的话来说,这一决定“必须被看作他整个人生复杂的内在和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处境、经验、条件和态度的整体结构的一部分”。<7> 也就是说,朋霍费尔参与政治密谋并不是早期思想自然的结果,而是随着时间、情势和自身境遇变化的产物。很有可能,他在写作《教会与犹太人问题》一文时,头脑中根本不会想到自己最终会走上暴力反抗之路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
对应朋霍费尔在“国家与教会”(state and church)一文中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朋霍费尔就个体抵抗政权(government)的思考分为不同层次。第一种情形,政权使命(task)的范围和内容成问题,导致个体对此产生怀疑,然而此时个体仍要服从;第二情形,政权在某方面逾越自身的使命,比如使自己成为会众信仰的主人,那么为了良知和主的缘故,个体应当拒绝服从。但是,这种不服从只能是在个别情况下的具体决断,而不能普遍化推论说该政权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不再有资格要求人服从。“即使是一个反基督的政权,在特定的方面它也还是政权。拒绝向迫害教会的政权交纳国税是不允许的。”第三种情形,《启示录》意义上的敌基督的政权。由于任何个别的服从行为都同否定基督相结合(启13:7),其后果必然是全面的不服从。此时对政权的拒绝服从,是“对自身的责任的一次冒险”,或者说是个体面对耶稣基督的呼唤时,基于自由责任做出的回应。<8>
由此可见,对政权全面的不服从(暗指朋霍费尔加入地下抵抗组织),只是在极端情况下个体不得不做出的回应。准确说是在极端情况下,负责任的个体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呼召(vocation)的回应。这样的生命从基督的视角看来是人的呼召,从人自身的视角看来则是个体的责任。<9> 正因为呼召即责任,而责任“是完整的人对实在整体的一次完整的回答”,所以不应该把自己限制在最狭窄的呼召义务上,使自己被束缚在所谓个人的职责、义务等“确定的活动领域”(a definite field of activity)。个体的呼召所要回应的不是这些所谓的“确定的活动领域”自身的价值,而是始终要面向对耶稣基督所负的责任。因此,呼召就可能会突破个体的活动领域,保持对福音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负责任的行为认识到并且承认突破律法的客观的罪,但突破律法的结果则导致对律法的真正尊崇。<10>
朋霍费尔批评德国教会斗争期间,许多神职人员秉持狭隘的呼召观,只要自己的教区没有遇到困难和攻击,就拒绝对其他基督徒和各类受迫害者公开表态,伸出援手,承担公众责任。<11> 这样的人或许自以为尽职了,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绝不会冒险作出要自己负责的勇敢举动,最终“不得不对魔鬼也一视同仁”。在朋霍费尔看来,习惯于服从职责和权威的德国人,忘记了自我牺牲和服从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因为他们不理解呼召和自由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自由而负责的行动也许必须高于职责和号召。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那些以勇敢的行为自由回应上帝呼召的人,“对于在此过程中成了罪人的人”,上帝允诺给予宽恕和安慰。<12>
当朋霍费尔以自由负责任的行为回应上帝的呼召,试图将疯子从方向盘上拉下时,我们要知道朋霍费尔对此并无成功把握。他的脚下几乎没有根基,<13>所能抓住的唯有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并愿意为此献上自己的整个生命。即便如此,他也意识到在履行自己领受的责任时,也有可能失败。<14> 回顾纳粹上台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朋霍费尔甚至承认自己也是那些种种罪恶行径沉默见证人中的一员。面对周遭的处境和不确定的未来,连他也发出疑问:我们仍然有用吗?<15> 这不是一个坚定、满怀希望、相信善良终将胜过罪恶的人发出的声音,更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会说出来的话,但它反映出朋霍费尔开始理解了面对这个世界的力量,无力和软弱真正意味着什么。面对未来,最重要的不是确保他们仍然被当作英雄尊荣,而是以某种方式服侍将来的世代,对上帝的呼召负责。<16>
<1> 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Person und Werk,” Evangelische Theologie, vol.15, January 1955, 152.
<2> Ferdinand Schlingensiepen,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Martyr, Thinker, Man of Resistance, translated by Isabel Best (London & New York: T & T Clark, 2010), 344; 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A Biography, Revised Edition, revised and edited by Victoria J. Barnett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0), 851.
<3>拉特米拉尔在1946年6月3日致信朋霍费尔的妹夫格哈德·莱布霍尔茨(Gerhard Leibholz,1901—1982),提到他与朋霍费尔的这次谈话。Gartano Latmiral, “Letter to Professor Gerhard Leibholz , June 3, 1946.” Dietrich Bonhoeffer Yearbook/ Jahrbuch 1: 30,转引自Michael P. DeJonge, Bonhoeffer on Resistance: The Word against the Whe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第144页。贝特格的记载可能据此而来。
<4>对朋霍费尔抵抗思想的梳理和研究,参见Michael P. DeJonge, Bonhoeffer on Resistance: The Word against the Whe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这本英文研究专著的封面也是《世代》本期封三图片。
<5> Dietrich Bonhoeffer Berlin 1932-1933, English edition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DBWE]vol. 12) edited by Larry L. Rasmussen, translated by Isabel Best and David Higgin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 365.
<6> DBWE, vol. 12, 366-367.
<7> Sabine Dramm,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the Resistance, translated by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 6.
<8>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3、234页。
<9> DBWE vol. 6, 290.
<10>同上,第292、297页;朋霍费尔,《伦理学》,第237页。
<11>朋霍费尔,《伦理学》,第236页。
<12>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2016年,第5—6页。
<13>同上,第2页。
<14>同上,第7页。
<15>同上,第18—19页。
<16>同上,第7页。“After Ten Years”: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Our Times, edited and introducted by Victoria J. Barnett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7),14-15。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4期(2021年夏季号)。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14期的主题是“纳粹德国时期的认信教会”,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世代Kosmos);网站(www.kosmoschina.org)

发表回复